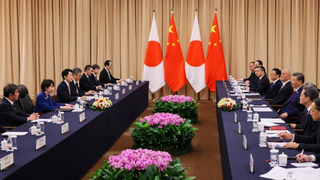最近與女兒逛街時,瞥見不少新一代化妝品的描述,發現當中的用詞已發生了有趣的轉向。我試解讀這些隱藏在美妝推廣背後的「語言密碼」。

相隔千里的兩地情誼,在酒酣耳熱的歌聲中,像為遼闊而歷史宏大的呼倫貝爾,發出響亮的讚歌。

今天的法治教育要讓學員了解法律知識,樹立法治觀念,培養法律素養和尊重法律。套用在學校的校規教育,也應是讓學生了解校規,樹立守校規的觀念,培養尊重校規的素養而進行的教育。

鹽之所以能成為「百味之王」,其核心機制並非簡單的味覺叠加,而是源於味蕾細胞膜上的「離子通道」機制。當我們深刻理解了這一粒微小晶體背後的科學,我們才能在新鮮食材中適量運用這份來自海洋的結晶。

國情教育是當下教育工作者急切需要認真總結和反思「為什麼做、做什麼、怎樣做」的領域。績效指標只是數字,但數字配不上感染力和溫度,反成一種威脅與破壞。

「經師易得、人師難求。」作為經師,應該是博學多才,能按學生不同的需要來授業、解惑,能啟發學生的潛能。若能品格高尚,能正人心、撥亂反正,認真負責地對待學生,移風易俗,影響周遭的人,這或可稱為人師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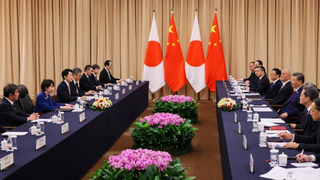
不少港人一到假期便到日本旅遊,日本文化在香港更是無孔不入,日本侵華、香港淪陷這些概念早已是「平行世界」。因此香港學校比內地更強調抗日戰爭,以平衡在香港青少年心目中對於日本的印象,也實在是無可厚非。

若老師能於批改和文件中多點空間,讓他們可以於球場上陪伴學生奔跑,或於一隅陪伴學生觀看周遭的事、物和人,快樂就在身邊,簡單也是十分快樂的。

教育、科技與人才的一體化發展,是香港基礎教育面向未來、提升質量的關鍵。要實現這一目標,不能僅靠學校單方面的努力,也需要多方合力,共同構建協同創新的教育生態系統。

春節是中國人傳統的習俗,同時也能鍛煉我們社交技巧。社交意欲及技巧是人工智能年代最寶貴的生活及工作技能,更能傳承中華文化意欲的黃金機會。

大埔,是一個有故事的地方,折射着香港發展的歷史;大埔人純樸、勤儉、誠懇、堅毅……借用余光中先生的話語──能成長、生活於大埔,是我的自豪與自幸。

在人工智能技術推動教育變革的背景下,為協助香港中小學教師、校長及教育行政人員掌握AI時代所需的知識、思維與技能,灼見名家傳媒與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將聯合舉辦AI賦能教學高峰會。

校董須理解問責機制、恪守專業,釐清治理界線,方能有效監督校務、管理人力與財務資源,確保學校健全發展。

考慮到我們東方社會對師道的期望,光是立下一道規例並不可能解決當前的工作壓力和專業需索之間的張力。如何調和,找出一個可行方向,實在有賴專家學者官員們去探求。

科技的進步不應只體現於金融指標,更應體現於對每個血肉之軀的守護。讓 AI 成為守衛生命的最後一道防線,這不僅是技術的必然,更是我們對死傷者的守望與對未來的承諾。

焦慮並不可怕,可怕的是我們被它所控制。當我們學會正視焦慮、專注於當下並積極主動地學習時,焦慮便會從一種壓力來源,轉變為促使我們成長的動力。

香港銳意發展成為國際教育樞紐,表演藝術正是一個契機。它不僅能完善豐富青少年生活,更能在提升人文素質的同時,與本港現行的多元發展方向形成相輔相成之效,推動整體社會的創新與活力。

希望藉由「快樂七式」,提供一套有系統、有方法的心靈陪伴指引,支援受影響的居民,也幫助社區中的每一個人,在這樣的時刻學習照顧自己、關懷彼此,共同凝聚心靈的韌性。

戶外考察不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一場觸動心靈的教育旅程。它讓學生學會尊重自然、關懷環境,並在探索中建立自信和解難能力。我們應充分利用這些自然資源,為下一代提供更全面、更深刻的教育體驗。

國家認同的培育不是從外部灌輸的標籤,而是從內部生長的認知情感體系──從小培育幼兒的家國情懷正正是我們為師應做的事。

學校製作音樂劇,新一年招募演員的工作又開始了,中一、中二年級同學踴躍熱情,中三、中四年級的參與人數卻明顯較少。原因何在呢?

教育局月中推出的「智」啟學教計劃,幫助香港學校主動轉型科創教育及擁抱AI,益處多多,也有潛在挑戰。

這趟送暖更像一堂真實的課:我們以為自己在送出「幸運」,其實對方可能疲憊、麻木、甚至不想被打擾。人的反應不可控,而我們能控制的,是是否仍願意做那件對的事。

閱讀的「動感」,從來不在於外在的喧嘩,而在於內心價值的覺醒與行動。它們在安靜的閱讀中生根,在熱血的運動中茁壯,最終在年輕的生命中,活成一段段屬於自己的傳奇。

南雄偏處粵東北,踏秋賞黃葉故然寫意,走梅關古道更能添追憶往昔情懷。

北都大學城的樓梯響了,接下來的是要見人下來。

品嚐梳乎厘的樂趣,正是在於體驗短暫存在、由溫差所帶來的極致口感對比。這不是魔法,而是精準掌控乳化、蛋白質變性與熱力學等一系列科學原理。

我曾舉辦專為教師設計的生涯工作坊,邀請老師畫下三個圓圈,分別代表生活觀、工作觀、教育觀。2026年讓我們從這三個圓圈的對話開始:不追求完美的重叠,而在動態的平衡中,尋得既能篤定前行、又能安頓自我的從容。

華師大在1980年首辦了華南師範大學香港書法函授班,課程竟羅致了當時眾多全國知名的大家。可惜,華師大的函授課程就只辦了一屆便被迫停下來,超強的教授團隊也就解散了。

現在的網絡平台充斥着大量粗話視頻,不少中小學生鸚鵡學舌,從小已經學得一口流利粗話。但其實粗話對香港青少年的負面影響深遠,不得不正視,否則教育界難以扭轉整個社會的風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