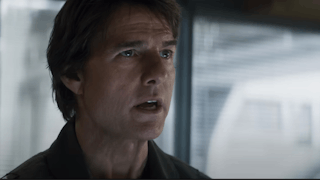與2820萬美元的直接院線利潤相比,IP授權與衍生收入累積約為票房的30 %++++++++++至50%,即2.8億至4.7億美元。對索尼而言,這意味着1.4億至2.3億美元的累積利潤──這才是真正可能在集團層級留下痕跡的數字。

看《無限城篇》的流水,製作費始終是前期沉沒成本,不會因票房變化而調整;而行銷與發行成本則攸關作品能否站上全球舞台,通常隨上映市場的擴大而增加。

野村證券就《鬼滅之刃:無限城篇》發表研究報告。我將以此為基礎,加上一些假設,解構一部動畫電影的經濟學:從票房到報表,從觀眾的一張電影票到跨國企業的現金流。

整齣電影看來,蘇諒當然不是主角,但他每次出場都帶着經濟學的冷光。這樣的角色或許繼續會不被重視,但正是這些「蘇諒們」,貫穿古今,讓代代文明和實體經濟得以持續運轉。

隨着荔枝專案受到朝廷關注,李善德離打通「荔枝路」只一步之遙。但右相楊國忠的華麗登場,讓蘇諒的投資頓成泡影。

創投自然要有耐性、得冒險,李善德確實不是一個空談理想的小吏,他的理性與執着近乎現代發明家及創業家。

在華人世界的敘事中,商人通常會被排除在主流之外。儘管當代中國大陸早已是工商金融業現代化的實踐者,卻依然不怎麼把那些「蘇諒們」放在眼內。

張蘭會輸的原因不是未達標的業績,而是因為拖帶權。拖帶權剝奪了創始人(或任何不想走的投資者)「留守」的選項。無論你對公司多麼有感情,無論你還想不想做夢,當觸發者決定離場,你只能隨波逐流。

資本世界的制勝關鍵往往濃縮幾行條款中,除了對賭協議外,控制權與優先權這兩大類條款,已經足以支撐一場史詩式的夜宴。

不論是 Earnout 還是 VAM,設計初衷也許都不壞。問題在於當這些制度被放進一個複雜而仍帶着野蠻生長特質的市場環境時,結果往往南轅北轍。

張蘭欲把其品牌俏江南做成餐飲界的 LV,但她與基金的兩次交鋒──估值調整機制(VAM)與回購條款,皆以慘敗收場,最終失去其公司控制權。無論企業家把資本當推手還是羔羊,都應量力而為。否則,故事的結局往往與銀幕上的同等慘烈。

VAM 與 Earnout 都是金融市場的下注機制,只不過下注的方向不同。一個讓賣方背書未來,一個讓買方押寶表現。

對賭協議多見於私募股權、併購交易和上市集資的交易之中,是投資者和被投企業就業績未達預期所訂的估值補償機制。但在香港,對賭協議未有被視為主流程,反使用英美常見的「棘輪條款」作為反稀釋保護工具,但這與中國式以業績為賭注的強硬協議並不盡相同。

打從上世紀 80 年代的《華爾街》(Wall Street)開始,金融電影的結局似乎都大同小異。《獵金遊戲》整體不失趣味,但劇情仍顯老套。

美國鍍金時代,面對資本野蠻式擴張與政商勾結的挑戰,引伸了一系列的改革與監管政策,才成功令市場推向較為成熟和規範的軌道。內地亦正經歷類似的拐點。這也許是穿越兩個世紀的「鍍金遊戲」最值得借鑒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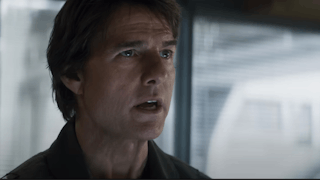
科幻電影揭示人類正站在技術發展的臨界點,人工智能的快速擴張,已讓現狀與虛構情節難分難解。真正「不可能的任務」,其實是如何駕馭AI。忽略這個平衡,最終可能引爆人類自我毀滅的連鎖反應。

臧姑娘的奮鬥值得欽佩,但仔細一想,從事餐飲服務業的誰不是如此?那麼,臧姑娘究竟有何超越這些能熬的人之處,能脫穎而出?

電影《水餃皇后》中不斷標榜的個人奮鬥精神固然值得肯定,背景音樂反覆哼着〈阿信的故事〉,但我們不能忽視「邊有半斤八両咁理想」的普遍性。

呼籲大家重新審視教育的本質在於引導而非操控,象徵一種更包容、更協商的家庭與社會價值觀。

當我們說市場「有效率地反映資訊」,不應代表市場的價格一定正確。有效率地反映信息,僅僅是表示新資訊能快速地進入市場價格,至於這些資訊究竟正確與否,市場並不保證。

當荷李活忙着在漫威電影塞進熊貓元素時,內地的製作單位也學會了用「去意態化」都市劇來敲開國際市場。

人是有記憶的動物,我們被記憶所定義,愛情、友情和榮耀等的回憶固然珍貴,但對味道的記憶和對母親的懷念和鄉愁,或許同樣來得強烈。美食是我們稱之為「家」的鑰匙,它鮮活地存在於我們的記憶中。

或許,邁向永續的旅程,就像跨越百尺之遙,其實並非遙不可及。我們過去在追求無盡增長的同時,是否忽略了近在咫尺、更為珍貴和持久的東西?漫步生命之旅,何不放緩腳步,細品沿路的小店,米芝蓮美食可能就在眼前。

為什麼雷文洛克能被稱為麥當勞「創始人」?儘管他並不是系統的發明者,但他是將麥當勞模式帶向全球的那個關鍵人物。他擁有敏銳嗅覺,看到了潛力,並用他獨特的企業家冒險和「賭一鋪」的精神,將其推廣。

儘管萬斯帶有一些經濟民粹主義色彩,但在每天受到嚴格監管措施威脅下的矽谷新派的眼中,卻顯得愈來愈具吸引力。

月本來就有陰晴圓缺,在大自然的規律下,「人」不可能長久,但信心和夢想卻可以。張黎在異國奇跡相遇,是故事使然。今日這個歷史時空,更需要我們敢想和追夢。

這是《但》鏡頭之下,1997年香港的「工業」面貌,鏡頭令我感到一絲惋惜。想起我的父輩,也是70年代來港的新移民,許多就是《網中人》中的阿燦,都是在膠花紗廠等的工廠裏上班,被純香港人和早來的同鄉調笑。

戲劇性的情節原來在荷李活的現實世界中,更引人入性。近代的巔覆者、打着串流旗號的媒體們,也正依循上一代人的步履,放棄激進,奔向「古老」廣播大台,有刀無鋒。曾經叛逆、在網上飛馳的冒險家,已變成平庸三色台。

不過,變幻原是永恒,扭斷狗脖子的凶漢,既然會被吃魷魚有如吃生菜的玩家KO出局,那麽,該玩家是否也應該會預料到,他總會遇上狗血的一刻?

也許,本地大台要做好的,不是口碑,而是學寫聰明的廣告算法,兼職做房東,學做「市集」和「果欄」,多在串流媒體的寵兒Z世代身上打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