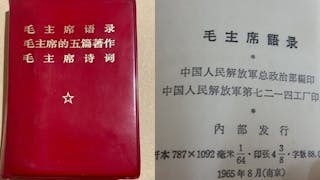參加1991年立法局直選的「親中」候選人共有3名,3人在各自的選區都得票第三,贏不到議席。

學校的日常工作已上了軌道,而且有一位得力的副校長負擔了最重要的校務。我感到精神有點空虛,要找點既有挑戰性、又在我能力範圍內的事情來做。於是給魯迅那句詩說中:「無聊才讀書。」

在馮可強的號召下,建港協會於1990年2月宣告成立。協會「論政而不參政」,即研究香港的政治、經濟、民生等問題、提出建議,但不會派出成員參加選舉。

為了平穩過渡,中英兩國政府同意立法機關以「直通車」跨越回歸,唯具體安排理應由中英雙方共同決定。但港英政府推出代議政制發展綠皮書和白皮書,完全沒有諮詢中方的意見,偷步推政改,引發了一場風波。

香港社會意見分歧,《基本法》自不可能滿足所有人的要求;但這部經過「三上三下」廣泛諮詢、歷時4年零8個月寫成的法律文件,事實上獲得大多數香港人的接受。

六四事件之後,中國政府一再強調對香港的政策沒有改變;然而,香港各界與中國政府過去數年在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建立起來的互信、互諒、互讓關係,已嚴重受損;這對《基本法》的最後定稿,不能沒有影響。

1989年2月,基本法草案初稿公布,再進行5個月的諮詢,準備翌年提交全國人大審議通過。4年多的起草和諮詢過程,體現了中央官員和香港社會各界對制訂一部最好的《基本法》的共同意願和合作精神。

麥理浩1979年3月從鄧小平口中知道中國要收回香港後,馬上向倫敦報告。英國政府一方面極力爭取1997年後繼續管治香港,另一方面為爭取失敗部署。在這樣的背景下,香港社會出現了對民主採取相反立場的兩派意見。

草委會主任委員是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姬鵬飛;8名副主任委員中有4名港人:安子介、包玉剛、費彝民和李國寶;秘書長是港澳辦副主任李後,兩名副秘書長是魯平和毛鈞年。草委會成立後,歷時4年多的《基本法》起草工作隨即展開。

我們的教育碩士課程即將完結的時候,程介明告訴我,他要到英國讀博士,邀我跟他一起去。我婉拒了他的美意,跟他分道揚鑣。

對於培僑申請加入直資計劃,李越挺署長顯得十分熱心。我們相信,這直資計劃開始時很大程度是為愛國學校度身訂做的。

我們收到可靠消息,港英政府高層已同意讓我們獲得資助。問題是要找一個辦法,讓我們自行收生;政府對我們只給錢,不派學生。

1985年,我出席一個論壇。有人問講者之一的教育署長梁文建,為什麼像培僑中學這樣的學校不獲政府資助。梁文建坦白承認:「跟學校的教育質素無關。」潛台詞是:「與學校的政治立場有關。」

在座的一位老校長和我都犯了英國人犯的錯誤:低估了當代中國領導人對國家主權問題的執着。我們當然還未知道,鄧小平發明了一國兩制解決國家統一問題。

在教學生涯的早期,我遇到幾個難忘的學生,增強了我當教師的決心和自信。

教學管理改革措施的推行,在同事當中引起不同程度的抵觸情緒。但掀起最大風波的,是我負責執行的優秀教師評選計劃。

文革過後,香港左派陣營裏的價值觀念改變了:中資機構招聘職員,除了講愛國,更要講學歷。家長都要求學校提供的教育令他們的子女取得良好的會考成績。

有人說吳校長出訪東南亞,是藉籌款之名遊山玩水;有人說新校舍設計奢華,有違愛國學校艱苦樸素的精神。吳校長憋了一肚子氣。

李兆基對培僑籌建新校舍表現得很熱心,爽快地承諾了分擔全部建校經費的七成。但沒土地便建不成校舍;他建議我們先向政府爭取一塊土地。

政協委員的職責是參政議政、建言獻策。我到廣州開會時最大的意外收穫,是有機會和培僑中學的第二任校長杜伯奎先生見面,並到他家裏作客。

在培僑,我們時刻關注國家的發展,留意來自國家的每個重要訊息。1970年代,國家發生了許多出人意表的變化;我們收到的訊息,有的振奮人心,有的令人沮喪,有的使人迷惘。

文革掀起愛國熱潮,其他愛國學校也和培僑一樣,在這段期間急速膨脹。1971那一年,培僑正分校5個單位合共有中、小學超過100班,學生4300餘人。

我在培僑的第二年,加入了班主任的行列。班主任要做家訪,這對全面了解學生幫助很大,一次家訪,可以完全改變教師對一個學生的看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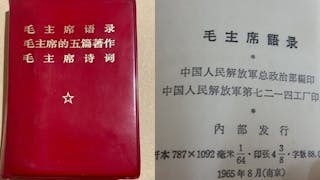
我入培僑時,學校受文革的影響,實行天天讀報或《毛主席語錄》的習慣。有一位老師,「天天讀」時只看報紙的娛樂版,從不看新聞。另有些人拿起報紙瞧一瞧便放下,做其他事情。我心想,這樣的「天天讀」有什麼作用?

上門來做訪問的《學苑》記者是黃紹倫和李明堃,他們後來都成為很有成就的學者。那篇訪問在港大學生中引起了相當熱烈的反應,很多港大學生通過這篇訪問認識了培僑、認識了我。

我入職時,培僑只有很少數像我這樣的外來人。所有同事,不論年輕年長,對我都十分友善。我覺得自己很快便融入了培僑這個集體。

這是一場「三不」面試:不查學歷證書,不考專業知識,不講聘任條件。吳康民校長即時告知我已獲聘任,但沒簽聘約、沒提薪酬。這次見面開始了我和吳校長的交情。

因決定暫時不到外國留學,當港大數學系助教的一年合約結束後,我便要另找工作。毛鈞年知道我有意到學校教書,建議我去培僑中學。數天後,我收到程介明的電話,說吳校長歡迎我到培僑教書。

那時反英抗暴已經沉寂下來:炸彈沒有了,示威遊行沒有了,罷工罷市罷課也沒有了。市面恢復平靜,生活恢復正常,沒有任何迹象顯示香港很快要解放。我知道畢業試決計逃避不了,唯有收拾心情,埋頭苦讀。

毛鈞年和傅華彪同齡,他們兩人都很有學識,見解相當接近,待人接物的誠懇友善態度也很相似。但兩人的形象與說話風格卻很不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