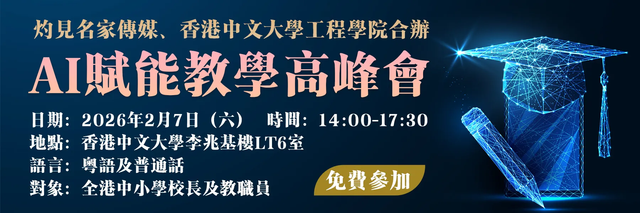我本來沒打算長期在培僑工作,但年復一年過去,離開培僑的念頭從未在我腦中閃過。
在吳康民的領導下,和培僑的同事們一起奮鬥,我很愉快。同時,我對教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在教學生涯的早期,我遇到幾個難忘的學生,增強了我當教師的決心和自信。
批評與道歉
第一個是戴同學。我開始教學不久,他在我上課時不專心,我批評他,他竟駁嘴,說了些難聽的話;我無名火起,痛罵了他一頓。下課後我回到教員室,靜下來想想:剛才沒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緒,對學生罵得太兇,一定傷害了他。我整天感到不安。
兩天後,我到同一班上課,對全班同學說:「前天上課,我對戴同學罵得很兇,那是不應該的。我誠意向他和大家道歉。」全班靜下來,沒有人作聲。下課時,個子高大的戴同學從後排的座位衝上來,跑到我面前;我吃了一驚,以為他要有什麼動作。不料他垂下頭,眼有淚光,低聲對我說:「老師,是我錯,對不起,對不起!」多年後,我數次偶然碰到戴同學,彼此都沒有提起這陳年舊事,但從他的眼神,我看出他對這往事記憶猶新。
字典錯了
第二個是黎同學。我在英文課講解一段文字,他在座位上打斷我說:「你解錯了一個字。」我覺得他很不禮貌,便冷冷地回應說:「我沒錯。」誰知他從書桌裏掏出一本翻開了的字典,指着上面一行說:「字典說的不是你的解釋。」
我接過他的字典看了一眼,說:「嗯,果然錯了⋯⋯字典錯了。」我拿着字典走向牆角的廢紙簍,接着說:「這字典不好再用了。」說罷把字典扔進簍裏。這事很快便傳遍全校,都說我把學生的字典丟到垃圾桶裏。有學校領導找我談話,批評我毀壞了學生的財物,對工人子弟缺乏階級感情。黎同學的字典其實沒有損毀;他的家人我認識,感情還可以。
錯過了關心
第三個是姜同學。我上中二數學課,要講「直角」的定義。我把記憶裏的英文定義翻成中文說出來:「當一直線站在另一直線上,兩鄰角相等,兩線的夾角就叫『直角』。」個子矮小的姜同學舉手,很認真地問:「老師,站着叫『直角』,蹲着是不是叫『扁角』?」全班爆起笑聲,我也禁不住莞爾而笑。
在這小猴子身上,我看到我小時的影子。不久後一天,我有事外出,看到小猴子和一個婦人並肩坐在校門側,小猴子哭得很傷心。我正趕去開會,又估計問題已有其他同事在處理,便沒停下來關心他。想不到那是我最後一次見到姜同學:他當天退學,以後再沒回來。
學生來學校讀書並不容易。我們要讓他們在學校每一天都過得愉快、過得有意義。
1979年,我決定回大學去,充實自己的教育理論知識。我決志以教育為終身事業。
我沒留意,麥理浩剛去了北京,開始了中英兩國關於香港前途問題的角力。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