蜞/蟣(kei11)、女(na35)
粵語叫「水蛭」為「kei11 na35」,通常寫作「蜞乸」。白宛如《廣州方言詞典》及周無忌、饒秉才、歐陽覺亞《廣州話方言詞典》都有「蜞乸」條。白氏云「水蛭,北方叫螞蟥。」不過未引古書為證。北宋 丁度《集韻》‧之韻下有「蜞」字,音「渠之切」(粵音就是「期」),釋曰︰「蟲名,水蛭也。通作『蜝』。」可見「kei11乸」的「kei11」,確實可作「蜞」;不過,其實又可以作「蟣」。
《爾雅‧釋魚》「蛭,蟣。」晉 郭璞《注》︰「今江東呼水蛭蟲入人肉者為『蟣』。」唐 陸德明《經典釋文‧爾雅音義》「蟣」條︰「郭音『祈』(黃氏案︰「蟣」、「祈」在北宋 陳彭年《廣韻》均有「渠希切」[微韻]一讀,此音粵讀亦與「期」同)。《字林》云︰齊人名蛭也。《本草》又作『蚑』。」《說文》「蛭」︰「蟣也。」又「蟣」︰「蝨子也。一曰齊謂蛭曰蟣。」周無忌、饒秉才《廣州話標準音字彙》「蟣」條云︰「kei2(黃氏案︰此音即筆者所用音標的「gei35」[音同「己」] )虱卵k'ei4(黃氏案︰此音即筆者所用音標的「kei11」[音同「期」] )水蛭。」
由此可見,粵語「kei11乸」的「kei11」作「蜞」或「蟣」都可以,只不過今時今日「蟣」在普通話裏只存「蝨子的卵」一義(見《現代漢語詞典》[第7版]「蟣」[音「ji3」(漢語拼音)]條),而大部分粵音字書又只收錄「蟣」的「gei35」一音,不收其「kei11」音(《廣州話正音字典》、《商務新詞典》及上引之《廣州話標準音字彙》除外[詳粵音資料集叢網站]),所以大眾就以為「kei11乸」就只可以寫作「蜞乸」了。

蟣、蜞為一物
若以為筆者視「蟣」、「蜞」為一物,可能武斷了一些(二字「中古音」不同,前者在《廣韻》‧微韻,後者在《廣韻‧之韻》;但若以元朝 周德清《中原音韻》的音系為代表的「近代音」為準,則二字已同音七百年左右[「中古與「蟣」同音的「祈」和與「蜞」同音的「期」同收在《中原音韻》‧齊微韻‧平聲‧陽[平]的同一組字內,間接告訴我們,當時「蟣」、「蜞」是同音字。] ),那就不妨看看明朝李時珍的名著《本草綱目》的說法了。該書《蟲之二》的「水蛭」條云︰「釋名 (與『蜞』同。《爾雅》作『蟣』。)至掌(《別錄》),大者名馬蜞(《唐本》)、馬蛭(《唐本》)、馬蟥(《衍義》)、馬鱉(《衍義》)。」觀此即知筆者非武斷也。
再細心一點看看二字出現之先後,若以古代語文工具書為準,可知「蟣」先而「蜞」後(成書於戰國至漢初之間的《爾雅》、東漢的《說文》均已收錄義為「蛭」的「蟣」字,而北宋的《集韻》始有義為「水蛭」的「蜞」,前此各字書、韻書的「蜞」[或作「蜝」]只是「蟚蜞」[小蟹]一詞之語素);所以筆者認為「kei11乸」之「kei11」,寫作「蟣」或「蜞」都可以。
乸在粵語的用法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何以提到「水蛭」,今日粵語「kei11」(不論用「蟣」還是「蜞」)後面一定要跟一「乸」字作為其無意義的後綴呢?粵語的「乸」有幾個用法。
《香港粵語大詞典》「乸」條︰「雌性動物︰我養咗兩隻狗,一隻公,一隻乸。……母的;雌性的(附於動物名詞之後)︰豬乸[母豬]。[貶]妻子;女人︰呢個係我隻乸。乸型的省稱……」
其實,「乸」至少還有第義︰「母親」(此一義至少白宛如《廣州方言詞典》「乸」條有收錄)。如「兩仔乸」就是「兩母子」;「有爺生,冇乸教」(字面義就是「有父親生,沒母親教」)實在的意思就是指「(某人)缺乏家庭教育」。但「kei11乸」的「乸」並無上述任何一個含意,只作「後綴」用而已。

(Shutterstock)
乸與女
就此問題,筆者又想到「蝨乸」(蝨子)與「蛤乸」(田雞。「蛤」音「gɐp3」[音同「鴿」或「gap3」[音同「甲」])這兩個粵語詞。此二詞中的「乸」同樣只是後綴而並無「雌性」、「母親」、「妻子」等義。筆者又想到古代有「縊女」一詞。「縊女」為昆蟲名,而當中的「女」同樣不表「雌性」、「母親」、「妻子」等義。《爾雅‧釋蟲》「蜆」條云︰「縊女。」晉 郭璞《注》曰︰「小黑蟲,赤頭,喜自經死,故曰『縊女』。」筆者覺得,如此以表女性的詞作後綴來命名昆蟲似乎是吾國語言史上一種值得注意的習慣,有心人不妨研究一下。
筆者又想,「蜞乸」、「蝨乸」與「蛤乸」的「乸」與「縊女」的「女」本來都指「雌性」,卻都作「蟲名」的後綴,並且兩字的聲母都是「n-」;何以會有這樣的巧合?筆者是相信上古有「複輔音聲母」的,所以曾經懷疑「母」字上古讀「mna」或近乎「mna」的音(因為「mna」丟掉「m」就是「na」[令人想起「乸」],丟掉「n」就「ma」[令人想起「媽」],兩音在粵語裏都可以有「母親」義),不過一直找不到證據。現在既然發現「乸」與「女」在意義、用法和發音(聲母)上有這樣的巧合,那何不查查「女」的上古音呢?一查之下,就有如下的發現了。
「女」今日粵音有陰上[第二聲]「nœy13」及陽上[第五聲]「nœy35」兩讀,這不用筆者說,大家都知道;但大概很少人知道的是,根據已故學者王力的「古音構擬」,其上古音是[nia](見《王力全集》第十二卷《詩經韻讀 楚辭韻讀》第115頁《詩經入韻字表》「5.魚部」)。
筆者在幾本拙著中講過不止一次,古音中的介音到了今日粵語的演變方式之一是︰脫落。如︰死(上古音[siei],粵音今讀「sei35」)、美(上古音[miei],粵音今讀「mei35」)、六(上古音[liuk],粵音今讀「luk5」)等。
若上古音「nia」的「女」脫落介音的話,就讀「na」了。顯然,「乸」的本字應該是「女」,只不過不知我們哪一個年代的祖先,因為不知自己口中的「nia35」或「na35」就是「女」,就創一「乸」字來表意而已。「縊女」這一名詞若自古一直流傳在粵人的口語裏,今日自然是讀「縊na35」了。
當我們知道粵語義為「雌性」、「母親」、「妻子」的「na35」,是「女」一詞的上古音([nia])的遺傳與變異時,我們就可以解釋何以在甲骨文中,「母」、「女」竟然可以同用。
馬如森《新版殷墟甲骨文實用字典》「女」條云︰「卜辭義︰1. 女同母,用作母神,東母。『……尞于東女九牛。』(《續》1‧53‧2) 2. 用女為母。……『大甲女妣辛……(黃氏案︰此一省略號為馬氏所加)』(《粹》182)……」又,崔恒昇《簡明甲骨文詞典》「女」條︰「女。女性。……用為母。指前一輩女性親長。『惠(惟)羊侑于女丙。』(《佚》143)……配偶。『尞于王亥女。』(《乙》6404)……」兩位甲骨學家都指出在甲骨文中,「女」可用為「母」,卻都沒有解釋何以會有此現象。
其實,知道「女」是「乸」的本字之後,我們若用今日粵語的「na35」(女)套進甲骨文裏,至少可以解釋何以「東母」又可以叫「東女」;何以「女己」即「母己」,「女戊」即「母戊」,「女辛」即「母辛」,「女庚」即「母庚」(參崔氏《簡明甲骨文詞典》各相關條目);又何以「王亥女」不是王亥的女兒,而是王亥的妻子。粵語真的可以「證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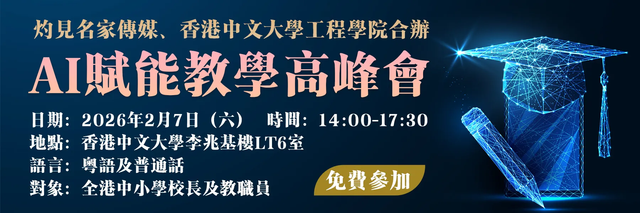



![粵語義為「雌性」、「母親」、「妻子」的「na35」,是「女」一詞的上古音([nia])的遺傳與變異。(Shutterstock)](https://bucket-image.inkmaginecms.com/version/desktop/9dde7c0f-adea-48d0-9671-8f5a6345ad4a/image/2025/10/7af6cfae-d005-48c7-bb02-15fe6b6a2fee.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