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聶華苓說她一輩子「恍如三生三世:大陸,台灣,愛荷華,幾乎全是在水上度過的。長江,嘉陵江,愛荷華河」,又說她是「一棵樹,根在大陸,幹在台灣,枝葉在愛荷華」。

我在看這本《等閒識得東風面》時正是這樣,這個書名立刻使我的大腦浮起這首詩的下一句「萬紫千紅總是春」。

60至70年代全球正值反殖浪潮,港英過去行之尚可的「華洋分治,以華制華」策略已不足以應對世局,六七暴亂付出難以彌償的大量傷亡代價,也成為香港社會轉型的契機。

李智慧接近完美而又揮灑豪氣的演出,無疑與德伏扎克的作品風格不謀而合。但如果還要入型入格,帶着斯拉夫民俗氣色的風高亮節的菱角,小姑娘還未能完全做到,不過事前亦無估計她能夠做得到。

高樓夜靜參差影,故園萬里關山冷。

可惜天意弄人,香港中樂團12月27日宣布彭修文出任音樂總監之後僅僅一天,民樂一代宗師騎鶴西去,年僅66歲,出師未捷,留下無限遺憾。

每一個大流派的興起,必伴隨着對命理的不同見地。對命運的看法,看四柱的看法,對推算法則的看法,都有自己一套較完整的規範。使用的人愈多,這套規範就愈完整,解釋命運就愈精準。

每朝代都有人說一些書法大家寫醜書。其實只要被評為寫醜書的書法大家,他們的字都被讀到,也見到書、法和書法的含義,那便是書法作品,美醜是見仁見智問題而已。

「戲劇,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如果沒有戲劇,我就不可能走到這一步,演戲為我帶來很多……」戲劇,讓李鎮洲的生命變得完全不一樣!

庚戌子按照金庸在該篇後記論及的思考方式,又破解了一個本來毫不起眼,也可能因而從來未有研究者深入分析過的事物──西瓜。

術數界近年最多談及2024年,社會便轉入「下元九運」。到底什麼是「三元九運」曆法?運的起點如何計算?一起聽聽術數名家蔣匡文從占星及數學角度剖析。

粵地有一種食品叫「煎dœy55(音同「堆」)」,通常就寫作「堆」。劉扳盛《廣州話普通話詞典》「煎堆」條︰「油炸年宵品,球狀或餅狀。」

宋太祖雖然以禮待文臣著稱,但脾氣再好的人,當了皇帝也會有脾氣,宋太祖也未能免俗,一言不合就打掉了大臣兩顆牙齒。但他害怕史官春秋之筆,載其過錯,故能及時醒悟,以賞代罰。

《婦人集》為陳維崧所撰,記明末清初數十奇女子生平軼事,李香君為其中一則。其所謂「與陳處士小札」云云,頗值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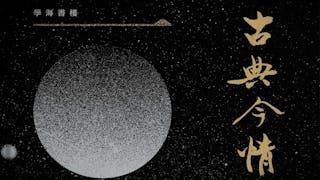
學海書樓始創於幾位積學之士的崇高理念與坐言起行,在百載變遷之中,逐漸與香港公共圖書館、教育界、藝文界結合成學術文化的共同體。

《相約星期二》誠意邀請你,在舒適的劇院裏,「圍觀」張可堅和方力申如何處女對決,看誰對前人的成績,抗壓性較高?新的組合、新的演繹,訴說一個動人的故事。

能敬重和欣賞別人,才能增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原來十分重要。

筆筆見筆毫不含糊。景生情,情生景,岑文濤的藝術導出生命不息的意義,況且不落他人窠臼,所謂其志不在毫里而存千里!

廉政公署(ICAC)於1974年2月15日正式成立,而葛柏案亦成為廉署要處理的首宗大案。葛柏服刑後出獄當天,傳媒如何展開追逐戰、TVB新聞部如何絕處逢生,50年後今天仍然是新聞界的話題。

羲之在唐太宗的推崇下,竟未有一紙真跡存世,所見均為雙鈎、摹本,但學書者均以之為大宗,天下第一行書的複製品多達百餘種,可見追隨者眾,純從書法而論,既是極品,真真假假並不能減退蘭亭的價值。

寒鴻夜雨,誰曉蘭心語,霜染青絲飄幾許,回首紅妝院宇。

最後一首演出樂曲是布瓦爾迪厄(François-Adrien Boieldieu)的《豎琴協奏曲》(Concerto pour harpe),與古典時期海頓的風格非常相似。

10月19日,中國香港傷殘人士體育協會舉辦杭州亞殘運香港殘疾學生觀摩交流團發布會,並與香港中國旅行社簽訂合作備忘錄,約有50名特殊學校師生及發展隊殘疾運動員到場,他們也將親赴杭州與亞殘會運動員交流。

記得有一次演出貝多芬《皇帝》鋼琴協奏曲,老外獨奏錯音頻生,全曲結束時,忍不住喝倒彩。誰不知錄音咪就掛在前面半空,當電台重播該音樂會時,清楚聽到掌聲中的「雜音」。

香港的構成一向多元,建立共融和諧的香港社會有賴各個群體彼此尊重,香港新聞博覽館舉辦「推動多元文化,建立共融和諧社會」講座,意在推動多元文化融合,另「我們的女勇士」專題展覽展期至 11 月初,歡迎參觀。

粵語「冇定準」意思是「沒準兒」。《香港粵語大詞典》「冇定準」條︰「不一定的;不固定的」。凡知道「冇」即「無」的音變的朋友,自然知道「冇定準」即古文獻中的「無定準」。

在金庸數百萬言計的著述中,寫及親兄弟的也實在太少。而那些兄弟友愛,同步同心的親兄弟,卻又是難以結交,沒有知心朋友的人。

堅稱要維護普世價值,處身高度文明的列強,為何不應將其得之不「義」的文物,文明地歸還中國呢?

驀然回首,鄧美玲在粵劇圈,已發展多年,從早期習藝於八和開始,至今已有40年的光景。憑着鍥而不捨的精神,她不斷追求進步,亮麗的表現,亦有目共睹。

創辦於四十四年前的「油中」,自創立之日起,便定位為人文社科專門店,當中尤以文史哲書籍品類最為齊全。在「油中」遇見「似曾相識的香港」,秋夜有書香盈袖,便是香港書業邂逅香江文化的一道亮麗風景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