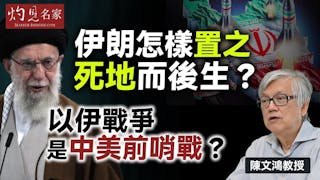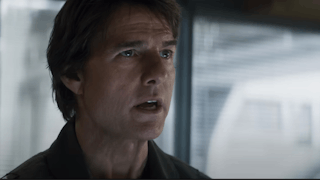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的故事家喻戶曉。這件事在蕭統《陶淵明傳》有記載:「會督郵至縣,吏請曰:『應束帶見之。』陶淵明歎曰:『我豈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兒!』即日解印綬去職」,應該是確有其事了。
古代重量單位,一石(百斤)十升,一升十斗,斗即是一斤的重量。五斗折合五斤,如果陶淵明因為不稀罕五斤米而辭職,應不是什麼值得表揚的事。就正如一個月薪萬多元的職位,你和上級有過節,憤而辭職,如要誇耀自己多有犧牲,應該沒有什麼說服力。
但事情不是這樣的。按晉朝官俸,薪金為「半錢半穀」制,即錢米各佔一半。陶淵明彭澤令的職位,俸祿為月錢二千五百,米十五斛。一斛為十斗,一天工資是五斗米和八十三文錢。所以五斗米只是半天的薪酬,這樣的俸祿可不輕啊!
而且這職位得來不易,是陶淵明的叔父在戰亂的環境下多方請託求得的。陶淵明在年過五十時寫了一篇《與子儼等疏》,慚愧自己沒有什麼財富留給兒子,對兒子「幼而飢寒」深自責備,慨歎「稚子家貧,每役柴水之勞,何時可免」。可見陶淵明「這份工」,對他和家人來說是多重要,在41歲時就「提早退休」,是多麼大的犧牲。何況辭工也大可不必,就像很多「打工仔」般,口甜舌滑討好上司,日常打躬作揖任人差遣,不就可以嗎?半天賺五斗米,長做長有,雖不及「萬鍾則不辯禮義而受之」(《孟子‧告子上》)中「萬鍾」這「一筆過撥(鉅)款」這麼宏偉,但也足夠誘惑了。陶淵明不是蠢,只是心理上過不了自己一關,招來金錢的極大損失也不計較。這是一種傲氣,一種自尊,一種風骨,人生再重來一次,想這抉擇也不會更改。
個人抱負的實踐微不足道
別以為陶淵明歸園田居就像他自己所形容的「久在樊籠裏,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般毫無牽掛,他的內心痛苦可不足為外人道。陶淵明本非無用世之志。以前,他「少年壯且厲,撫劍獨行遊」(《擬古》)、「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雜詩》)。朱光潛說「陶潛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魯迅反過來說「陶潛並不是渾身是靜穆,所以他偉大」。不靜穆,心潮就會時刻逐浪高。不這樣,陶潛就不會在夜闌人靜時慨嘆「氣變悟時易,不眠知夕永。欲言無予和,揮杯勸孤影。日月擲人去,有志不獲騁。」(《雜詩.其二》)
但陶淵明自我犧牲的精神,卻比孤煙里巷生涯更值後人景仰。這日夕漿水之勞,尤其內心世界的衝擊,原本並不需要,也不值得,但相比於人格的尊嚴,個人抱負的實踐,無論如何是微不足道了。這種孤懷,不是人人明白。陶淵明隔壁住了一位農人,也不明白。有天農人拿了一壼土酒,來勸陶淵明不要這樣固執。「襤褸茅檐下,未足為高栖。一世皆尚同,願君汨其泥。」(《飲酒.其九》)這種粗樸率直的「睇錢份上」的勸勉,是人同此心了,但卻得到「且共歡此飲,吾駕不可回」的回絕。
陶淵明是一個好人,有良知,有原則,還富有同情心,有人道主義精神。他自己窮,「禍」及妻兒,不去說了。就是他環境還不至於拮困,還有彭澤令哪半天五斗米的俸祿時,他派遣一僕人給兒子,但不忘叮囑:「汝旦夕之費,自給為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也,可善遇之。」他沒有因自己是「老細」而「擺款」,反而要兒子推己及人,不要虐待別人的兒子。香港近月發生多宗街頭警民暴力衝突,防暴警察配備精良,捉到沒有武器隨身的示威者,有時幾個軍裝圍上一個被制服的,在毫無反抗力量下還是揮舞警棍,打得頭破血流。想想「此亦人子也」,如果被打的是自己子侄,又怎打得下手?
陶淵明是什麼時候人?他生於公元365年,卒於公元427年,無論如何都是中古時候人了。他的人道主義精神,他的自我犧牲精神,後人可以學得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