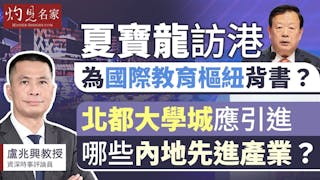上周本欄文章,我以「殘局」去形容當前香港形勢。過不了此關,則一切向前看的思考都屬徒然。無論這場政治危機最終以和解還是武力收場,港人和中央當局都面對同一問題,「一國兩制」能否走下去、可如何走下去。
民心不能靠止暴制亂爭回
目前與政府處於「對立」的,不止是一小撮的「搞事者」,而是佔較多數的市民,中央及特區政府對此應心中有數。當中有反對修例、有不滿政府施政、有批判體制不公、有懷疑「一國兩制」,也有對政治現狀失望甚至絕望的。在憤怒、仇恨、創傷和悲情交集下,要化解危機,需解開大大小小的結,始終需由政府採取主動,非朝夕可達,學理上有「4R」──回應(Response)、和解(Reconciliation)、檢討(Review)、改革(Reform)四部曲。動亂未止,則難以推動。
激進抗爭者以為憑藉民情再加勇武「攬炒」、訴諸國際便可逼使特區和中央政府屈服,這屬想當然。任何政府當局均不會對破壞公共秩序者放軟。任何社會皆存在一個「法紀多數」(law and order majority),一旦觸及這條民眾底線,民心便移動。1967 年左派反英暴動,最終殖民地政府以軍警粗暴平亂,當時多數市民肯站在政府維持法紀的一邊。國際輿論也不會同情暴力升級(註)。若變成暴力革命行動,則中央定必武力進場。
但是,廣大民心不能靠「止暴制亂」爭回。參考法國總統馬克龍處理「黃背心」抗爭的經驗,他雖對暴亂採取強硬手段,可是作為領導人其重點是放下身段,走進民間,以「更軟」的施政改革去爭回主流民心。公權力要彰顯,靠的是民氣。究竟香港九七回歸以來,出了什麼大問題?這裏暫不談經濟民生,並非不重要,乃因當前主要矛盾在於政治和管治,可見諸三方面。
一國兩制下的存在主義危機
(1)「一國兩制」下的「不自在」,導致某種存在主義危機(existential crisis)。「兩制」之間必然存在張力,特區高度自治與國家中央權力之間需找出平衡點,關鍵是尊重、兼容、互利。一個沒有特色及異彩的香港,對國家沒有好處;但是,一個只強調自己、不重視國家連繫的特區,不會令內地當局與人民覺得為國家「加分」。回歸以來,矛盾和張力增加,處理不好「異」與「同」之間的平衡,及內地與香港因歷史及制度因素構成兩地不同的「存在」方式而產生隔閡和認知差別,致雙方容易出現「受威脅」感。
幾任特首政治上皆受困或敗於涉「內」(地)、涉「中」(央)的爭議。董建華敗於《基本法》23條國安立法,曾蔭權首任政改挫敗,2010 年政改險陷滑鐵盧,梁振英受挫於反國民教育及「佔中」抗爭,而今林鄭月娥敗於《逃犯條例》修例。此外,凡涉「內」的重大基建項目和經濟合作皆被反對派抹紅否定(指為「被規劃」),因為他們知道,不少市民對內地制度戒心仍重,批判內地有政治市場。
所以,若不理順民心,只重申憲制秩序和全面管治權,效果不彰。應要再思考「一國兩制」的實踐及香港的前途問題。
「怕失去」的政治
(2)香港身份的迷惘,令港人患得患失。回歸以來一直存在香港身份定位問題,初見於文化及價值領域──如早期關於母語教育(被視為不再重視英語)及普通話教中文(被視為排斥粵語)的爭論,及一些文化人和知識界鼓吹香港傳承、歷史保育與維護核心價值,因為他們怕「失去」原有的香港制度與方式。2003年50萬人反23條立法是這種「怕失去」(自由)的潛在焦慮首次走入群眾政治,今次同樣大規模的反修例抗爭,也是「怕失去」之政治的延續。
早於1980年代初,中央主理香港回歸事務的官員對港人心態,摸得十分清楚,所以才有「馬照跑,舞照跳,一切不變」的承諾,鄧小平也不以擁護共產黨為愛國者標準。《基本法》盡是延續原有制度、政策和方式的表述。因此,不用懷疑中央尊重香港現實、爭取港人民心的初衷。《基本法》也以「香港永久性居民」作為港人身份的法律和公民權利定義,與內地有別,並維持香港特區管治的獨特性。
香港身份與國民身份,不必互相排斥,關鍵是如何平衡,港人可既愛港也愛國。按香港大學民調,1997 年自認是「香港人」和「中國的香港人」佔比分別為36%和近24%,合計六成,這不應是意外。過去20多年,前者大底波動於三、四成之間,2012 年曾最高見45%,但今年中因修例風波,急升至53%,後者為23.3%,加起來超過四分三,預計經過持續抗爭的刺激,會進一步向上。
本來,本土性各地皆有,但當本土主義演變成為否定內地甚至尋求與國家主體切割的分離主義,必然引來中央的憂慮與強力反應,又若本土抗爭走向勇武(暴力)化,也會令中央以極端角度視之。這樣,原來回歸的兼容就無可避免走樣。究竟要保持一個怎樣的「香港」才具時代意義?

港人治港體制缺乏改革求變動力
(3)現行的「港人治港」體制凝聚不了社會,缺乏改革求變的動力。1980年代制訂基本法時,為求平穩過渡,傾斜於延續舊有管治體制和邏輯,輕視回歸帶來無法迴避的人心和社會政治變化。《基本法》鞏固了由港英殖民地政權繼承過來的行政型政府結構和政策思維,又同時把既有資本家及精英利益權力分配體制化,以地區直選為本的主流政黨(建制或泛民)卻無機會執政,更遑論培養治港人才。
於是產生多重結構性落差:以傳統行政型體制,去治理政治及利益多元的社會;以未受民意洗禮只靠中央授權的特首班子,去「行政主導」有地區民意及功能行業利益為後盾的議會政治;以延續及避險為上的行政思維,去應對急劇變化的社會經濟大環境。政府弱勢,加以行政立法拖拉、失去應有綱紀,經常議而難決,為既得及短期利益所束縛,又指揮不了多數黨派,政策落後於時勢需要,予民不勇於作為之感,因此才會令一些人緬懷過去港英改革的日子。
回歸20多年,香港一直受民主問題及政改爭議所煎熬。中央對政改雖有「8‧31」底線,但若不肯正視現有「港人治港」體制的缺陷,以為能吏就能治好香港(「港英能,我們為何不能?」),顯然低估了香港本土政治的複雜性。如不改革,特區就難以走出管治死胡同,不斷內耗,失去昔日敢為敢試的前進都會。香港之失,也是國家之失。
註:Peter Hartcher, A message to Hong Kong’sprotesters: there’s only one way you can win,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 3 September 2019。作者乃該報政治及國際編輯,長期批判中共,支持近期香港的抗爭運動。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