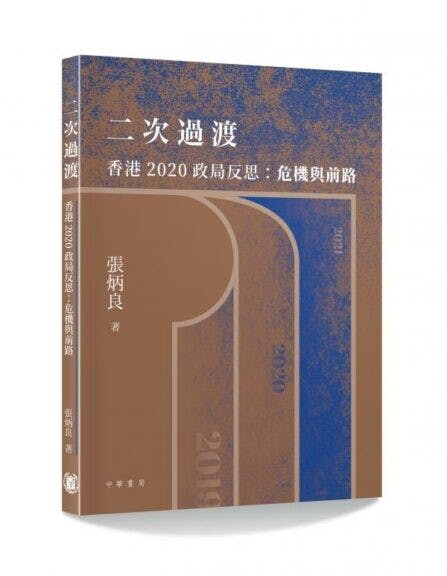續接前文:〈歷史轉捩點上的香港〉
第四,撕裂與仇恨加深。從2019年6月包圍立法會、包圍警察總部及個別政府部門的衝擊權力機關和不合作行動,以至七一當天衝擊及佔領立法會大樓、塗污特區立法機關權威象徵、展示港英殖民地旗幟等舉動去看,一些年輕激進抗爭者的行動,已非純屬抗議已經「死亡」的修例法案,也不止於所謂不滿林鄭月娥特首對民眾訴求缺乏「全面真誠的回應」,而是去到否定特區憲政秩序的地步,處處展現「癱瘓政府」的符號主義(symbolism),套用當時一位專欄作者所說,年輕人眼中香港未來是個謎,所以他們只能行動在當下,但求遍地開花。
社會分裂,「和理非」路線消亡
另邊廂,反黃的藍營及反對抗爭暴力化(「黑暴」)的民眾,也動員起來。721元朗事件後,警察被泛民主派和黃營定性為敵對的鎮壓力量(「警暴」、「黑警」),黃對藍、「黑暴」對「黑警」的鬥爭論述,籠罩整個社會,各行各業甚至公務員和專業人士之中,也以顏色定位,且延及經濟及消費領域(所謂「黃色經濟圈」、黃店對藍店), 撕裂與仇恨之深前所未見。
香港已不復一個平和及講求理性兼容 (agree to disagree)的社會。泛民主派支持者常標榜的「和理非」 (和平、理性、非暴力)已靠邊站。
第五,和解對話之路走不了出來。年輕抗爭者的激進舉動和激情,不單令全社會矚目,也吸引了全球各地的眼球和想像力,一時之間他們變成牽動事態發展的真正推手和「歷史主角」,甚至影響他地的社運模式,如2020年泰國的反政府抗爭。
本來不認同如此脫軌衝擊的一些「成年」抗爭者、公民社會及泛民主派人士,紛紛調整思想:「因為絕望,所以……」,客觀上也等於宣布了「和理非」路線的不濟甚至死亡。這的確是他們自己的結論嗎?這個轉變,影響了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對於事態嚴重性的評估。
2019年7月起,北京全面以「止暴制亂」及反對「港獨」和任何分離主義為綱,重整對港管治方針,而特區政府愈發依賴以警察去鎮暴和控制亂局。和解對話之路雖曾一度有點曙光,但始終走不了出來。
第六,當下香港,新世代的怨氣和憤怒,源於難以認同一個他們視為不公平、只傾斜於一邊的體制。社會經濟問題如房屋、就業及社會流動停滯,肯定是造成年輕一代看不到前景、容易激進化的部分因素,但是解決深層矛盾已不僅是改善他們的生活這麼簡單,因為他們持有的公義感及社會核心價值是既有體制未能足以反映。
而他們害怕失去的「香港」特色,也不是一些冷酷的 「你們怕什麼?」或「應走出香港,到大灣區去闖」般的言詞便可疏解得了。他們當中固然有擔心學業、事業甚至置業無望的問題,但是往深一層就算有了這「三業」,若他們認為失去心中仍可引以為傲的香港、失去了其所追求(也是官方及教育論述和上一 輩予其願景)的自由自主性時,則物質滿足又如何。當年輕一代感到體制是由他人主宰、城市空間(包括交通甚至購物)愈來愈為外人進佔時,其「保衞我城」便不只屬於單維的本土政治了。

一子錯滿盤皆落索
最後,政府管治表現,關乎制度、能力、判斷和領導質素,最終離不開體制問題。回歸近1/4世紀了,難道我們還看不到惡性循環、社會內耗的種種惡果嗎?當然,改革不易,但這不是不去改革的理由。內地在文革後,鄧小平曾說:「……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美國前副總統戈爾在90年代推行「政府再造」(Reinventing Government) 運動時,也曾說過:聯邦政府充滿被壞制度所困的好人。兩者道理相若。
由反修例運動演變為後來的全面政治對抗、街頭暴力、社會黃藍撕裂、仇恨文化蔓延至日常生活,當中既有政府處理危機失當的因素,致一子錯滿盤皆落索,也因九七回歸以來社會深層次矛盾所累積政治張力的總爆發,更有全球新地緣政治的衝擊(如美中衝突)。偶然加上必然因素,造成今天政治上覆水難收。《港區國安法》實施後,社會表面上雖然較2019年時平靜,但掩蓋不了深層的焦躁、不安與無奈無助感。
面對當前複雜及其來有因(即有其「路徑依賴」)的局面,可以如何解困突破呢?我並無即時見效的靈藥,但我知道,悲情只會滋長宿命感,仇視只會助長撕裂,敵對不能帶來信任,缺乏互信就難推動改革。要去再度出發,前提是準確研判當前局勢及深層次矛盾的成因,並能跳出過往的思考框架去探索其所以然。
在此關鍵時刻,面臨內外嚴峻挑戰,最大的風險是來自認知上和行動上與現實及其背後結構因素之間的落差。特區管治體制已明顯與時脫節,非改革不可,不能再諱疾忌醫。如何防止傷患惡化擴散,如何部署有利於改轅易轍式改革的條件,能否對症下藥,卻事關重大,欲速不達。
香港的管治更關乎一國兩制在回歸後21世紀國內新秩序及國際新形勢下的實踐問題。無論中央層面,或特區內政府及社會各界與政治光譜各方,是否都掌握到一國兩制應有的靈活性、兼容性、模糊性和創造性,正確看待香港之「異數」?如何促使「兩制」回復基本的互信,香港和內地都要深思與學習。
怎樣的香港才可在國家發展和國際大局中扮演關鍵角色,好讓港人尤其年輕一代足以自豪,重拾自信與希望,得以由回歸以來的內向、失落、悲情思維中逐步走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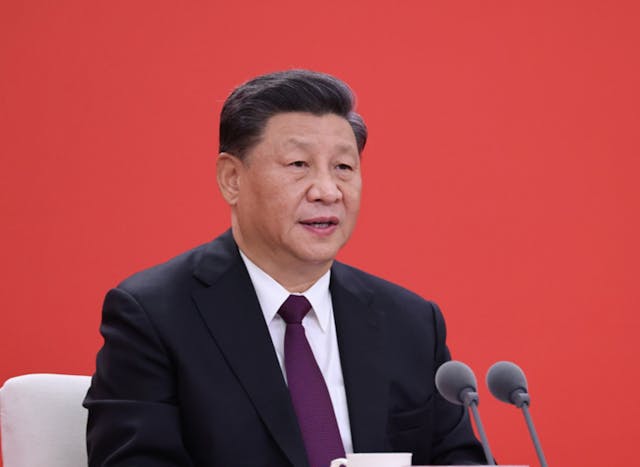
二次回歸的關鍵時刻
「二次回歸論」者指九七回歸,雖然體現了領土和主權的回歸 (國家官方表述是1997年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可是人心尚未回歸,如今有了《港區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強化國家意識,確保愛國者治港,從而由亂趨治,好讓人心歸向。
香港的確進入了新時期,但實事求是看,社會及政治深層次矛盾依舊存在,人心鬱結未解。要解結贏回民心,有賴對策得宜、主政者視野廣闊,又需自由兼容、求同存異的社會氛圍,這要求很大的努力和遠見。
2020年的香港,與1997年比較,隔了一個世代,社會環境、民情和全球局勢都已大為不同,國家也蛻變了不少,不可同日而語。一國兩制不能停留於九七前的設定,但也不會凝固於當今,未來仍會迎着種種挑戰前行,順逆變數或不比過去少,切忌一廂情願、單維認知。
現代治理,有若「園藝」(gardening),需細心栽培,古訓言 「治國如烹小鮮」,治港也一樣。人心回歸須基於良政善治及官民重建互信,此仍乃長路,非一蹴而就。故我以「二次過渡」識別當前關鍵時刻,視之為回歸後再攀新峰之始,本書也就以此命名。
當下香港,在此「二次過渡」之關口,究竟是處於最壞的時代,還是最好的時代(借用英國大文豪狄更斯〔Charles Dickens〕在其名著《雙城記》的開卷語),視乎我們的領袖及民眾何去何從。
一些身邊的朋友憂「香港已死」,這是何等悲情的申訴!我認為絕大多數港人(縱使當中政見不同),仍是和平理性、熱愛這個歷史異數城市的,他們不肯認輸,他們既害怕、焦慮,但也十分堅強。是這樣堅強不認輸的力量,一直在各種困難和逆境中支撐着香港不斷前進。

歷史轉捩點上的香港
我那一代(50後)的港人,見證了香港的現代化成長,成為舉世知名的自由法治之都,我們不會讓香港倒退。我不希望年輕人只因心感絕望而抗爭,或追求虛妄而迷失方向。為何不可以為希望而創造力量?如何締造希望,是香港朝野內外、跨政治光譜的所有領袖皆應致力之要務,也需要中央政府的支持。
新時代要求新思維、新出路;窮則變,現在是求變順變的關鍵時刻。能逾越此關,一國兩制可找到新台階;過不了此關,「香港」的萎縮會成為自我應驗的預言。
我在學生時代屬於思想前衛的活躍份子,曾積極參與學運和社運,打從上世紀80年代便涉足香港九七前途及回歸祖國的討論和行動(包括起草《基本法》時的辯論),對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制訂有所理解和期盼,亦明白歷史契機和制度局限交集下特區之旅的不尋常。
當我身邊不少朋友(包括曾並肩作戰的早期民主派)紛紛轉向悲觀無奈,我仍不肯認命放棄。我一直在民間與建制、議會與政府、學術與政治之間來回游走,深明事物之變,不盡必然,但也非毫無可為。極端樂觀或極端悲觀、虛妄想像或向現實低頭,皆非我杯中茶。
撰寫本書時,我疏理了過去近兩年來所發表評析時局文章的觀點,作系統化討論,希望為香港處於當前歷史轉捩點,留下思想足印和時代見證。一代人做一代事,世界最終是屬於新一代的,就讓他們踏着前人的經驗和走出來的路徑,再闖新天。

作為對香港的政治反思,本書第一部分共三章,從2019年修例說起,先講述移交疑犯逃犯的國際一般做法和基本準則,以及特區政府原本修例的緣由和範圍,當中的複雜性和爭議性所在,然後分析為何修例竟釀成一場政治風暴,繼而探討為何一次危機,因處理失當、落後於形勢而演變成政治災難,令社會以至國家付出沉重代價。
第二部分進入對特區管治的多方面剖析,分為四章:特區管治的根本結構性難題與缺陷;一國兩制下的不自在與張力;新世代的失落與焦躁;以及新冷戰與國家安全衝擊下香港被北京視作國安短板等最新課題。
第三部分共兩章,探索香港及一國兩制的前路,針對當前一些本地和海外評論擔心「香港不再香港」,檢視香港的強弱機危,提出如何保持香港的特色,並思考可怎樣亂後重建。最終的結語章綜述回歸歷程,如何面對2047的所謂一國兩制大限,究竟是歷史的終結還是見證一國兩制持續化的新里程碑。這既要看國家長遠的發展,也視乎香港能否發揮「國家所需,香港所長」的作用,以及其制度和軟力量是否仍為世界所重視。
本書得以出版,全賴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黎耀強副總編輯的鼓勵,及其團隊的支持。在撰寫過程中,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曾提供一些資料蒐集的協助。另外特別感謝,香港《信報》和《明報》慷慨同意我在書中使用我曾在兩報發表的一些文章的內容和觀點。
新書簡介:
書名:《二次過渡──香港2020政局反思:危機與前路》
作者:張炳良教授
出版社:中華書局
出版日期:2021年7月
《二次過渡──香港2020政局反思:危機與前路》序言二之二
延伸閱讀:〈歷史轉捩點上的香港〉(序言二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