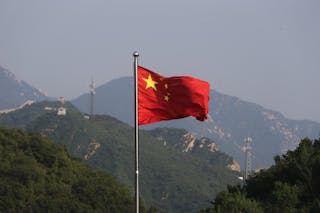
許多國家都有立法規定使用國歌的場合和方式,以及在奏唱國歌時在場人士的行為舉止。

香港政治人才從何而來?如果仔細一看,香港的管治人才似乎都是分崩離析的。

維護香港司法獨立和法治精神不能只靠有法律條文保障的制度,和政府依法執法的權力,還須靠市民。

這次高鐵一地兩檢方案的推銷手法,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為何政府推行政策時必須全面準備主動出擊。

由於近年貧富不均日益嚴重,社會主義平等與均富的要求呼聲愈來愈強烈。

年輕人關心社會的確值得支持鼓勵,但現在的上訴及判決要打擊的,只是「違法」的一部分,絕非追求公義之心。

我認為要有兩制的對立統一,才能有生命力、讓香港具有獨特的地方及對國家有獨特的貢獻。

澳門很多年前就用一套最簡單思維,就是用錢解決問題,年年派錢,個個開心。

如今香港的傳統建制力量,從上到下都不想融入大灣區的話,就算是中央命令,特區也有各種對策。

香港的科研與教育,除了急功近利的數量化增長,看不到有什麼實質的進展。

佔中的後遺症正逐步顯現,泛民宜及早檢討戴耀廷的那套對泛民在總路線方面的影響。

歷史中的光明與黑暗,現實社會的改革與僵化及敏感政治話題,都不應刻意迴避。

高鐵的低回報已引起市民關注,持續擴建鐵路網會否是一個聰明的投資?

觀看境外小醜的表演有一段時間了。本以為我國的主流媒體會有明確表態,很遺憾,中國的知識精英集體啞然了。

法治是香港最後一道防線,如今已是風雨飄搖。這是香港當前最大的警號。

對政府有不同看法的人,對官員政治動機這問題有不同的臆測。

鄧小平南巡是一個時代拐點,中國的改革開放是空前大步邁進。

即使不相信律政司,也相信那些法官吧?年輕人本來就知道這一點,才開始衝擊。理性地看,那是「求仁得仁」。

我們要知道,在蘇格拉底受審時,在甘地絕食時,在馬丁路德金被暗殺時,一樣有許多人在旁邊嘲笑在背後擲石。

不要爲了要打倒一個制度,而自己慢慢變成了要打倒的對象。

令港人迷茫的,是兩者之間的鴻溝十分清楚,解決的方法卻沒人知曉。

市民便會質疑司法是否已成為依法維穩,罔顧民情的行政工具,這將是對香港法治的最大破壞。

明明說明公民抗命,以身試法,甘受牢獄之苦。但到頭來面對判刑上訴的結果,心感不忿!

從我國利益出發,我不想見到美國轟然塌下去,情感上我也不喜歡這情況出現。

「法治」似乎只是在「治」某些特定的對象,而「治不了」某些惡行。

也許有些人特別喜歡陰謀論,對一地兩檢有情意結,在杯弓蛇影的心態下,才會一葉障目,盲撑林子健。

這樣下去,法官會愈來愈害怕輿論壓力。群眾壓力同來自北大人或權貴的壓力,一樣可怕。

這班人卻自以為真理在手,可以指點江山,非要全社會走他們心目中的必由之路不可。

通識教育和中史科的相關研究、教學、教材,必須尊重事實,讓學生了解真正的歷史,並建立獨立思考能力。

政府必須承認無奸不商,這個世界上沒有太多個微軟的蓋茨和股神巴菲特可以捐出大部份身家作為善事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