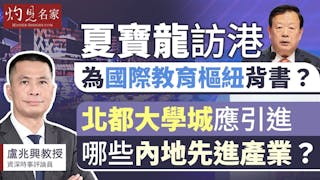信不信由你,叫人某君、某甲、路人乙和「那個人」的稱謂,幾千年前就有了,不信?且看幾個例子。
一、某日孔子同生徒經過石門(魯城外門),那位晨門(早更看門更夫),知道是孔子經過,竟然很不禮貌地對孔子說:「是那個明知辦不到,而還硬着頭皮去幹的那個人嗎?」(「是知其不可而為之者與?」,見〈憲問‧十四〉)。
二、「不知何一男子」,是西漢中、晚期至東漢初期常用的口語,在《居延漢簡》裏就常常有這樣的一句話。例如:「不知何男子」(見《居延漢簡釋文》,頁173、175);《漢書‧王莽傳‧中》說:「不知何一男子,遮臣車前。」而最離譜的,則是王充《論衡‧實知篇》之托名孔子偽讖:「孔子將死,遺讖書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謂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後,秦王兼吞天下,號始皇,巡守至魯,觀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
三、東漢之邯鄲淳,就是那位作〈孝女曹娥碑〉,而被蔡邕譽為「黃絹、幼婦、外孫、虀臼」-絕妙好辭(辤,見《世說新語》),而文、謎因而得留存史冊的博士給事中。他又著有《笑林》一書,以調侃庸愚,藉資一粲;今文多佚散,但所遺之二、三十則中,亦有某甲、有甲兩篇:(1) 某甲(某人也)夜暴疾,命門人鑽火。其夜陰暝,不得火,催之急。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太無理,今暗如漆,何以不把火照我,我當得覓鑽火具,然後易得耳。」-孔文舉(融)聞之,曰:「責人當以其方(道理)也。」(2) 有甲(某人也)欲謁見邑宰(縣令),問(縣令之)在右曰:「(縣)令何所好?」或語曰:「好《公羊傳》」(公羊高所撰,解釋孔子重寫的《春秋》;《公羊傳》、《左傳》和《穀梁傳》,合稱為《春秋》三傳)。
後入見,令問:「君讀何書?」答曰:「惟業《公羊傳》。」「(令)試問(根據《公羊傳》所說)誰殺陳他者?」(背景是:縣令故意把陳佗說成陳「他」,來考有甲對《公羊傳》的認識。陳佗是陳國陳文公的兒子、陳桓公的弟弟;桓公死,殺太子免而自立。《春秋·桓公六年》錄有「蔡人殺陳佗」條,《公羊傳》解釋說:「蔡人殺陳佗,陳佗者何?陳(之)君也。……淫于(欺凌)蔡人,蔡人殺之。」)
甲良久對曰:「平生實不殺陳他。」令察謬誤(知道有甲胸無點默),因復戲之曰:「君不殺陳他,請(問)是誰殺?」(有甲)于是大怖,徙跣(連鞋子都不穿了)走出。人問其故?乃大語(聲)曰:「見明府(縣令),便以死事見訪(以命案相詢),後直不敢復來,遇赦(要等到大赦時)當出耳。」
疑似人物,疑似新聞?
仔細想一下,這都是謔人的稱謂。殖民地時期的香港媒介——尤其是印刷媒介,最怕犯誹謗罪,故當處理社會新聞時,例如,打架事件,對於涉事人物、武器、打鬥受傷經過及原因,都必小心翼翼,以免犯上誹謗官司,久而久之,就形成之一種無解的獨特報道方式、詞項和文體。例如,涉嫌之人,用「疑人」,任何物件,都加上「疑似」兩字;報道打架時說:「混亂中,一名男子手持一把疑似手槍物件向受傷男子射擊,事發後,疑人逃逸無蹤。…….」有時,也真令人看得有如丈二金剛摸不着頭,早有識者詬病之。
但,也不知何時開始,台灣報紙在處理被報道的人名上,卻「偷工減料」,大做手腳。中國人姓名,以三字居多,報章卻喜縮為兩字——除姓氏之外,一律「加上」固定的單名,男的稱男,女的稱女;例如,名叫李大文(虛擬)的男子,新聞中就稱為「李男」;名叫張心(虛擬)的女士,新聞中就稱為「張女」。李男,不過比李大文三個字省去一個字,兩字總筆畫卻是一樣,而張心同張女則不但字數一樣,女字比心字亦只不過少了一畫,實在看不出將人稱男道女,到底有甚麼好處?
相反,這正是醜陋的「返祖現象」,是報紙輕視報道中人物的口氣,堂而皇之地公然侵犯人類姓名的尊嚴(這不同於英文簡稱,如 Kenneth,可簡稱為 Ken),令人不忍卒讀。即使是一條狗,通常也都叫全名;例如,布希的愛犬叫把弟(Buddy),它就可能聽不懂人叫它「把」(Bud)。不知道經常自我期許為社會良心的報業,是否可以冷靜的檢討一下,請撰稿者稍為留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