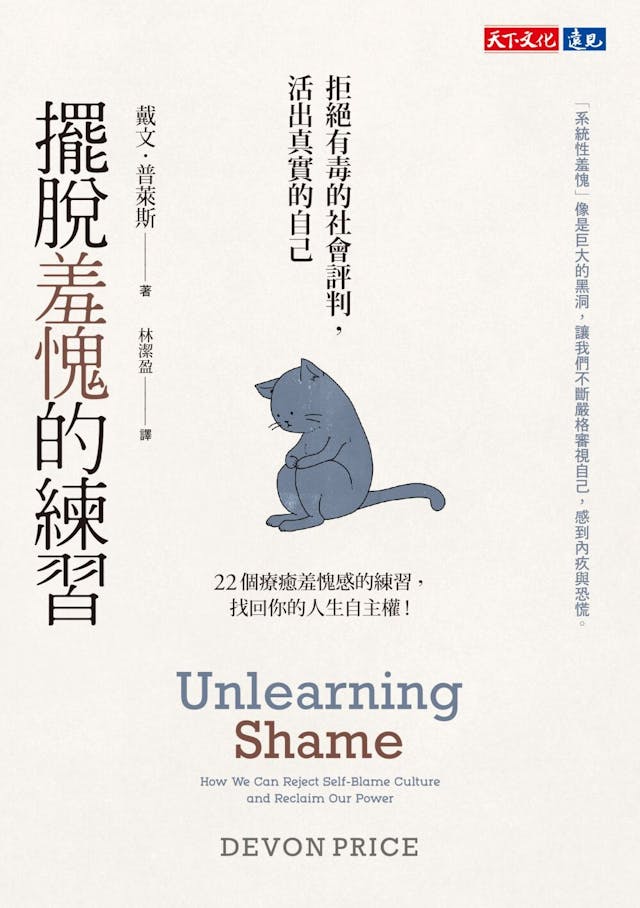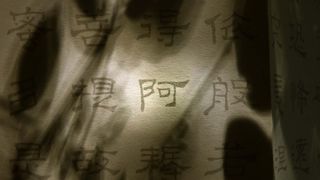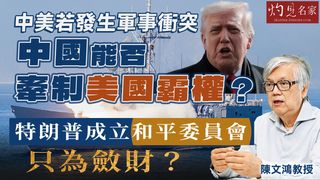正如許多人一樣,我也深受「系統性羞愧」(Systemic Shame)所苦,這是一種強烈的自我厭惡信念,讓我相信自己遭遇的一切都是咎由自取,唯有依靠個人的善良與恆毅力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羞愧是一種相當正常,但會令人不舒服的情緒。哲學家對它的運作機制似乎深感興趣,所以我們可以輕易在文化及歷史背景中,看到許多關於羞愧的細膩描述,包括感到羞愧時的內在感受及相應的外在表現。簡單來說,羞愧是一種感覺,我們不僅覺得自己做了錯事,甚至覺得自己本質上就是壞的、具有某些非常糟糕的核心特質,以至於必須將自己隱藏起來。感到羞愧的人通常缺乏動力,會盡量避免接觸他人、覺得自己無能為力,他們就像憂鬱或嚴重倦怠者一樣缺乏活力及專注力,因此往往需要更多時間與社會支持,才能慢慢重建起值得被愛的自我價值感。
「系統性羞愧」是一種情感創傷
羞愧可能會對我們造成很大的傷害,但「系統性羞愧」所帶來的巨大傷害,往往比我們做出殘忍或有害的事所帶來的悔恨還更深刻,這是因為「系統性羞愧」不只是一種情緒,還是一個關乎誰值得獲得幫助、誰應該為所受傷害負責的信念系統。羞愧讓我們覺得自己本質上就是壞的,這已經是一種很可怕的感覺;而「系統性羞愧」則告訴我們,整個群體都是壞的。它讓我們透過選擇與身份認同,時時刻刻向他人表明,自己屬於值得救贖或天生邪惡的群體。
當我們經歷一般的羞愧時,可以透過重新審視自身行為、彌補過失、投入自我成長來加以修復。然而,「系統性羞愧」就像是日復一日被重新撕裂的傷口,無論我們是否嘗試改變,無論我們多麼渴望能愛那個真實的自己,它都依然存在。無論我們投入多少努力、多麼認真體現德行,「系統性羞愧」始終盤旋在我們的文化之中,告訴我們自己是懶惰、自私、噁心、不值得信任的人,讓我們覺得生活中遭遇的一切問題,全都是咎由自取。

當一個邊緣人必須為自己所受到的壓迫負起所有責任,「系統性羞愧」將帶來一種不知所措的絕望感。當我們責怪自己未能採取「足夠」的行動,來對抗跨性別恐懼、種族歧視、勞工剝削、全球氣候變化或流行性疾病等不公正的現象時,「系統性羞愧」也會讓我們付出沉重的情感代價。當我們認為必須靠個人行動來改善根深柢固的不平等問題,改變購買與消費行為來彰顯我們的美德,並且不該接受任何幫助時,就意味着我們正在遭受「系統性羞愧」的折磨。「系統性羞愧」幾乎無所不在。每當我們講到對彼此的虧欠,或是提到真正創造一個更美好、更具社會正義的世界可能是什麼樣子,都可以感覺到「系統性羞愧」的影子。
「系統性羞愧」是一種揮之不去的情感創傷,一種關於世界如何運作的心理認知,同時也是一種會讓我們心煩意亂、快樂不起來的破壞性意識形態。「系統性羞愧」與清教徒的「道德是簡單且絕對」信念密切相關,也與美國人長久以來簡單又粗暴的認為「每個人都應該成為獨立個體」的價值觀緊密連結。早已根植於我們的文化與歷史之中,出現在政治辯論、政府公告、廣告、教科書、我們被要求參加的研討會與培訓、我們喜歡的電影及電影討論中,甚至出現在我們如何判斷自己與朋友行為的方式中。
「系統性羞愧」主張,每個人唯有透過持續努力付出,並始終做出「正確的」決定,才能帶來有意義的改變。它告訴我們,身心障礙者不能把自身不利條件當成落居人後的「藉口」,貧窮者應該發憤圖強,靠自己逆轉命運。它告訴女性,只要學會勇於表達自我並勇往直前,就能克服工作場所的性別歧視;它還告訴黑人,只要注意修飾自己的語氣,就能避免職涯中的種族歧視。當一名黑人女性覺得很難同時遵循以上兩個相互矛盾的建議時,「系統性羞愧」就會把問題歸咎於她不夠堅強,或者轉而指責她太過偏激。

「系統性羞愧」讓我們相信,全球流行病是自私的人造成的,並不是因為企業的跋扈與政府的疏失。它大力鼓吹大規模槍枝暴力事件源自壞人或精神異常者的隨機行為,與白人至上主義或其他仇恨運動的興起無關。它還告訴我們,我們必須嚴守某些個人習慣與某種消費方式,因為我們所採取的每一個行動都帶有強烈的道德色彩,世界的命運取決於我們所做的每一個決定。無論我們多麼關注他人與社會問題,它依舊會讓我們相信,我們並未落實這些價值觀、沒有投入足夠資源、做得始終不夠多,或是仍然不夠努力。
「系統性羞愧」讓我們陷入困境,就像我經常感覺到被困住一樣,我討厭自己,只能拚命工作以贏得生存的權利,而且從不相信有人會真的支持或關心我。我知道我不是唯一一個這麼想的人。這種思考方式會阻礙人際之間的有效對話,讓我們無法聚焦於想要達成的社會變革,並一同思考該如何從系統層面促成這樣的變革。
以下幾種跡象,顯示你可能正受到「系統性羞愧」所困擾:
- 你總是透過那些對你不認可的人的視角,來嚴格審視自己。
- 你會花很多時間反覆思考過去的決定,即使是那些不太重要的決定。你會對那些決定感到懊悔,認為當時如果能做出「正確的」選擇,事情的走向可能會有所不同。
- 唯有在獨處時,你才能感到放鬆、真正做自己。不過即使在這樣的狀態下,你依然不允許自己有某些想法與感受。
- 你隨時都保持警覺,擔心旁人會根據你的身份、外貌、甚至是過去經歷,而對你產生刻板印象,並小心的監控自己的行為,以免讓這些刻板印象成為事實。
- 你強迫性的不斷接收世界各地令人感到不安的負面新聞,但你並沒有因此感受到知識所帶來的力量,反而因此感到內疚與恐慌。
- 你很難想像未來的你能感到滿足,無法肯定你的人生具有價值。
- 你覺得自己背負着沉重的義務,但你所做的一切似乎全都徒勞無功。
- 你很難相信有人會真正欣賞及關心那個「真實」的你。
- 你對自己的預設態度,是不信任與厭惡。
- 你試着獨立完成所有事情,並認為一旦放慢腳步或接受幫助就等同於失敗。
無論從哪個方面來看,「系統性羞愧」都是非常普遍的問題。從氣候變遷到性別歧視,從醫學上的肥胖恐懼症到全球流行病,幾乎所有社會議題都觸及「系統性羞愧」。一個人遭受的苦難愈多,社會的經濟體系與公家機關就愈想讓我們相信,這一切都是咎由自取。但我幾乎可以向你保證,即使你不覺得自己受到壓迫,這種意識型態也會對你的生活造成影響,因為我們所有人的生活都無法避免受到資本主義與環境退化等力量帶來的傷害。「系統性羞愧」讓我們無法意識到,自己與生活在這個星球的大多數生物一樣,都在為這些問題苦苦掙扎。「系統性羞愧」讓我們無法團結起來,要求現有系統變得更好,或是一起努力建立起替代系統,而是讓我們生活在恐懼與自我厭惡之中,拉開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書籍簡介:
書名:《擺脫羞愧的練習:拒絕有毒的社會評判,活出真實的自己》
原文書名:Unlearning Shame: How We Can Reject Self-blame Culture and Reclaim Our Power
作者:戴文.普萊斯(Devon Price)
譯者:林潔盈
出版社:天下文化
出版日期:2024年12月
作者簡介:
戴文.普萊斯(Devon Price),社會心理學家、教授、作家,同時也是一名自閉症患者。他的研究曾發表在《實驗社會心理學期刊》、《人格與社會心理學期刊》和《正向心理學期刊》等;文章散見於《金融時報》、《赫芬頓郵報》、《洛杉磯時報》、《石板雜誌》、《雅各賓》和《商業內幕》、文學網路媒體LitHub,以及美國公共電視網(PBS)、美國國家公共電台(NPR)、美國新聞網站MSNBC和英國廣播公司(BBC)。著有《揭開自閉面紗》(Unmasking Autism)一書。現在是芝加哥羅耀拉大學(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助理教授。
譯者簡介:
林潔盈,台灣大學動物學學士,英國倫敦大學學院博物館學碩士。現為專職譯者,譯有《蘋果進行式》、《綠色星球》、《博物日本》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