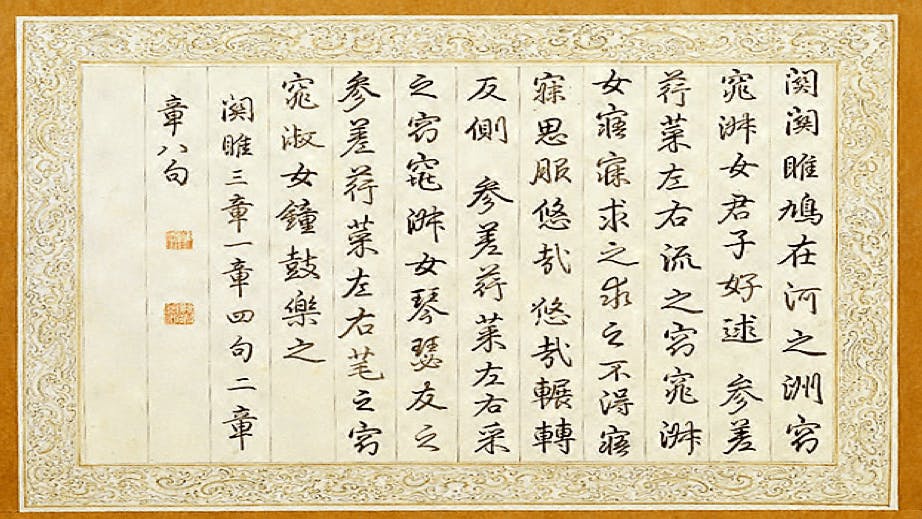在中國文獻典籍中,對中國歷史影響最為深遠者,莫過於「五經」。「五經」中影響最廣,感人最深者,則莫過於《詩經》。故《詩序》說:「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正得失」,言其倫理道德功能;「動天地,感鬼神」,指其情感功能。正人之行、動人之心的雙重功能,確立了《詩經》在中國文化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然而我們今天閱讀《詩經》,卻感受不到這兩種功能的存在,這原因便在於觀念上的差距與價值取向上的變化。要想走近《詩經》,還須先破除觀念形態上的障礙。
恢復了《詩經》的文學真面目
第一須破除的是 20 世紀對《詩經》性質的認定。幾乎所有的中國文學史著作,以及語文教材、文學通俗讀物,對《詩經》都給出了這樣的概念:《詩經》是中國最早的一部詩歌總集。這似乎已成為天經地義。這個結論被認作是 20 世紀《詩經》研究的最大貢獻。因為歷代都把《詩經》當作「經」來對待,只有 20 世紀的文化運動,才所謂「恢復了《詩經》的文學真面目」。
這個觀念最大的問題是,忽略了《詩經》對於建構中國文化乃至東方文化的意義。我們不否認《詩經》的本質是文學的,但同時必須清楚《詩經》的雙重身份,她既是「詩」,也是「經」。「詩」是她自身的素質,而「經」則是社會與歷史賦予她的文化角色。在2000多年的中國歷史乃至東方歷史上,她的經學意義要遠大於她的文學意義。《毛詩序》說:「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孔穎達《毛詩正義》說:「夫詩者,論功頌德之歌,止僻防邪之訓。」朱熹《詩集傳序》說:「《詩》之為經,所以人事浹於下,天道備於上,而無一理之不具也。」其在中國文化史上之地位由此可見。同時她還影響到了古代東亞各國。如日本學者小山愛司著《〈詩經〉研究》,在書之每卷扉頁赫然題曰「修身齊家之聖典」「經世安民之聖訓」等。朝鮮古代立「詩」學博士,以「詩」試士。他們都以中國經典為核心,建構着自己的文化體系,由此而形成了東亞迥異於西方的倫理道德觀念與文化思想體系。這是僅僅作為「文學」的《詩經》絕對辦不到的。作為「文學」,她傳遞的是先民心靈的信息;而作為「經」,她則肩負着承傳禮樂文化、構建精神家園的偉大使命。一部《詩經》,她承載着的不僅是幾聲喜怒哀樂的歌詠,更主要的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精神與心靈世界;一部《詩經》學史,其價值並不在於其對古老的「抒懷詩集」的詮釋,而在於她是中國主流文化精神與主流意識形態的演變史,是中國文學批評與文學理論的發展史。如果我們僅僅認其為文學而否定其經學的意義,那麼,不僅無法理解《詩經》對於東亞文化建構的意義,而且也無法解釋東亞的文化與歷史。
錢穆先生說:「《詩經》是中國一部倫理的歌詠集。中國古代人對於人生倫理的觀念,自然而然地由他們最懇摯最和平的一種內部心情上歌詠出來了。我們要懂中國古代人對於世界、國家、社會、家庭種種方面的態度觀點,最好的資料,無過於此《詩經》三百篇。在這裏我們見到文學與倫理之凝合一致,不僅為將來中國全部文學史的淵泉,即將來完成中國倫理教訓最大系統的儒家思想,亦大體由此演生。」(《中國文化史導論》,商務印書館 1996 年版,第 67 頁)錢先生對《詩經》的這一把握應該說是非常精確的。「文學與倫理之凝合一致」,更好地說明了《詩經》的雙重價值。從「倫理」的角度言,《詩經》中所運載的觀念形態,可以說是中國文化精魂之所在,其之所以有「正得失」的功能,有「止僻防邪」的社會功效,原因正在於此。如果拋棄了這個精魂,而只關注其「歌詠」,關注其所謂的「文學本質」,實無異於捨本逐末。而要想正確認識《詩經》的價值,走近《詩經》,就必須糾正 20 世紀形成的這種偏見,從「文學與倫理之凝合」的角度,把握《詩經》的真精神。

破除《詩經》作為「古典文學知識」的觀念
其次須破除的是把《詩經》作為「古典文學知識」的觀念。20 世紀在文學研究領域出現了許多新觀念,其中影響最深者有三:一是「唯物論」,認為文學是一種客觀存在,它有其自身的規律,文學研究就是要研究文學的運動規律,用規律來指導當下的創作;二是「進化論」,認為文學是不斷進化、發展的,中國文學史就是中國文學的發展歷史;三是「遺產論」,認為古代文學是古人留下的一筆值得繼承的文化遺產,有了這筆遺產,可以使民族文學寶庫更豐富,成為我們今天創作的知識資源。在這三種理論的觀照下,《詩經》便成了一種古典知識。這種「知識」,其意義重在認識上,即認識中國文學發生期的詩歌形態,認識賦比興對後世詩歌藝術的影響,認識其在中國文學發展史上的位置,同時幫助理解和閱讀古典文獻,等等。許多人閱讀《詩經》是為了掌握知識,獲取古代信息,《詩經》的精神意義在這種觀念中喪失殆盡。顯然,這大大地影響了對《詩經》的正確、全面的接受。當然,我們並不是說這三種理論不好,而是說不能僅以此來認識《詩經》。在這種觀念下,所發現的只能是《詩經》作為客觀存在的意義,而難以把握其內在精神。要知道,文學中有知識,但文學不是知識,她是一種生命的存在形式,有思想,有情感,有靈魂。對於她,不能用對待知識的方法去分析、把握,更重要的是要用心靈去感悟,去感知她作為精神存在的意義。
破除「創新」觀念
第三須破除的是「創新」觀念。「創新」是我們這個時代的一個關鍵詞,在許多方面確都需要創新。但對人文學科來說,更需要的是「務實」,是「守正」。在「守正」的基礎上「出新」是可以的,而不能刻意去「創新」。只有在原有基礎上自然而然生出的「新」,才是有生命力的。孔子說「述而不作」,「述」便是「守正」,「作」便是「創新」。「述」比「作」難,因為只有全面地把握前人的成果,才能準確地「述」出來;而「作」則可以不管別人怎麼說,自己另搞一套。當下在人文學科中,「創新」意識過於強烈,好像「新」就是好的,「舊」便意味着沒有意義。在這種意識支配下,有些人不從正路上去理解《詩經》,也無心去瞭解前人研究成果的合理性,而是銳意求奇、求深,近於「腦筋急轉彎」的方法,於是觀之則「新說」叢出,按之則無一能落到實處。這些人「創新」的目的,不是為了解决問題,而是為了出成果,寫文章。一般讀者不能辨其是非,只是覺得新奇便好,奇便能刺激自己對知識的興趣。這樣自然很難把握《詩經》的精神實質,也不可能有耐心去領會《詩經》的真正意義。
總之,「詩歌總集」觀念關注的是詩的藝術形式,「古典知識」觀念關注的是《詩經》中的文化知識信息,「創新」觀念關注的是自我表現,其目光投射皆是外在於《詩經》的東西,而忽略了詩歌的內在精神。只有清除了觀念上的這些障礙,才有可能走近《詩經》。
繼承前人閱讀《詩經》方法
就具體閱讀方法而言,前人有不少值得我們繼承、學習的成功經驗。首先最重要的一個基本原則,就是孔子所提出的「思無邪」的讀《詩經》方法,即要從正面理解詩意,不能想歪了,想邪了。《詩經》是中華文明大廈的支柱之一,她與大廈的存在是聯繫在一起的,如果她歪了,那就意味着大廈傾頹。
其次是縮短與《詩經》的時間距離。也就是說,在觀念中,不要把她當作古詩,要看作就是自己或身邊人作的。即如朱熹所說:「讀《詩》,且只將做今人做底詩看。」「讀《詩》正在於吟詠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詩,自然足以感發善心。」「千古人情不相違」,縱然《詩經》是數千年前舊物,事態萬殊,而人的情感反應則與今人無別。在略檢注解、疏通大意的基礎上,把她的意思品讀出來,而後與自己及身邊、眼前的人、事、物聯繫起來,其中的道理、情感自然會汩汩流出,使自己進入情景之中,去體會其心靈的脈動。在這種情景下,你可能會把外在的什麼賦比興之類統統淡化,而感受的是她的精神力量。
其三是靜心平讀,反覆涵泳,不可有絲毫私意摻雜。朱熹說:「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胸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措置,務自立說,只恁平讀着,意思自足。須是打迭得這心光蕩蕩地,不立一個字,只管虛心讀他,少間推來推去,自然推出那個道理。」朱熹曾批評人說:「今公讀《詩》,只是將己意去包籠他,如做時文相似,中間委曲周旋之意盡不曾理會得,濟得甚事?」(上引皆見《朱子語類》卷八十)這就是說,不能把自己的意思強加在詩上,而要通過反覆涵泳,讓詩意自然流出,與自己的情感、思想相融匯。王陽明《傳習錄》中有訓蒙的《教約》,他說:「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王陽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2 年版,第89頁)
這是讓《詩經》的精神匯入自己血液的一種方法。
前人的這些寶貴經驗,在今人看來可能已經不合時宜。原因是 20 世紀西方學術思想的輸入,徹底改變了中國學術原初以「修己」為第一要義的治學方向,而代之以知識開掘為第一目的。於是《詩經》由原初的鮮活的精神生命,變成了凝固的古典知識,其正人之行、動人之心的雙重功能也隨之喪失。同時學術界也出現了學術與人格分離、學術與人生分離的現象。這不能不引起我們的深思,也不能不引起我們對古典的閱讀方法的重新呼喚。
新書簡介
書名:《怎樣讀經典》
作者:王寧、彭林、孫欽善等
出版社: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9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