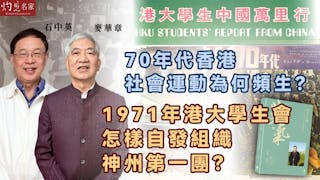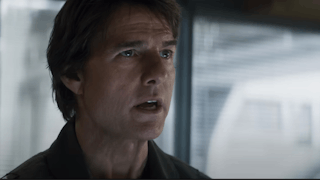編按:2017年5月27日,城大公共政策學系助理系主任兼高級特任講師張楚勇博士擔任「周末時事講堂─城大公共政策、政治、哲學公開講座系列」講者,以主題「政治是可行的藝術?──『一國兩制』的例子」發表對政治的看法,內容豐富,本社將分四篇刊出,以饗讀者,第三篇演講內容如下:
什麼是公共事務?
什麼是公共事務?這是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之前提過國家本身的中文含義,究竟是國還是家?以前中國不區分兩者的分別,直至經歷船堅炮利西方侵華的歷史,現代概念出現後,中國人才可開始關注國與家的分別。事實上,即使西方在探索公共與私人區分的過程中,也是十分複雜,因這議題本身不容易界定。整體來說,什麼是公,什麼是私,是有不用的方式去思考。如果沒有私人領域,所有東西都是公共的,這就是全能政府,無所不包。相反,如果全部都是私人事務,沒有公共領域的話,就沒有政治,那麼不是世界大同便是世界大亂,同樣是十分危險。在這兩極端之間,存在着不同的方式,視乎我們對不同政治理念和信念的解讀。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包括︰第一種是由政府去界定──當政府決定什麼該管時,全由它話事;當政府決定不管,把事務留給市場、私人機構或非政府組織管理,便成為私人範圍。但問題是,究竟香港城市大學是屬於公還是私?大學有55%是受政府資助,這是否代表大學老師有55%是公家,而45%是私家?這都不能算得很清楚,而一般非嚴謹的學術書都對此沒有清晰的定義與區分。
另一種界定來自德國的思想家哈貝馬斯(Habermas),他提出了一個重要的理念──公共空間(Public Sphere)。如果仔細閱讀,哈氏的理論背後建基於17世紀大哲學家康德的整套哲學。根據哈貝馬斯的講法,公共空間屬於共同的規則,發揮社會整合的作用,尤其是人們自我制定的共同規則,以管理共同的行為和標準。這些公共空間,很多時很大程度上是屬於政治空間。哈氏最初關注的公共空間,是與公眾輿論與溝通有關,後來再伸展到法律等層面。哈氏認為如果我們在共同規矩內,通過某種方式,經大家同意和審視後,再制定出管轄和影響大眾活動的標準,這通常是法律,是屬於公共層面。相反其他的領域是屬於私人,不需要共同決定,只依各人的喜好運行。

第三個界定來自19世紀自由主義大師彌爾(John Stuart Mill),其理論在中國比較著名,因嚴復先生在百多年前曾翻譯其著作《論自由》。彌爾提出了幾個重要的講法,其中在《論自由》一書中,他認為他找到了一個準則是可決定政府的職權。彌爾認為,當人的行為如果傷害影響到他人,政府才有理由去干預,否則政府是絕無理由去干預。如果某人或某一班人不傷害他人,或他/她們心甘情願下互相同意而作出不傷害其他人的行為,都不應受政府干預。從某個意義來說,以彌爾的自由主義理論進一步引申,今天關於成人間自願的性虐待行為、同性婚姻、色情或亂倫等爭議是否應該不受政府干預,道德的介入應減至最低?彌爾同時又是效益主義或功利主義者,效益原則和他在《論自由》中論述的傷害原則是否一致是有爭議的,在此我們不去討論。傷害原則,即是一些行為在別人不願意下影響傷害了他人時,政府及公權便有理由去干涉;相反如果沒造成傷害,或這種傷害是雙方你情我願的,政府便不應干涉。以賭錢為例,即使賭徒輸得傾家蕩產,這只是她/他個人的事,公權不應干涉。又例如在繫安全帶上,乘客皆有個人自由選擇,公權不應作家長主義式(parentalism)干預。同理,自由主義者亦會反對強制性公積金,因政府不應強制個人的退休安排和自由。所以人的行為所產生的公眾效果,如果沒出現傷害他人的情況,政府不應該管,只有在出現傷害他人時,政府才有權去管。
另一種界定則與自由主義唱反調。根據道德主義者的看法,由於人有道德理想,追尋某種的道德生活是十分重要,所以反對同性婚姻等主張,認為政府需同時管轄私人道德的範疇。相反,自由主義者不同意公權對道德介入,認為法律與道德需分開,法律不應該追尋道德的目標。
關於道德主義與自由主義之間的爭持,如果是自由主義式的秩序,會認為道德並不是法律的範疇,只有法律的範疇才是政治的範疇。而道德主義者則認為道德社群與政治社群分不開,講政治同時要講理想與對錯,追求完美以達至道德理想。如儒家提出「修身、齊家、治國」後的理想是「平天下」,追求不可停在中間,故道德主義認為政府的角色是幫忙推進社會到至善的地步。
另外,除了以道德與法律界定公私之別外,自由調協的市場制度與公權干涉的制度也對政府職權有不同的看法。干涉的制度由政府執行,強調所有集體決定需要理性地由強制性原則支持,否則會秩序大亂。例如如果沒有強制性要求市民交稅,人們難以自願遵行,令政策難以施行。可見人類社會存在不同的秩序,有些秩序需要政府強制性介入才可運行,如殺人犯罪需及時制止和懲罰。但自由交易並不一定需要受強制性干預,市場可自由運作,投資者賺蝕都屬自己的事。因此秩序的劃分可分兩種,一種是由政府管轄的強制性秩序和手段,另一種是自由市場的自發秩序,如交友結婚、貿易買賣、升學等是屬於自由自主秩序,不需政府監管也會自動出現。如果政府監管反而是干涉,因個人婚姻選擇與政府無涉,與全能政府理念不同。因此,從這意義上分析公與私的界定,公是指非要用強制性手段不可的範疇,餘下可自由運作的便是私。
最後,關於公私領域的界定,一些比較新穎的理論會將政治說到無所不包。尤其是文化批評式及女權主義的理論認為,人類文化幾千年以父權為主,從出生到死亡,大部份社會都被男權壟斷。這種父權式與文化霸權式的秩序,在不同社會都存在,當以上文化權力式的關係無處不在時,背後是靠男權去維繫,所以最私人親密的關係,都有政治的關係。由於文化關係背後受權力影響,所以有一句名言︰「個人的即是政治的」( The personal is the political)。一般來講個人的事屬於私人領域,但女權主義認為當父權無處不在時所有關係都是政治。這思想間接呼應全能政治的邏輯,當所有範疇都是政治時,政府是否什麼都可以管?或是否需要反對時,什麼都要全盤反對?中國歷史上曾出現全盤西化、或文化大革命等事件,都是將舊有制度全盤否定,是文化與政治互涉的結果。
人民是誰?
另一個令人頭痛的問題,也是香港現在遇到的問題,究竟誰才算是政治共同體內的眾人?香港愈來愈多年輕人,覺得自己不是中國人,不願做中國人。我父親在70年前從上海來港。我雖然在香港出生,但以前香港人的意識是比較模糊的。當時學校仍需填寫籍貫,各人多重視自己鄉下籍貫身份,鮮以香港人互稱。直至70至80年代時,才開始自稱為香港人。究竟如何才可構成政治社群的成員,政治共同體的成員如何構成?最近在年輕學生界別內,大家比較喜歡引用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講法──想像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y),認為社群都是靠想像建構出來的。

究竟誰是香港人?本人在教授比較政治學課時,當課堂討論到公民民族主義(civic nationalism)時,有同學認為香港需有自己的民族主義,以認同普世政治價值如人權、法治、自由為香港人標準。但如果根據這標準,是否代表重慶大廈暫住的非洲人、深水埗南昌街作買賣的黑人、菲律賓或印尼傭工、南亞裔人、或世界各地的人在認同這些普世核心價值後,全可成為香港人?若真如此,香港能否接受以上所有的人?究竟如何構成一個政治共同體內成員的身份認同,是一個令人頭痛和複雜的問題。若缺乏意志和決心去保衛一個共同體及其身份的話,或當這些人都是大難臨頭各自飛時,是不會出現一個民族的。當提到民族主義,成員的認同與犧牲同樣重要。
進一步說,關於民族的構成,在歷史與現實的經驗上,都出現過不少爭議與不完美的界定。其中一個看法是以血統和種族(race)為依歸,認為一生下來便屬於當地的民族。但這也不是十分可靠,例如中華民族本身包含很多種族。另一種是以文化為民族的構成,這固然有一定的道理和作用,但英美的文化都十分相近,結果雙方曾出現激烈戰爭,即歷史上的獨立戰爭。中國大陸與台灣的文化雖然十分相似,但台灣人卻很不情願與中國大陸政治統一。香港的情況也一樣,不少香港人不願認同中國大陸,但香港文化很難說不是中華文化一部分。另一種民族構成的界定是歷史。但事實上,撰寫歷史不少是有政治目的的。我們閱讀中國歷史時會發現,以前的晚清民國歷史論述,不少是同情國民黨的立場者編撰,以歌頌孫中山先生的偉大。但當《南華早報》紀念創刊一百周年時,再刊出孫中山先生當日去世時的社論,說到孫中山某程度上是位失敗者,很多問題都無力解決。很多時歷史故事都是受政治需要而說出來的,例如慈禧太后的負面形象便受到改革派文人梁啟超等的影響,「唱衰」慈禧是他們當時的實際政治需要,為達到他們的改革目的。關於慈禧廢科舉與開憲政等措施,或許並非如改革派說得的那麼差。可見共同歷史某程度上可以是建構出來,成為想像的共同體。
在今天的多元文化社會,有一段時間人們曾認為政治只需集中關注普世政治理想價值,不用再提不同文化或「安心立命」的終極道德議題。當冷戰結束後,社會主義集團瓦解,世界好像只剩下自由民主制,當時美國日裔學者福山(Fukuyama)便提出歷史終結論(End of History)。他借用黑格爾的講法,認為歷史並非完全理性,當人類不能成熟至完全理性時,歷史還充斥着很多偶然因素和不穩定因素,所以還會出現盲動。但理性會不斷發展,並通過國邦的共同體來實現。當一切的雜質及非理性東西全被篩走,理性絕對顯現時,就不需要再講歷史,因理性已取代歷史,成一種新的必然秩序,情況好像是將天國搬往地球的想法,正如《禮運大同篇》至馬克思說的終極理想完全實現時,無紛爭無政治的情況。福山認為有一些普世的東西,維繫我們的價值,只有以理性來規範,偶然和例外的錯誤便會消失。但這種說法有很多問題,第一是如果歷史真的終結,世界已變得大同。但今天世界大同了嗎?第二是歷史並沒有終結過,當冷戰結束後,文化衝突反而不斷出現,不論是最近英國曼切斯特或菲律賓南部棉蘭老島的恐怖襲擊,宗教文化衝突持續不斷。第三是普世價值本身的爭議,究竟普世價值是否真的那麼普世?不同論者都有不同意見,眾說紛紜。

無論如何,人們的確嘗試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如種族、歷史、文化、和普世的政治價值,來維繫政治共同體,但沒有一種說法和定義是可完全取代說服任何一方,當中還充斥着不同的爭持,甚至是衝突,各不同的民族文化戰爭仍持續不斷。在未達至世界大同或出現大亂兩種極端之前,不論喜歡與否,政治總需要分野,建立彼此,即是我與他者之間的分別。從這一點上,政治的出現等於分野的存在,其中分野可以是好是差,可以是建設性或侵略性和破壞性,但如果沒有分野便不需要講政治。在分野的過程中,還需要區分敵我的分別,分辨誰是誰非。其中毛澤東對此分野具一定的洞悉力。他認為政治的關係有兩種。一是人民矛盾是內部的,二是敵我矛盾,是你死我活,並非請客食飯。即使是最仁慈的政體,都會分敵我,否則不能建立自己的主體。與毛澤東的分野相近,另外一位德國的重要法理哲學家施米特(Carl Schmitt),亦寫了一本名為《政治性概念》(The concept of the political)的小書,他說,推理到最後,政治活動與現象,最根本的關係就是敵我關係。
很不幸地,我們都在不完美的世界內生活,只要有政治便代表不完美,因完美已不需要分野和政治。但盡管不完美,政治同時可使人們避免完全的敵對,正如現代政治學之父霍布斯(Thomas Hobbes)說過,如果我們想像在沒有國邦的年代,沒有主權巨人(Leviathan)時,任何人都是我們的敵人,形成一種百分之百的恐懼生活,即是陷入自然狀態(state of nature)中。有了政治秩序後,至少人們可以區分敵我與對錯,犯錯後會有後果,接受巨人(Leviathan)的懲罰。政治不會帶來天國,但至少會帶來秩序,然後可進一步區分各意識型態、宗教信仰和文化等,以上這些界定都是幾百年以來,我們對政治學的思考。
政治是可行的藝術?
關於可行的藝術,簡單來說可用一句話來概括── 既然那麼多不同意見和分野,如何才可變成共識和集體的決定?如果成功,這可避免天下大亂。因此要避免天下大亂,我們需要懂得政治。究竟有什麼辦法、制度、或做法比較上有保證和可靠地能將紛亂、分歧和衝突變成共識?而這共識是通過政治權威,真正有權利地作決定和說了算,嚴格來說,千言萬語講政治,便是這個意思。
在中華文明中,儒家思想自漢武帝獨尊儒術後,成為一種獨特而延續的秩序。當中華文明進入現代文明之前,儒家思想為主的政治秩序影響了我們二千多年,強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關係和權力的運用。君臣關係的存在是必然不平等的,但同時強調如果君不君、便臣不臣。儒家思想並不假設人人平等,並非是民主和一人一票,認為有君子與小人之別。在這情況下,他們的秩序是從某套思想演變出來,從中界定中國人的政治關係。
到了現代,今時今日最著名和主導世界的政治制度,是自由民主的制度。與儒家制度相反,自由民主制強調自由平等,個人是最重要的。如果沒有人民的同意,政府便缺乏合法性,因而引伸出代議民主,個人權利至上,共同規則比共同追尋更重要等政治特色。
第三種重要的政治秩序,但現已過氣的,是共產主義制度。在上個世紀,人們以為共產主義可以取代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制,但1989年卻失敗告終,餘下還奉行共產制的小國不足為道。即使是標榜共產的朝鮮領袖金正恩,也不能對世界有很多的影響,可能其核子武器會帶來威脅,不會取代自由民主制。現今的中國模式對民主持比較批判的態度,對自由民主制具相對較大的威脅,但仍遠不及冷戰時期,一套意識型態可能取代另一套意識型態的激烈競爭。共產主義強調平等、先鋒黨、和革命手段,與自由民主制都是現代的產物,但各有不同的政治假設和秩序。
第四種政治秩序,是近年伊斯蘭文化內的宗教復興所追求的政教合一體制。簡單地說,他們追求某種宗教上原教旨的復興,與西方基督教文化持比較敵對狀態。由於與西方強弱懸殊,他們中的激烈者只能以恐怖手段的非正規戰爭對抗,對世界仍具一定的影響。
縱觀以上各種對政治的嘗試,說政治是可行的藝術,其重要意義在於──如何將紛亂和分歧創建成共識?如何在各種的私人利益中尋找共同利益?如何避免所有人都變成敵人,避免全面的戰爭,進而建立合法性秩序?如何將衝突以談判和互諒互讓方式達至共同決定?以及如何以選票代替子彈,即英說的以Ballot 取代Bullet。
政治為什麼重要?
根據以上對政治學、政治行為和政治經驗的理解,我們開始明白為什麼亞里士多德會認為政治學如此重要。亞氏以「首要學科」(Master Science)來命名政治學,認為政治是一個至高無上與事關重大的學科,以解決各種重要的問題,例如生死的問題,決定整個共同體的命運。因為政治有壟斷壓制他人的權,和懲罰判斷別人生死的權,這全屬於合法及應然的權利,非只單靠武力執行。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如果要做一個比較完美和具充分生命的人,沒政治不能成為「正正當當」的人。如果沒有政治秩序,便出現天下大亂,所以政治學和政治行為在人類文化中,從第一天開始已經是十分重要。縱觀所有文化,政治學留下的經典,都對後世有很大的影響。在芸芸文化的經典中,政治學很早便出現。而中國其中一本最早的書《尚書》,主要是記載論述當時的憲政,不過是以當時的方式講述唐堯夏商周時期,帝王是如何作決定,及其決定的正當性。雖然政治不是唯一,因為人類文化比政治豐富,經典還包括《易經》、《詩經》等,以記述人類各種在人間世內重大的經驗。但政治作為人類文明一個很重要的資源,如果能認真通透地認識,可對今天與將來有很大的作用和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