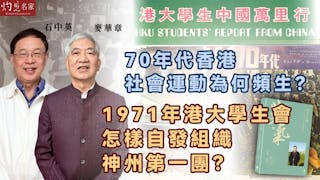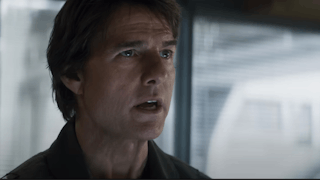香港過去數年,經歷前所未有的動盪及變遷。
一場反修例事件風波,掀起了一場又一場街頭上的示威、衝突。家庭因而分裂、社會因而撕裂,無論是政府與市民,還是建制與泛民陣營支持者之間,皆出現了前所未見的鴻溝,甚至仇視。是次事件,也在香港觸發了一場嚴峻精神健康危機,令不少人陷入精神困境;而7月1日發生的刺警及自殺案,更發出了令人觸目驚心的警號。
姑勿論支持此運動的人初心如何、反對此運動的市民原因又是如何,我們應當在遵守法律的大前提下向前看,必須着手解決困擾我城的巨大精神壓力,讓港人重新出發,共建一個能為不論政見、不論立場,皆可安居樂業,找回安全感的家園。

香港精神健康問題不容忽視
國際醫學期刊《刺針》於2020年發表由港大進行的港人精神健康研究報告,發現2019年9月到11月期間,約有22%港人患有抑鬱症及創傷後遺症。同時,香港心理衞生會於2020年的全港抑鬱指數調查,進行了1366份問卷調查,當中超過20%受訪者呈現嚴重抑鬱情況,其中主要原因的首三個,乃是政治及社會動盪、疫情及和家人的相處關係。
也即是說,每五個香港人之中,便有一個出現精神健康問題。相對於不少發達國家及地區來說,20%──這絕對是較高的數字。英國的抑鬱及焦慮症的呈現機率,約莫每100人中不到10人,只有約8%的機會率。美國(5.2%)、日本(7.6%)等地患上嚴重精神健康問題人口佔總人口的百分比,也遠比香港為低。
近日香港瀰漫着一股令人悲觀的陰霾。有不少人因社會事件與及後的一連串社會改變,而對香港萌生去意。走不了的人,則有不少對現況感到絕望,並對政局及體制產生一種強烈反感,甚至仇恨與敵視。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來說,當一個社會出現嚴重的動盪不安及「失範」(anomie,這是社會學家涂爾幹所提出的一個概念,大致形容在現代化或其他大型社會變革前提下,因傳統價值觀的顛覆或削弱,個人所經歷的方向迷失)之時,個人有可能會對社會整體框架及結構產生排斥,甚至認為自身與「新」社會格格不入,而踏上偏激化、自我封閉、消極抗衡等之路。若單純聚焦於陷入精神危機人士的「反社會行為」,只會令這些人感到更為孤立,更難取得社會信任或重投社會當中──這只會令他們與社會大眾愈走愈遠。
在身患精神疾病的市民當中,尤其值得關注的,乃是因社會事件而被捕的一眾青年人。根據警方資料,自2019年反修例事件爆發至今年4月底,警方共拘捕10260人,當中39%乃是學生,17%(1754人)乃是18歲以下未成年人士,而這1754人當中,有473人被檢控,其中大部分須承擔法律後果。25歲以下的年輕人有超過6000人被捕,他們是香港下一代關鍵一部分。作為我們城市的一部分,值得給予他們機會,以具建設性及正面態度,協助他們在承擔法律責任後重投社會,為香港未來出一分力。

被捕青年人身心健康受創
撇除生活在香港這類高壓城市所帶來的「必然」壓力不說,身陷在司法風暴當中的被捕青年人的心理和個人生活問題,絕對值得我們關注。被捕青年人經歷了街頭暴力、警民衝突、拘留或保釋期間承受極大的恐懼及孤立無援,以及在司法程序面前面對失業、坐牢、被社會所排斥等種種長遠隱憂,這些壓力點讓他們很多原本潛伏在內(latent)的精神健康問題,一一浮面。
久不化解的精神問題,除了會對當事人身體及個人發展構成嚴重威脅,更會令他們承受極為痛苦的精神壓抑,以自殺或自殘等無補於事的悲劇手法處理自身問題。撇除個人政見立場不說,這樣的香港,相信絕大多數人都不想看見。
須知道,被捕年輕人所面對的問題,並不限於他們的精神困境,也包括其他種種問題。當中有不少人與家庭關係本已經疏離,而因他們在社會事件中的參與,以至及後牽連,家庭關係更進一步惡化。有部分家長對子女的政見立場、行為手法強烈不滿,更有個別人士會對子女的遭遇進行公開的批評及嘲諷。這除了令他們兒女難堪以外,其實於事無補。
另一邊廂也有不少家長,雖然對自己子女遭遇表示一定的關注及同情,卻因為缺乏適當的訓練及經歷,而不懂得與子女溝通、聆聽他們的聲音,因而錯失疏導及引導他們重回正軌的機會。不少家庭因生活壓力及經濟環境,根本負擔不起昂貴費用的私人家庭輔導員服務,而政府的輔導服務卻需長期輪候。
在這種情況下,家庭關係惡化,無疑是年輕人被捕所埋下的計時炸彈之一──若不妥善處理,只會把更多的家庭成員拖進漩渦當中。家長與子女、長輩與後輩之間的心結一日不解,我們都很難可以看見真正的社會復和。每一個家庭,都值得一個能讓下一代茁壯成長,及時反省更新的機會。
容納不同意見及聲音,鞏固民心改善治理
此外,這些年輕人與體制之間如今的勢成水火,也令對他們的輔導變得攸關重要。不少被捕人士和他們的父母及朋輩,往往對政府及官方機構,存有極度強烈的反感及不信任。除了對在司法程序當中對法庭、警察、檢控官等懷疑或厭惡,也會長期懷疑法治和法制,並會對任何政府施政投射負面的標籤。
這一來對他們與政府、與社會其他持份者合作以改善香港於事無補,二來也只會為政府施政增添阻力。一個對體制死心的信念,不單影響自身行為,更有可能影響其同輩、同僚、在監獄或司法制度中遇到的其他人,令他們對香港及中央政府產生誤解及敵對,為香港未來埋下地雷,對促進社會進步及改善,也是毫無幫助。
若要香港找回希望,在守法的大前提下,我們必須願意在香港的同一屋簷下,容納不同政見及聲音,才能真正地鞏固民心,改善治理。
最後,正如坊間不少評論皆指出,有不少參與社會運動的年輕人,家裏經濟環境本身不佳,也看不到社會流動的出路及可能性。他們並沒有足夠的資源能夠在候查候審過程當中維持穩定生計,或是因着資金短缺,而不願意尋找法律及專業援助。每一個人──姑勿論歷史或背景──皆擁有接受關鍵醫療支援及輔導的權利。精神健康,作為人類生命不可或缺的一環,必然要得到適度的保障。
如今只見公立醫院精神健康資源嚴重不足、精神病診症輪候時間漫長、社會上普遍仍然充斥着對精神病患者的誤解及無知。在這種種問題交織下,試問身患本來可治可控精神病的少年,又怎會願意主動求醫,尋求協助。甚至有不少人,乃是在經歷司法程序過程當中,才發現自身原來患病,需要接受治療輔導──雖然為時未晚,但預防確實勝於治療。若社會能避免更多的被捕人士墮入思想及生理誤區,及時將他們從危險邊緣挽回,豈不是更佳?

紓緩港青心理危機須對症下藥
要全面解決被捕青少年的心理危機,需要的並不只是單純增加資源、提高有關精神健康的關注度,又或者透過硬性手段,向這些年輕人灌輸「特定」的思想及概念。我們需要的,更多的是能針對性化解問題根源的對症下藥,以確保青少年能準確地報告自身病情、尋求他們可信任的專業持份者協助,最終重投社會,為香港未來貢獻。
第一,我們倡議非政府、非牟利機構應當擔任更為主要的角色,在官方渠道和體制以外,直接服務年輕人。不受政府資助的機構,更能在觀感及實際操作層面上政治中立,不為政治立場所左右及秉持專業準則。同時,作為曾參與不少非政府機構的統籌及執行工作的學者及專業人士,我們認為在官方架構以外的機構,更能採用全面而具彈性的輔導方向,以確保在協助具精神問題的年輕人時,他們的父母、家庭、同僚等各大持份者,可同時參與其中,從而將效益最大化,幫到最多的人。
這些機構也應當與學校、教育機構及社區領袖合作,以吸納及鼓勵更多的年輕人向他們求助。此過程當中,這些機構必須維持獨立、中性、平衡、公允的立場及態度,不讓政治及意識形態所干預,更不能成為政治目的的代理人。反之,也不應抗拒與各持份者正常專業的合作,以疏通年輕人與體制之間的距離及隔膜。
第二,我們倡議提高香港──尤其是年輕人當中──的整體心理健康辨識度(literacy)。如今坊間充斥着不少有關精神健康的「假新聞」及似是而非的半事實,這些皆令處理問題事倍功半。透過與學校老師、大專院校教授的合作,我們認為獨立而具公信力的學者專家,應當提供適度評核標準(assessment),以供受過訓練的業界內人士,為年輕人診症、把脈,以確保能及時發現出現心理健康紅燈訊號的救助人。
有心人士甚至可以鼓勵感覺到自身有需要的年輕人,自行嘗試透過網絡或社交媒體等渠道,聯絡可為他們提供支援的團隊,透過半匿名、高隱私度的渠道,向具資格人士滙報及查詢自身症狀,從而得到較為快速的協助及幫忙。
以有效、開放方式,疏導精神壓力源頭
第三,港人所面對的壓力龐大。無論是上樓困難、政治分歧、意識形態的執着,還是個人與體制之間的衝突,這些壓力煲中的「成份」,必須得到適度的釋放疏導,否則後果則不堪設想。我們認為香港如今不應以政治及立場掛帥,而忽略了超越政治、回歸社會管治的基本公共衞生及健康問題。年輕人需要有效、開放的方式,讓他們能在不違法的前提下,抒發己見,尋覓與自己能產生共鳴的理性同路人。
政府應當讓香港擁有此類的空間及平台,才能讓民心轉向,讓普遍年輕人能看到制度內改進現況的空間。正本清源,需要我們就着精神問題從上游入手──若一味以為堵塞「極端行為」的呈現,便能解決問題,實為頭疼醫頭,腳疼醫腳的表現。多管齊下,才能為香港迎來新氣象。
我們明白不同群組的市民對近年的社會運動有十分不同的看法,不過在尊重法律的大前提下,我們不能讓意識形態及政見凌駕於心理復康和精神健康之上。若要我們這城市修補裂痕、穩定大局,我們需要的是同理心(empathy)及愛護情懷(compassion)──對於因應2019年事件而從而對政府徹底失望的一代年輕人來說,他們尤其希望及需要我們釋出善意;在法律所設定的框架內,接納及擁戴合理的多元,才能讓香港再創出一片天。
聯名作者簡介:
袁家慧為輔導心理學家;黃宗顯為精神科專科醫生;黃裕舜為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生。
原刊於《信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