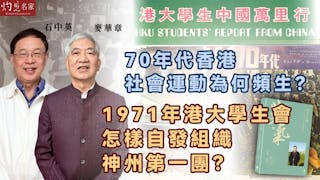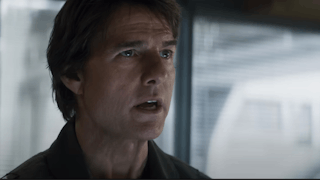過去數年,中國外交部多次就《中英聯合聲明》(以下簡稱《聯合聲明》)在今天的效力公開說:「香港已經回歸祖國懷抱,《聯合聲明》作為歷史文件,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對中國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也不具備任何約束力。」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外交部又稱《聯合聲明》的「核心要義是中英間關於中國收回香港及有關過渡期安排」,強調「回歸後香港事務純屬中國內政」。
對此外交部宣示的立場,應如何理解,完全認同該文件「已是歷史文件」的論斷,以及其引伸指《聯合聲明》就「中央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不具備任何約束力」和「現實意義」的演釋和說法?相反,如果對以上的說法有保留,基礎又在哪裏?

中山大學粵港澳發展研究院副教授伍利斌,日前在內地《中外法學》(Peking University Law Journal)(2021年第6期)發表了一篇題為〈試論《中英聯合聲明》的法律效力〉 論文,從國際法角度,對此具爭議性的課題,也就是《聯合聲明》在今天的法律效力,提出不少深值重視的見解。《中外法學》是北京大學法學院主辦的雙月刊。
英方《香港半年報告》:中方違反「法律義務」
在介紹伍利斌教授論文的觀點前,不妨先看看英國政府日前向國會提交的最新一期《香港半年報告》,英外相卓慧思在該報告強調,中港政府透過實施《港區國安法》「打壓香港反對聲音、支持民主的新聞媒體及公民社會,以及徹底改變香港的選舉制度」,違反了中國在《聯合聲明》中的「法律義務」。報告書所指的「法律義務」,在國際法中又是屬於何種性質的指控?

伍教授在論文中首先指出,《聯合聲明》在法律性質而言屬於「雙邊條約」,是「受條約法規範,但同時又是一個特殊的條約,其部分條文屬於當事國的單方面聲明」。伍利斌表示,「國際文書的法律性質不取決於其名稱和用語,取決於當事國的主觀意圖。中英兩國同意受其約束、聲明的生效程序及提交聯合國登記等外部因素,已經充分表明中英兩國都具有使聲明屬於條約的主觀意圖」。
他解釋道,「中國是否具有受約束的主觀意圖呢?答案是肯定的」,聲明第3條第12項和附件一第1條均清楚寫明中國「承諾」將以制訂《基本法》的方式具體落實第3條及附件一所列各項對香港的基本方針政策,且50年不變。「簡言之,作為單方面聲明的第3條及附件一具有產生法律義務的條件與效果,聲明第3條及附件一構成中國的國際義務」。
他又提到,時任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吳學謙在1984年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審議中英關於香港問題協議文件的報告中就曾明確表示,「《聯合聲明》也是國際條約的一種形式,同樣具有國際法效力和法律約束力」。
主觀意圖構成的「國際義務」
第二,伍利斌在強調《聯合聲明》在法律性質上屬於雙邊條約,受條約法規範的同時,又「是一個特殊的條約,其部分條文屬於當事國的單方面聲明」。至於國際法是否允許一個雙邊條約的某個條款屬於單方面聲明,而不是條約當事國之間的共同條款?
他表示,「從國際法的性質和國際法的理論與實踐來看,國際法不禁止一個條約的某個條款僅屬於某個當事國的單方面聲明;一個條約的某個條款究竟屬於各當事國的共同條款還是屬於某個當事國的單方面聲明,取決於國家的主觀意圖」。
他續稱,《聯合聲明》是一個求同存異的聯合聲明,「其中,第3條及附件一在性質上便屬於中國的單方面聲明,但其「以公開方式作出,明確表達了中國受其約束的主觀意圖,構成中國的國際義務」。
第三,伍利斌表示「中國在中英談判過程中一再申明反對英國對回歸中國後的香港享有任何權利」,同意英國對回歸以後的香港不享有任何權利,也就是「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但即便如此,亦應正視「《聯合聲明》的權利義務關係具有特殊性。鑒於中國以公開方式作出、且明確具有受其約束的主觀意圖,《聯合聲明》第3條及附件一構成中國的國際義務」。

《聯合聲明》應不准許單方面終止或退出
因此,伍利斌認為根據條約的整體性原則,不能因為部分條文已過履行期限或履行完畢而簡單宣布整個《聯合聲明》已經終止。此外,「聲明各個條文有效性的時長有所不同,不宜以部分條文效力已經終止為由而否認整個聲明的繼續有效性」。「根據沃爾多克的條約性質分類,《聯合聲明》應屬於不准許單方面終止或退出的條約」。「概而言之,在《聯合聲明》未對效力終止作出規定的情況下,聲明當事國中國或英國一般性地不能單方面終止聲明,同時也不存在允許單方面終止聲明的例外情形」。
伍利斌的結論是:「在與英國權利義務有關的條文實際上不再產生效力的情況下,主張聲明中這部分條文已經終止效力,則是對法律事實的準確描述」。
如是以觀,伍利斌的見解,是從國際法角度對外交部指稱《聯合聲明》只是一個「歷史文件」和不具備任何「現實意義」說法的修正建議。至於被認為構成中國國際義務的《聯合聲明》的第3條及附件一,是否已被履行,以及《港區國安法是否違反中國在《聯合聲明》中的「法律義務」,伍利斌的文章未有涉及,也不屬本文的討論範圍。
原刊於眾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