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官場的腐敗,也加劇生態惡化,導致防備天災能力的下降,這都是震前的人禍。中小學的「豆腐渣」,導致大量少年兒童在地震中喪生,更是無可饒恕的人禍。回顧歷史,重視古代的「天災警示觀」,有助思索減少災害和人禍、落實科學發展觀。

1944年,平民一天只能配給一碗飯,菜和魚蝦都沒有了。沒想到在這餓肚子的時候,有個東京大學留學生朱紹文被憲兵抓進牢裏,因為是軍隊配給,可以每天吃三頓飯,不光比一般監獄好,比外面也好。

有關普教中爭議,我們應該用平常心的角度作出兼容並蓄的選擇,還是以二元對立的態度作非此即彼式的取捨?

一個世紀後的旅行家很可能發現地球語言環境有如下的兩個特點:首先是,語言種類大大減少;其次是,語言將比現代的更為簡單──在口語方面尤其顯著。

拔萃一向都被視為一所非常英國化的英文中學:學校只重英文、學生忽視中文。施校長上任後,便想方設法去扭轉形勢;郭校長接棒後,也不遺餘力地推展新猷。他曾先後向兆傑和官銳提出,要求搞一齣中文話劇,但最後都沒有結果。

是甚麼原因使地球發燒?有兩個年份很值得注意:一個是1750年,那是標誌着工業革命開展的年份,另一個是1950年,是標誌美式壟斷資本主義經濟及其意識形態與生活方式向外擴散……

課室外,人人都是窺探者,對着張愛玲的家世、童年陰影、婚姻、政治立場……,無孔不入。

傳媒老闆及佔中積極參與者黎智英在他的周刊的一篇專欄文章中提到良知問題。他在和一位女學生的談論中提到:「我說,不用擔心那些反對我們的人,若然你相信真理,你便知道他們是被權力和利益蒙閉了思想,麻木了良知。但這都是暫時的,一切物質和利益都只會是暫時的,良知卻是永遠的,良知會喚醒他們。」

高度密集,高度濃縮,在這裏生活十年所見所聞,抵上在別處活上三生。

信不信由你,叫人某君、某甲、路人乙和「那個人」的稱謂,幾千年前就有了,不信?且看幾個例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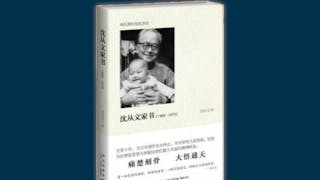
沈從文文革十年間寫給家人的83封信,有三大看點:一,有助於了解當時的社會,尤其是運動的情況。二,有助於了解當時民眾的生活。三,有助於了解沈從文的思想……

2012年諾貝爾文學奬得主莫言,是少數在小說中書寫獨生子女政策的中國作家。早在上世紀80年代,莫言剛開始其寫作生涯時,他的小說就已經涉及這一敏感題材。

沒有春天的心情便無法欣賞春天的景色。春天的心情,卻不是要有便有。世上許多地方,都難有這種心情……

莫熙穆,一生清貧,是廣東最早接觸並研究現代生物學的少數學者之一。他為農民奉獻一生,期望土地再有肥沃,耕民能擺脫貧困。……

何秀煌老師不持教案,不談功課,多談的是情意我。說愛情使理學家變成詩人;說痛苦在牽掛,境界應在了無牽掛憶舊情;說文人的客廳是書店的延長……如此輕鬆、隨意和隨心,道盡了教育的自由。

在嘉禾片廠的配音室工作時暈倒,鄒文懷即時致電李小龍在港的家庭醫生, 後者指示鄒立即送李到就近的浸會醫院急症室。入院時李已昏迷、痙攣並嘔吐……

近期各地水災、旱災頻仍。天災往往與人禍交纏,古代的天道觀與當今社會治理往往又聯在一起。天道觀,源自儒家經典和儒家前的歷史典籍。本文思索歷史文化,略析「天」的意涵,古代的社會治理觀、制度構想和權力約束。

由香港貿發局主辦的第 26 屆香港書展將於 7 月 15 至 21 日假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今屆書展以「從香港閱讀世界‧一讀鍾情 」為主題,寓意遇上優秀的書籍就如碰到令人幸福的好情人,期望讀者可在書展與好書多談戀愛,豐富人生。

現實的變速有高有低。當變速低的時候,我們很自然的不會想到要捕捉現實,相反亦然……旅遊者從景點到景點,現實轉移頻繁,自是以相機捕捉現實。

原來他一直活在那個尚未開發的鄉郊,那是個年輕、激動而浪漫的世界。但他定時從那裏面走出來,以一個八旬老人的身份和我們吃飯,談天,身體漸漸衰微。從一場美夢醒來時,我發現自己抓住了他的畫筆……

呂思勉和錢穆同是20世紀的四大歷史學家,他們對於歷史事件的看法,對今天仍具重要參考價值。

1963年11月一個晚上,我在閱讀李相勗的《課外活動》時,忽發奇想:拔萃應有一份學生報。想到這,我霍然而起,立即更衣,開車回校,找兆傑商討大計……

無數實驗證明,真實的人,在博弈時很少會理性地作決定;而人們憑「非理性」決定得到的收益,又往往比理性決定好得多!對於政治博弈,這道理尤其真確。

就在這抗戰勝利紀念之年,我們在此回看一下這些因為日本侵華而中斷了藝術事業的書畫家們……

如果能把儒家跨越時代的部分跟憲政民主相結合,也許會有一種稱為 Confucian Democracy (儒家民主)的東西出現。這東西如果真的出現,我相信是中國政治思想史上一個發展的里程碑,也代表着中國傳統的政治智慧並沒有因為進入現代而將之放棄,只留下些倫理學而在政治上沒有任何地位。

有報道說,因為由手機代工業者的自行開發,類似蘋果iphone的「山寨手機」,在大陸市場走紅,令「山寨」一詞,成了網路流行語……

我仰首之際,與祢慈眼雙垂之間, 世外淨土,就在現前。 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薩摩訶薩, 看穿一千六百年光景, 仍眷顧地凝望着我們, 照亮着這塵封了的心靈⋯⋯

早在1940年代朱光潛在談到文學的時候,已強調一種代表性的說法,說文藝乃人類為超脫自然需要的束縛而自發的活動;它起於實用,但又超於實用。

我多麼渴望我們能在道別時互說「明天見」。明天見不到,那就「下個月見」吧。甚至如牛郎織女,珍重話別時說:「明年七月七日再見。」可惜我們沒有那麼幸運,天曉得那一天才可以回到你身邊。……

如果我說儒家說得那麼好,我們就必須問一個問題,為什麼儒家沒有在現代社會更加發揚光大?為什麼我剛剛所說的儒家政治,沒有在今天可以看得到?在回答這個問題之前,我們必須對什麼是政治的統治有一個初步的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