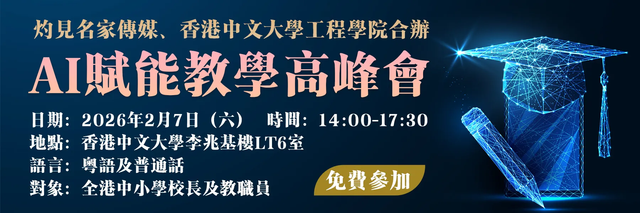當我認識的朋友紛紛對我敬而遠之的時候,一天,宿舍裏來了個不速之客,要和我交朋友。
他是英國人,名叫Leo Goodstadt,有個中文名字「顧汝德」。他突然來到宿舍找我,自我介紹說是《遠東經濟評論》(Far Eastern Economic Review)的副總編輯,曾經在香港大學教經濟學;他知道我弟弟入獄的事,特意來找我聊聊。
對這陌生人,我自然抱有戒心;我猜他是什麼記者之類,來向我套取弟弟的資料;又或者他像很多人一樣,認定弟弟的行為是我指使的,要來查我的底細。不管怎樣,我沒有什麼可以告訴他,因為事實上,對於弟弟在學校的行動,我事前一無所知。
初次會面的冷淡
我的冷淡態度沒有令他知難而退;他顯然看透了我的猜疑,有意讓我覺得他不是要來蒐集什麼材料。他說他很同情我弟弟,知道我在港大讀書,於是特來慰問;如果有什麼他可以幫忙,他很樂意。我多謝了他的好意,沒向他提出什麼。我們談了大約半個小時,他提議約個時間一起午飯,我答應了。
大約兩個星期後,我應邀到中環一家餐館和顧汝德午飯。我們邊吃飯邊聊,漸漸他把話題帶到左派和政府的矛盾。他漫不經意地問:「『鬥委會』的真正領導,其實是楊光、費彝民還是新華社?」(鬥委會即1967年5月成立的港九各界同胞反對港英迫害鬥爭委員會,工聯會理事長楊光是主任委員,《大公報》社長費彝民是副主任委員。)他還問了其他一些有關反英抗暴的人事和組織問題。我想:他找我的真正目的暴露了。我當然不會回答,因為我根本不知道答案!
試探與補習邀請
之後他再來找過我幾次。有一次,他和我談馬克思的學說。他說他不同意馬克思的階級矛盾理論。他說,不同性質的工作,需要不同的人才,也需要不同的工作環境和條件。譬如你寫學術論文,需要有一間冷氣房間;但從事體力勞動的工人,便沒有這個需要;這不是歧視體力勞動,更不是階級剝削。我聽了只是唯唯諾諾,沒跟他辯論。
又有一次,他說要請我做他的補習老師,教他數學。他說,他是研究經濟學的;經濟學的新發展需要很多數學,所以他要補習。他知道我在港大校外課程部教過課,便特別強調,他給我的報酬肯定比校外課程部慷慨得多。我不至完全沒有自知之明,自以為真的有資格給這個大學講師補習;我認定這只是他要和我保持聯繫的手段而已。我直接推了他說:「經濟學需要的統計數學,我不懂,沒學過,沒能力替你補習。」
我們的交往維持了一年多,之後我便沒有再見他了,直至20多年後我踏足政壇,才再遇上他。我跟顧汝德的短暫交往,引起了一個人的關注。這人是比我高幾屆的港大校友,名叫毛鈞年。
原刊於《明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