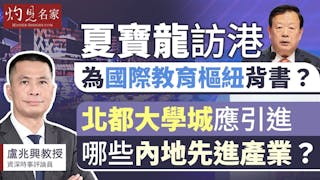今天,人們普遍認為,西方自由主義再一次面臨嚴峻的內外部威脅。內部的威脅來自民主治理的失效甚至失敗,表現在抗疫不力、遍布各國的「黑命貴」(BLM)運動、黨爭、「權威民粹主義」(authoritarian populism)領袖的崛起、各種激進左右派思潮和勢力的復興等各個方面。而中國模式的崛起,則被視為是對自由主義的外部威脅。
中國在過去數十年間不僅造就了世界經濟史上的奇蹟,而且在各個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中國所發展出來的制度體系,則是建立在自己的文化和文明之上的。並且在國際層面,這套制度體系開始為他國(尤其是發展中國家)所關切。儘管中國本身並沒有意圖,要在國際社會輸出自己的制度體系,但西方還是感覺到了制度競爭的壓力。
近代以來,自由主義一直主導西方世界,是西方的主體政治思想。無論是西方還是非西方,都把近代以來的各種成功,歸諸於自由主義的崛起。對西方世界來說,自由主義就是西方核心價值觀中的核心。在其產生以來,西方世界花費了最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和智力來發展、維持和擴散自由主義,保護自由主義免遭來自內部和外部的挑戰和威脅。
的確,自由主義始終是在與其他「主義」的鬥爭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冷戰之前有西方內部的各種主義,尤其是法西斯主義;冷戰期間,以蘇聯為代表的共產主義,被視為是對自由主義的最大外部威脅。
不管自由主義辯護者的說辭如何,實際上,自由主義的最大威脅始終是來自自身的邏輯,無論是理論邏輯還是實踐邏輯。法西斯主義是西方國家內生的,並且法西斯主義的崛起的背景也是自由主義,即法西斯主義是通過選舉和人民主權登上歷史舞台的。冷戰期間蘇聯共產主義也從來沒有對自由主義構成過真正的威脅;相反,西方內部則以此為名,對內部的異端力量進行整治壓制,尤其表現在美國的麥卡錫主義上。
自由主義的威脅和危機
那麼,自由主義本身的邏輯如何導向自由主義今天的危機的呢?可以從如下幾個方面來看。
自由是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觀,而自由的核心又是個人自治。但自由主義對個人自治無限制的追求,導致了社會大眾最終失去了自由。顧名思義,在自由主義那裏,一個社會的單元就是個人。但「個人單元」並不是事實,而是假設。人是社會的動物,生於社會,長於社會,沒有人可以完全和社會分離開來。人是社會群體的內在部分,這是人的優勢。在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Alexis de Tocqueville)那裏,人的價值就在於其社會性。因此,托克維爾所強調的並非個人自治,而是社會的自治,社會群體的自治。
儘管托克維爾也是西方自由主義者,但其對人的集體性的強調,並非西方自由主義的主流。自由主義的主流強調,個人要從所有一切制約中解放出來,實現完全的自由,包括所有的傳統制度、規範和價值觀。對自由主義來說,個人唯一需要受到的制約就是國家的法律;除了法律,沒有任何其他因素可以制約個人,也不應當對個人構成制約。
但即使是法律,對自由主義者來說也已經是一個巨大的妥協了,因為沒有法律,個人就會變得無法無天。實際上,極端的自由主義者也是反對法律的制約的。結果,當個人的行為不受任何社會規範制約的時候,法律成為了唯一的制約。但法律意味着什麼?法律代表着國家,法律的擴張代表着國家權力的擴張。這就使得自由主義走向了自由主義的反面,因為自由主義的「初心」就是要制約國家權力。
托克維爾強調,自由存在於從家庭到國家之間眾多的社會團體(或者今天所說的市民社會);或者說,自由意味着所有這些團體的自治。但當所有這些「市民社會」消失的時候,自由和自治也隨着消失。不過,這種「消失」是自由主義本身的內在邏輯所致,因為自由意味着個人逃避來自所有這些團體的制約。
在市場方面更是如此。從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到當代新自由主義經濟學,自由主義提倡的是市場的完全自由。完全的自由意味着需要打破所有對市場的人為設置的邊界。市場就是沒有任何邊界。隨着資本主義的崛起和發展,市場打破了原來的地方化的封建邊界。全球化則賦權市場打破國家的邊界。到了自由主義經濟學那裏,自由意味着市場免於來自政府的所有干預。
很顯然,國家權力和市場權力的無限度擴張,使得個人無論是在國家還是在市場面前「原子化」了。從表面上看,因為在個人與國家和市場之間毫無邊界了,個人的權力得到了無限的擴張,但實際上無論是國家還是市場,都已經置個人於毫無力量狀況。
傳統上,西方自由主義用「原子化的個體」,來指向權威主義社會(尤其是極權主義社會)中個人的生存狀態。西方所說的權威主義社會下,國家重組傳統社會組織,把社會組織納入國家的管控機制,這是一種通過政治和行政的控制。
但西方社會所發生的「個人原子化」,較之權威主義社會有過之而無不及。「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市場面前人人平等」,意味着在個人和國家之間、個人和市場之間不存在的制約,國家和市場力量直接可以到達個人。沒有個人可以抵禦國家權力(法律),也沒有個人可以抵禦市場權力。
今天,沒有任何一個個人能夠逃避國家和全球化的市場,但同時人們感覺到,無論是國家還是市場離自己愈來愈遠,並非自由所能控制。個人對國家、對市場的「異化感」是史無前例的。這也不難理解,在今天的世界,社會抗議要不是直接針對國家,要不是直接針對市場。
即使在個人層面,自由主義也充滿了永無止境的矛盾,經常處於自我擊敗的狀態。這裏,自由主義的邏輯是在脫離現存社會群體的同時,尋找後者重組社會群體。人生於一個特定的社會群體,並且受這個群體制度和規範的制約。如上所說,這些制度和規範被自由主義視為是「不自由」,自由意味着個人從這些制度和規範中解放出來。但同時,自由主義又竭力鼓吹和提倡人的「認同」的重要性。

顯然,「認同」並非是一個「個體」概念,而是「群體」概念。在只有存在一個人的情況下,就無所謂「認同」,只有在不同人的比較過程中,才會有「認同」的概念。所以,對自由主義來說,個人的意義在於「解放」和「重塑」自己,即從傳統群體中解放出來,而把自己「重塑」成為自己想要的「那個人」。
這種情況在人的性傾向的界定上表現得特別清楚。傳統上簡單的男性和女性的區別,已經遠遠不能滿足現代社會的需要。今天,除了人們熟悉的男同性戀和女同性戀之外,不斷出現新的類別,形成了LGBTQ群體。實際上,網絡空間上各種虛擬社會群體形成的邏輯,和性別傾向群體是一樣的。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出現,為人們在全球範圍內「重塑」自己提供了技術條件。
人們只注意到各種激進化團體,在網絡空間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但實際上,所有這些群體便是現代社會的新生「物種」。對生活在實體社會的人來說,這種「重塑」的過程也是實體社會「碎片化」甚至消解的過程,對實體社會已經產生了巨大的破壞作用。
「無邊界」形式自由主義
自由主義認為,任何邊界,小到個人的性取向,大到國家的邊界,都是人為設置的,都應當被取消了。很顯然,自由主義致力於「無邊界」形式的社會,不是一般社會大眾所能接受的。可以說,可以無限制「微觀化」的認同政治,有效地摧毀着自由主義。如果這種認同政治繼續破壞現存社會,導致人類危機,必然會出現反自由主義的新意識形態,甚至宗教。實際上,在很多社會已經出現了這種趨勢。
在實際政治層面,自由主義往往表現為不同社會群體之間的權力之爭。自由主義在近代產生和發展早期,就是致力於「奪權」,即把權力從傳統貴族轉移到新的貴族(即商人和資本家)。傳統貴族權力是基於出身、家庭身份繼承等因素之上。
等到商人(和資本)崛起之後,他們認為這種權力基礎很不「自然」,一種更為「自然」的基礎是人們所擁有的財富。自由主義便論證了為什麼權力要基於(商人的)財富之上。所以,早期自由主義提倡傳統貴族和新貴族(商人)之間的分權。當時在所有西方國家,資本家或者商人控制了議會,和國王分享權力。
自由主義產生之後,它就成為了新群體爭取政治權力的有效工具。或者說,任何一個社會群體都可以把自由主義作為一種有效的意識形態工具來爭取政治權力。近代工業化產生了資本家群體,資本家群體又孕育了一個工人階級群體。工人階級崛起之後,也跟隨着從前商人和資本家群體的步伐,用自由主義為自己爭取權力和權利。社會主義運動的思想基礎也是自由主義,只不過在當時被視為是激進派的自由主義罷了。上世紀60年代西方學生運動,和70年代美國的黑人民權運動,其思想基礎也是自由主義。
實際上,今天從西方到非西方,幾乎所有社會抗爭運動都是打着自由主義的旗幟。甚至連自由主義所痛恨的民粹主義,也是自由主義的產物。沒有一個社會會如自由主義所設想的那樣變得平等,社會永遠會是等級性的,永遠會存在統治者和被統治者。特朗普被視為是民粹主義政治人物,但他也在鼓吹「還權於民」,權力不應當掌握在那些脫離社會的精英人物手中,而是應當讓人民真正掌握權力。
人們可以設想,特朗普在這裏把自己視為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了。但不管怎麼說,所謂的民粹主義政治人物,就是那些得到底層社會擁護和支持的政治人物。這些人物也是可以應用自由主義的原則來掌握政權的,儘管他們所作所為是被視為是反自由主義的。
歸根究柢,自由主義的矛盾在於始於「性惡論」但終於「性善論」。起初,自由主義對人性抱有一種極端的現實主義的看法,即假定人性是惡的,但最終自由主義走向了對人性美德的無限誇張,即人性是善的。這尤其表現在民主制度的運作上。

自孟德斯鳩開始,幾乎所有近代自由主義者都認為,民主是一種對公民具有非常高要求的體制,不管他們使用什麼樣的概念,無論是「政治美德」還是「公民品德」,都是強調對人的要求。他們意識到,儘管民主不可避免,但純粹的民主會破壞甚至摧毀自由主義原則,所以他們設計的早期民主,實際上在很多方面是「反民主」的,因為他們給民主附上了諸多條件,實際上是非常有限的民主。
當代民主理論家也在強調「公民品德」對民主運作的重要性。但現實是非常殘酷的。在自由主義推動下,民主的形式(即「一人一票」)得到了長足的發展和進步,但民主的內容(即「公民品德」)則漸行漸遠。近代以來很長一段時間裏,人們見到了「自由民主」的一體化,但當代的發展則是「自由」和「民主」的脫鈎過程。無怪乎,愈來愈多的自由主義者感嘆着傳統價值觀和傳統美德,隨着他們所爭取的民主的到來而消失了。
儘管世界各地的抗爭者仍然高舉着自由民主的旗幟,合情合理地為自己爭取着權利,但很可惜的是,今天的自由主義已非往日的自由主義,今天的民主也非往日的民主。
對自由主義來說,一個更為殘酷的現實是,如果「一人一票」的民主已成不可扭轉的政治「鐵律」,自由主義所謂的傳統價值和政治美德也一去不復返了。而所有這一些都是自由主義自身邏輯的結果。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