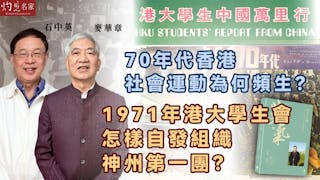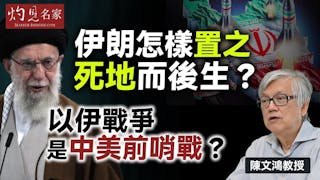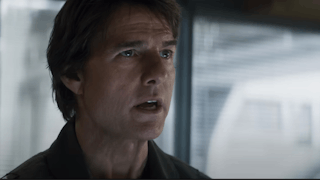編按:本文由張信剛教授根據李大白(灌茶家)2017年6月25日在公眾號發表的〈張信剛:現代大國進行智力構建的經驗〉一文改寫,本社獲作者授權分兩期刊出,是篇為文章下篇;作者對「近代強國的智力構建過程」和「美國的特殊做法」等看法可參閱上一篇。
我在美國、加拿大、法國和土耳其的大學都曾經正式任教,在英國、印度、埃及的大學也曾居住和交流。美國的政體是總統制,主要官員由總統直接任命;其他國家(不計埃及)則是內閣制,總理和內閣成員都是國會議員,閣員之下是不可輕易任免的職業公務員。所以美國的政界和學界,商界的互動較之其他國家更加簡易而見效。比如說,基辛格(Henry Alfred Kissinger)、奧爾布頼特(Madeleine Jana Korbel Albright)、賴斯(Condoleezza Rice)都是由大學教授轉任國務卿;現任的國務卿蒂勒森(Rex Wayne Tillerson)之前是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的董事長。美國各大基金會的研究人員經常會轉任聯邦政府各機構的官員;許多退任高官也經常會擔任基金會的理事或是高級研究員。
雖然美國政府整體上是為工商界服務的,但是工商界的利益並不一致,政府內部也因此有不同的聲音。身為五星上將的艾森豪威爾總統(Dwight David Eisenhower)在離任前就警告政府要慎防軍事部門和軍工企業綜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的過度影響。他這段話經常會有人重提,說明令他擔心的情況仍然存在。
文化傳統、社會風氣、學者修為
大學教員是現代大國智力構建中的重要力量,因此大學教員的態度與作為對國家發展的意義重大。我在匹茲堡大學的同事,哈佛歷史學博士羅友枝教授(Evelyn Rawski,夏威夷出生的第四代日裔美國人)在哈佛學了滿文,後來到北京研讀了許多故宮的滿文檔案;1996年她提出清王室並未真正漢化,他們是以不同的文化身份統治滿蒙漢藏回幾個疆域。這觀點引起史學界很大的爭議,但是似乎沒有人引用滿文資料來反駁她。「新清史」爭議給我的啟發是:一個學者要肯於學習一種或幾種有用的文字,甘於鑽進文獻裏一長段時間;無論能否因此而立一家之言,都是為學苦與樂的一部分。
持這種態度的學者,歐洲、美國、日本相當多,中國目前還較少。也許是受到「學而優則仕」和「光耀門楣」傳統思想的影響,中國有些學者稍微做出些成績就想當官,或是在媒體上出名,不願長期潛心鑽研學問。
再者,今日中國社會還處於財富積累的初期,社會上充滿了笑貧炫富和急功近利的現象──產業界大多重營銷,輕研發;一些學者們也難免受到影響而不願長期「坐冷板凳」。等中國社會發展到更高的階段,大家都不愁溫飽,子女教育不再是重大經濟負擔時,社會風氣應該會有改變,學者的修為也就更容易見到。
還有一點,我們也不能忽略歐美社會源自希臘文明和基督教傳統基督教因為真理已由上帝啟示,所以求善;希臘文明則注重求真。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運動之後,基督教的信條變得寬鬆了,古希臘人求真的精神被歐洲人再度重視。反觀中國,我們的社會價值觀一直是由道德主義和實用主義主導。很少人問「真理在何處」?多數人會問「應該做什麼」和「怎樣做最有用」?求真的傳統使歐美學者更願意通過邏輯辨析去找尋答案。而許多中國學者經常是先有「正道」在胸,然後秉承「允執厥中」的古訓,不願刨根問底和「較真」。由此看來,中國和歐美的文化傳統對學術發展肯定有不同的作用。
智力構建的必要性
十萬年前,現代智人走出非洲,依仗腦力逐漸成為地球的統治者。
一萬年前,地球變暖,動植物繁殖加速,人類開始有意識地生產食物,自此進入文明時代。
一千年前,人類聚落已遍及五大洲,開始在南太平洋東南部的一些島嶼上(如新西蘭)定居。當時世界不同地區人口的發展程度很不相同,有數百人構成的部落,也有同一政權統治的包括上億人口的國家。期間的區別主要是一個群體的生產力,而群體的生產力既和他們所處的地理環境(如平原、高山、叢林、沙漠、海濱)有關,也取決於他們是否能向周邊群體借鑒。公元11世紀初,全世界最發達的文明區都在歐亞大陸的溫帶。從西邊算起,有(1)西歐信奉基督教拉丁教派的日耳曼人的封建農業文明;(2)地中海西部信奉伊斯蘭教的摩爾人的農業及工商業文明;(3)地中海東部信奉基督教東方正教的工商及農業文明;(4)西亞信奉伊斯蘭教的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的商工農牧混合文明;(5)南亞信奉婆羅門教的印歐語人口和達羅比荼人共建的農業和工商業文明,以及(6)東亞漢民族儒道佛信仰幷存的小農經濟及工商業文明。當時全世界最先進的社會是中國的北宋。京城開封人口多達一百萬,而火藥、指南針、活字版都是中國在北宋時發明的。
一百年前,人類已能以量子論認識微觀世界,發現了生物遺傳的基本法則,還能克服地心吸力在天空翱翔──古生物學、考古學、人類學、語言學、古文字學揭示了人類的發展史。1917年,俄羅斯發生了十月革命,美國則先後推出了電燈、電話、電影、飛機、交流電、無線電廣播等發明。人類在20世紀以美國為前導開始了一次智力的飛躍。與此相對照,十幾萬名幾乎都不識字的中國勞工在一次大戰後期被英國和法國招募到歐洲,從事挖戰壕、搬貨物、掃街道等工作;中國北洋政府用勞工代替士兵加入協約國,希望戰後可以收回德國在山東的權益。戰爭結束後,美、英、法等國在巴黎和會中決定,德國在山東的權益由日本接收。這個決定在中國觸發了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此時中國不會製造縫紉機、鐘錶、自行車;沒有人通曉絲綢之路上的古代語文,也沒有學者在敦煌、樓蘭和吐魯番考察文物。當時中國的智力資源就是這樣。
經過了30年的戰亂和70年不平坦的工業化和市場化,中國現在已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今天,人類已進入人工智能的時代;要實現中國夢,沒有任何事情比提升民智、厚積英才更重要。
中國智力構建的選項
一個現代大國要從事智力構建,首先是要把小學、中學辦好。如果小學、中學教育能夠給予學生基本知識,啟發他們的好奇心和求知慾,並且培育青少年的公民素養,國家的智力構建就已經完成了一半。
其次是辦好大學教育。許多國人對當今的大學教育批評得很嚴厲,諸如「官僚化」,「行政化」,「只建大樓,不見大師」,「上面逼著出論文,教員懶得理學生」等。平心而論,這些現象在多數大專院校裡都能找得到;主其事的官員們真的必須要加以正視並切實改善了!但是,回想1919年至1949年間,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的畢業生累計不過1,500人,1977年對比年恢復高考後的入學人數,誰願意回到過去的「少而精」狀態?
今年參加高考的應屆畢業生和1977年年入學的「老三屆」時隔40年,究竟哪一批學生受的教育能給他們更豐富的知識和更廣闊的視野?作為40年來有機會持續觀察的個人,我認為進步是明顯的。查找不足不是否定成績,我們現在面對的問題是如何培養人才以支撐這個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繼續發展;把中國推進到按人口總數計算理應達到的世界第一大經濟體的地位。
再其次,但也十分重要的是尊重對知識的探索,鼓勵民間智庫,使它們成為展示民間智慧的窗口,而不只是政府既定方針的宣揚者。
我們需要清醒地認識,今日中國的智力資源並不強,在許多重要領域中的高端人才都不及人口只有我們四分之一的美國,也不如人口只有我們十分之一強的俄國,甚至不如人口更少的日、德、英、法諸國。
但是,我們無需因此妄自菲薄。美國從幼兒園到高中畢業(“K-12”)的教育質量近年來持續下滑,引起很多美國人的擔憂。根據標準測試,不少東亞和歐洲國家的學生成績都超過美國。我的觀察是,當前美國無論哪一行的高端人才的專業知識、敬業精神和創新能力確實是非常強,但是美國也有大量基層人口趨於懶散和放縱,缺乏學習的動力,在工作崗位上不能適應新時代日益增高的智力要求。
中國目前在全球人才比拼中還落後一大段。今後,不管別人是放緩還是加速,我們都必須下定決心,除弊興利,「惟精惟一」,加強自己的智力構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