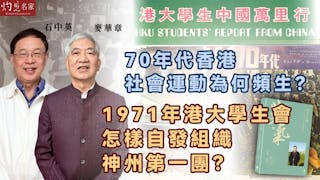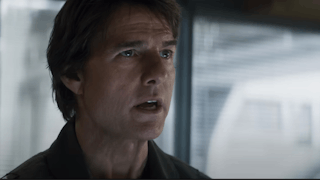承接上文討論未來本港經濟的發展,廖柏偉教授繼續剖析世界各國經驗對香港的啟示。
廖柏偉所在的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今年年初公布的一份報告指出,現今政府在增加經常性開支方面只有約300億元的空間,面對將來的財政困難,政府必須謹慎理財(註1)。他認為要小心利用這個空間:「扶貧是仍有空間可以做的,但當歐美國家都出現入不敷支的情況,紛紛縮減老年退休金福利之時,香港是否現在才開始呢?本港老齡化的問題比歐洲更嚴重,因為香港人口的生育率(fertility rate)比歐洲低,是全世界生育率最低的地區之一,同時本港人口的預期壽命是全世界最長之一,與日本不相伯仲。由此可見,將來香港長者比率相當高,工作人口比率相對低。現在本港15至65歲的工作人口與65歲以上人口的比率大概是5比1(撫養比率〔註2〕為18.3%),到2041年將會是2比1(撫養比率為49.7%)。簡單的說,將來從事生產的人會減少很多,這樣的年齡結構(age profile)如何支持一個全民的老年退休金?」
重蹈歐美全民退保覆徹?
不過,廖柏偉認為,這不代表不支持老人家,他讚揚去年新增至每月金額2285元的長者生活津貼:「跟以前的生果金不同,除了金額提高外,更增設資產審查,不是人人都有。津貼某些長者,例如我,作用不大。但若將我的一份集中給予有需要的人,一定比攤分到所有長者手上好,因為攤分一定會分薄,給有錢人是無意思的。攤分有兩個壞處,第一是每人所得有限;第二是成本更高,令社會負擔沉重。」廖柏偉指出回歸以來的17年間,若把一次性「派糖」花費掉的盈餘放在經常性開支,對扶貧來說更為有效,而最重要的是考慮哪些項目比較重要。

至於坊間有意見認為若全民退休保障能取代生果金及長者生活津貼,政府的額外付出並不太多(註3),他反駁:「那為何不增至6000元給有需要的老人家?為何要給我們每人3000元?要分清楚哪些人有需要,部分長者有積蓄、強積金及其他保障,為何要攤分這個福利?現在很多實施全民退保的國家接近破產,因為人口老化,結果只可以縮減福利,例如延遲領取福利金,由60歲延至65歲,同時降低金額。香港近年經濟增長放緩,由以往10多年大約4%,下降至近年約3%,正是由於勞動力下降。歐洲國家亦是一樣,他們發現退休制度的問題,我們無理由見到其他國家出問題,還要重蹈覆徹。」
參考歐美國家和鄰近的日本,廖柏偉認為,他們現在無計可施:「日本在人口老化方面比香港嚴重得多,看不到前景的經濟。他們現在的撫養比率已為3個工作人口對1個長者人口,到2041年時將會是3比2,而本港會是2比1。日本的解決方法是借貸,現在國債達GDP的240%,而本港政府現在負債是GDP的-30%,仍有儲備,但長遠來說還是會用光的。根據我們的報告,如果本港保持過往在教育、醫療及福利開支方面的增長速度,結構性赤字很快會出現,繼而用光儲備,到2041年時每年赤字佔GDP的比例大概升至23%,而政府債務將為GDP的154%。有人以為政府在嚇人,但1990年日本在經濟高峰、泡沫經濟爆破之前,國債只是GDP的60%,至今日已為240%,在短短20年間積累了100多個百分比。」
廖柏偉指出除了退休、醫療福利之外,其他國家更要面對一個本港不需面對的問題──國債及其利息,根據標準普爾(Standard & Poor’s)的人口老化報告(註4),日本在2040年的國債佔GDP比例為375%;美國為258%;而在歐洲,德國為130%;法國為163%;荷蘭為243%;先進國家總體平均為137%。「這些數據跟我們預測香港到時的債務水平差不多(約150%),而這些數字並非用來嚇人的。實際上本港人口老化問題比歐洲更嚴重,故此3900多億儲備實在不是很多。當然不是要儲起所有錢,但應小心利用這個空間,控制開支增長。」
新加坡靠三方面推動增長
不過,廖柏偉認為其他國家的做法對香港還是有參考性,新加坡是其中一例。他指出新加坡經濟增長靠三方面推動:勞動力增長、資本深化和全生產要素(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而面對今後本港的人口結構,在人口老化的同時,勞動力相應下跌,香港要走出困局,他認為要從人口政策入手:「首先,要填補短缺的勞工,最直接是輸入勞工和專才,這是新加坡正在做的,所以增長比香港快。第二,生產率是很難提高的,大部分鼓勵生育的政策成效都不顯著,所以只有依靠移民。香港人口老化問題到今日為止,仍未十分嚴重,是因為有移民。相反,日本是一個單一民族的國家,不願意接受移民,亦不輸入勞工,因此人口老化問題相當嚴峻。若日本開放移民政策,相信會有很多來自中國、韓國等國家的移民,但日本社會不可能接受。故此安倍經濟學(Abenomics)成效有限,因為人口老化、勞動力收縮等基本問題解決不了。而西歐的移民因為種族、宗教及生活習慣問題,造成嚴重的融合問題。相比香港的移民,雖然有文化習俗和生活習慣的差異,但沒有種族、宗教問題,已相對幸運,只是香港人仍然覺得難以接受。」如此看來,從經濟學的角度,香港的危機其實很容易化解。「但政治上能否做到是另一個問題。新加坡願意接受外勞,現在當地每10個人就有3個不是新加坡人,當然會有磨擦,但目前尚算管理到。」
第二,是資本深化,即是指投資土地、廠房及教育,廖柏偉認為香港遠遠做得不夠:「新加坡大規模填海造地,這是投資,但香港做不到。在經濟上,這是清晰的,但政治上做不到,因此是政治問題。」至於第三,是全生產要素,所指的是除了勞動力和資本的輸入,其他所有影響產出的要素,包括純技術的進步。「例如投資於研究開發(R&D)創新產品,又或者中港融合帶來的高增值服務,都會算入全生產要素。」不過,他堅持即使發展創新科技,傳統的金融業亦不應被輕視:「可能有人認為只有金融業得益,但它是一個相當大的行業,金融業旺盛會對其他行業有漣漪效應(ripple effect),例如飲食業、零售業。倫敦和紐約的人口都比香港多,但他們同樣是單靠金融業養活千多萬人口,而且生活水準很高。因此金融業對其他行業的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包括專業行業和服務行業。」

土地用途的選擇
開放人口政策,固然可以解決勞動力不足的問題,但從港人角度來看,無論是創業還是置業都需要土地,若讓大量移民進入香港,豈不令原本已短缺的土地資源更見緊絀?廖柏偉認為,土地永遠是本港問題的癥結所在:「這個問題是一定要解決的,然而港人比較不願意全盤去看待這個問題。香港確實缺乏足夠土地資源建樓,有人以為市區很多地,但其實空地不多,重建亦相當困難,因為清拆舊樓要先處理安置、賠償問題。我們要考慮自己想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大家僅住400呎的樓房,甚至部分人要住劏房,但外面空間廣闊,海岸線怡人,兼有龐大的郊野公園;抑或少一點郊野土地,每人的地方大一點呢?新加坡實際上人口土地比例跟香港接近,但他們的組屋接近一千呎,只是少一點郊野公園,海岸線也所剩無幾,因為填海後大部分會作商業用途。我認為我們要做一個選擇,現在香港在用的土地未到30%,是否要保持這個比例,而要市民住得擠迫?但現在香港人不嘗試討論這個問題,思考解決方案,而是一邊埋怨房屋短缺,一邊反對發展。增加土地供應要考慮的方案有很多,例如填海、發展郊野公園、綠化地帶等,最重要的是願意討論,但現在因為涉及政治問題,很多時候會卡着。我們不是沒有土地,只是不想開發。」
廖柏偉形容,新加坡政府很強勢:「新加坡的海岸線全是直的,顯示不是天然海岸線,而是填海得來的。結果是新加坡的增長比香港快很多。」數據指出,1997年時新加坡人口只有370萬,為同期香港650萬的58%,GDP則為香港的56.48%;但到了2013年,新加坡的人口躍升至540萬,為香港75%,但是GDP已增長至香港的108.73%(註5),可見其人均GDP及總量都在香港之上。相對於新加坡,香港政府更顯得弱勢。廖柏偉說:「(對於香港的問題)經濟學的應對方法其實相當清楚,但因為涉及政治問題,很多都執行不到。」
註1:<地價收入與政府財政——政府可否增加經常開支>,廖柏偉及林潔珍,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2014年2月。
個人介紹
廖柏偉教授為普林斯頓大學學士和史丹福大學碩士及博士,香港中文大學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研究教授及經濟學榮休教授。曾任大學副校長、經濟學系系主任、經濟學講座教授及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創所所長,現兼任香港中文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主任、東亞經濟學會副會長。研究專長為應用經濟學理論、不確定定理、勞動經濟學、行政人員薪酬、金融市場以及中國和香港經濟。
熱心服務社會,出任多項公職,包括香港金融管理局轄下香港金融研究中心董事,現為前任行政長官及政治委任官員離職後工作諮詢委員會委員及長遠財政計劃工作小組委員。曾任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非執行董事及其轄下薪酬委員會主席、香港特別行政區策略發展委員會委員、航空發展諮詢委員會委員、臨時最低工資委員會委員,以及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及政治委任制度官員薪津獨立委員會成員。1999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頒授銀紫荊星章,以表揚其「傑出的學術成就及在公共服務方面的卓越表現」。2006年獲委任為太平紳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