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黃仁宇當步兵出身,清楚明白要向最大量觀眾講解中國失敗真相,要快而準刺中核心。胡導既然代表黃氏教育群眾,我認為,要觀眾領悟黃氏從新角度來解析中國歷史,最重要。

洪秀柱走「正宗」的國民黨路線,卻遭到黨主席嚴詞批評,意味原本主張統一的國民黨已經揚棄了原先的基本路線。

王船信仰是台灣西南沿海重要的民間信仰,王船祭則是王爺信仰中最具代表性的宗教科儀。三年一科的東港王船祭,更名列台灣最有人文特色的民俗活動。

作為地理和文化雙重意義上的自我流亡者,奈保爾不止在印度,在任何地方都難以找到終極歸屬感。疏離感與他永生相伴。

古之才女,各有故事。「易求無價寶,難得有情郎。枕上潛垂淚,花間暗斷腸」……

稱謂得小心使用,方不失大體。容若繼續舉例說明。

吳天章記憶中的基隆,跟他的童年生活一樣深刻。活靈活現的有因戰爭經常上岸的美國水手,提供性服務的妓院處處,還有愛欲與別離。

對於靜思之美,我的詮釋是:靜坐水窮處,倚深山觀景平台,遠眺自然景觀,觀賞江淹(444—515)在〈別賦〉中的日月輪替:「日下壁而沉彩,月上軒而飛光」;在虛靜中「神遊」歷史的時間廊,尋覓人生腳印,思索歷史興亡。這就是讀書人從「場景」到探索的靜思之美,這就是思考者擁抱的「超然」。

如果說去殖化不足,影響更大、更全面透徹的,還有教學語言。可以肯定地說,香港沒有殖民地歷史,就不會採用英文作為教學語言。

來到美國,我是從金字塔底層做起,靠自己雙手掙來的一切,對自己不僅學會了尊重,而且充滿感激,我再沒有感到自己的渺小。

來到美國,我是從金字塔底層做起,靠自己雙手掙來的一切,對自己不僅學會了尊重,而且充滿感激,我再沒有感到自己的渺小。

「明天再讀吧,今天趕稿,累死了」的現實和藉口,很快就把書推到書桌的邊緣,最後它沒趣地自己爬上了書架,與灰塵為伴,從此落入「白頭宮女在,閒坐說玄宗」的淒涼境況……

我入職之後半年,明原堂開幕。十周年堂慶之後半年,我離職他去。我本來就不準備長期任職舍監,計劃中是五至十年。這時離開,應是最理想不過的了。

陳若曦以獨特的視角,穿梭於中國及台灣的重大事件之間。「我現在回到台灣20年了,我對台灣怎樣看呢?台灣不錯,經濟繁榮,可是這繁榮是犧牲環境換來的。」

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焉,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

陳若曦以獨特的視角,穿梭於中國及台灣的重大事件之間。「我現在回到台灣20年了,我對台灣怎樣看呢?台灣不錯,經濟繁榮,可是這繁榮是犧牲環境換來的。」

胡耀邦選擇了用一個折衷的方法解釋「一國兩制」——他對陳若曦說,中央給予西藏的,就是高度自治,更提議陳若曦有空可以到西藏看一看……這開展了陳若曦另一條文學道路……

胡耀邦選擇了用一個折衷的方法解釋「一國兩制」——他對陳若曦說,中央給予西藏的,就是高度自治,更提議陳若曦有空可以到西藏看一看……這開展了陳若曦另一條文學道路……

你真的用對了這些稱謂嗎?

誰又會想到,一位年邁拾荒婦的日常,竟得以拍成紀錄片,在「華語紀錄片節2015」亮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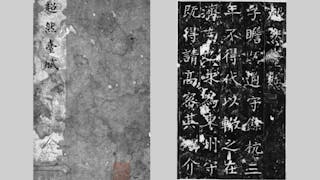
人人爭說香港的制度,卻無人提及「超然」一詞的本意。本文以語意學的視角,分析「超然」的意涵、虛靜的審美情趣。

我有兩段在該院任教的因緣,又長期擔任校外委員。這樣一算,彼此「糾結」了前後20年,從它13歲開始,到它33歲為止。我的學術生涯既與它共同成長,我也大致見證了它的承先與啟後。

且慢,我要在這裡停下車來,只因路旁的楓林十分可愛,要停下來享受一下紅葉滿谷的氣氛情調。投宿嗎﹖遲點也許無妨。

年輕時,陳若曦留學美國,後來她跟前夫因嚮往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前往中國居住。沒想到的是,夫婦倆遇上了文化大革命。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文革,從陳若曦口中說出來,一字一句都彷如昨天……

中學時上歷史課,知道了10月10日是推翻滿清帝制,建立民國的重要日子。為貼近歷史現場,筆者利用當年的報道作圖片說明,其中不少引自《泰晤士報》(The Times Peking)駐華首席記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的直擊匯報。

年輕時,陳若曦留學美國,後來她跟前夫因嚮往理想中的社會主義,前往中國居住。沒想到的是,夫婦倆遇上了文化大革命。發生在半個世紀前的文革,從陳若曦口中說出來,一字一句都彷如昨天……

中學時上歷史課,知道了10月10日是推翻滿清帝制,建立民國的重要日子。為貼近歷史現場,筆者利用當年的報道作圖片說明,其中不少引自《泰晤士報》(The Times Peking)駐華首席記者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 的直擊匯報。

是物色還是物識?角色或腳色?

生活與生存之別,在於是否沒有心靈只剩空殼。生命只剩空殼的人,是為掛空。

青蒿素和《詩經》所記載的「蒿」有沒有關係,我不知道,但單就字面來說,已經非常巧合,或許這是屠爸爸給女兒命名時不能逃脫的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