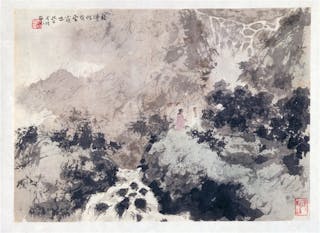張作霖雖然是土豪出身,但極愛國,愛民族。日人早想咬入東三省,均被他或軟或硬擋回。早前日人曾提議把日軍改穿奉軍制服替奉系作戰,被張一口拒絕。

史提芬史匹堡是戰後長大的獨立電影人,也是自由知識分子進軍荷里活的代表人物。這一代人對父母的反抗,首先表現在對外星人來地球的恐懼,提出另類觀點:為何假設外星人都是敵意的侵略者?為何人類不能與外人做朋友?

不會讀書的人,只活了一次;會讀書的人,活過一千次人生。

金庸武俠小說魔力無遠弗屆,有華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說,連帶與金庸小說有關的「副產品」也多姿多彩。筆者最近從海外購入一套漫畫版的武俠小說《天龍八部》,可說是副產品之中的佳品,它絕跡江湖已數十年。

由亞洲協會香港中心(ASHK)主辦,潘燊昌博士和灼見名家贊助的《復甦生息、逆中求存、重振旗鼓》展覽,展期將延長至9月30日,並將舉辦系列網上研討會,加強與社區的聯繫。

那些年港台推動閱讀風氣,多次舉辦徵文比賽,外界反應不錯。我們有機會與來自中、港、台作家同枱吃飯,想知道他/她們不寫作的時候,日子是怎樣過的。

中古至今,中華文化一脈相承,軟性共融是一大特色。倘若西方的政客,能從中華文化縱深角度了解中國,文化情愫在前,當不會再走圍堵中國之路。

中華文化的核心價值是重中之重,是教學上最難處理的問題。但這些皆可從豐富的詩詞經典中找到素材,聯繫學生的生活實踐,古為今用,在潛移默化中得到品德情意的熏陶。

嚴格來講,共產主義與儒家政治哲學抵觸不大,而其修身學哲學,或許在這個缺乏理想、缺乏宗教信仰、缺乏道德、一切向錢看的今天,能夠發揮一些社會和諧穩定作用。

吳祖強教授在國內外音樂界享譽盛名。早年參與創作多部經典作品。「文革」後首次在京公演,著名指揮小澤征爾聽後感動流淚,還親自指揮中央樂團。

深情書寫30位藝文界名人,包括劉德華、鍾楚紅、王菲、周潤發、張艾嘉、陳百強、關錦鵬……記敘他們甚或燦爛,甚或黯淡,甚或缺憾的人生風景。藉由文字為他人獻上真摯的祝福,為自己留下溫暖且芬芳的文學美醇。

香港愈來愈多人不斷在說話時,將原本的粵語普通話化了,包括字音、詞彙及語法等三方面。但其實,粵語詞雅於普通話語詞。

張作霖年輕時曾淪落街頭,甚為窘逼,四處以散工為活。從他後來發跡看來,張作霖的觀人於微,處世待人得法,容易贏得人心,便是這個時候磨練出來的。

前清太史賴際熙1923年在香港創辦的「學海書樓」,到明年便屆100周年。學海書樓是香港最源遠流長的書樓,3萬多冊古籍現寄存在香港中央圖書館,令一個世紀以來在香港的國學香火得以延續。

17世紀是西方的分水嶺,理性拉開了人類的新序幕,笛卡兒高舉「我思故我在」的旗幟,將人類抬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為西方哲學從神學走向人學奠定了重要方向,這也使樹木出現了「從神聖到世俗」的巨大改變。

到了球場,由於酒精、搖頭丸和口號的感染,往往在比賽開始前,球迷早就陷入癡迷的狀態,真正開賽,球員的跑動和對抗,就成為意大利諺語中的「在桌球抬上蠕動的螞蟻」。

40歲之前底盤要做大。因為到了一定年齡之後,知識就只能在原有基礎上堆高,卻無法再擴大。40歲之前做成的底盤大小,決定了以後成就的大小。

對於樹,我很有感情。它擁有巨大的襟懷,能夠包容很多的複雜和世情。面對一棵年代久遠的大樹,就像面對一位閲盡滄桑,慈祥靜穆的老人。他看過的比你多,知道的也多,經歷得更多。你不用説什麽,他都明白你的心緒。

《華燈初上》中亮相的一眾陪酒女子,在日式酒店「光」販賣「曖昧」感覺。雖然每天見面,總愛吵吵鬧鬧,但她們皆不算心腸壞透之人,她們上班,做到敬業樂業,是有着做人的基本信念:「做好本分,不能騙人」。

鼎鈞先生的家是個具體而微的藏寶窟。買藝術品妝點自己的家,隨便普通人都做得到,但因鑑賞眼光高下便有雲泥之判;只買幾件有口碑的藝術品,自然不易落人指摘,但要多多益善的話,那可是要有「調兵遣將」真功夫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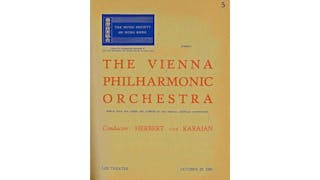
當時政府對藝術文化活動一毛不拔,香港音樂協會有見大會堂即將建成,於是接二連三邀請著名音樂家和團體來港演出。但協會其後煙消雲散,所主辦的節目也零散東西。

孔子是個虛懷若谷的謙謙君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認為「三人行心有我師焉。」,覺得「後生可畏,焉知來者不如今也。」遂稱項㯱為師,駕車繞道而行。

香港一直都是一個很好的交流中心,小交很多時都會將香港的樂人、作曲家作品帶到國外,讓全世界傾聽香港的聲音。但另一方面,政府應該對香港整體的文化藝術,提出一個更為明確的發展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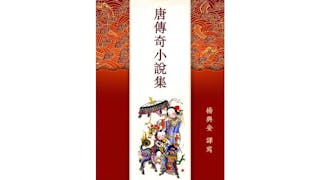
唐代小說何以稱傳奇呢?為什麼時人對唐代傳奇的認識比唐詩貧弱得多?

筆者一向相信,凡多於一個方言區所共用的詞語,我們若追尋其本源,當會發現,該詞通常是200、300年前,甚至是超過1000年或2000年以前的古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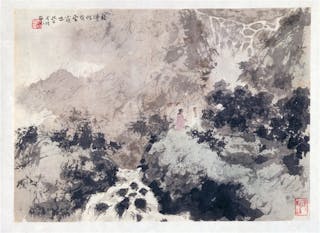
恩師的教導反覆地在耳邊叮嚀:「學畫是要細細感悟,不可急於事功,用審美陶冶心靈,慰藉精神所失,修煉情操人格,再探索筆墨自由的空間……適應隨時代而求變!」

人論吳氏做官數十年,統治過幾省的地盤,帶領過幾十萬的大兵。他沒有私蓄,也沒置田產,清廉有名,比較他同時的軍閥橫蠻肆欲,腰纏千百萬,實難能可貴。

區聞海談吐溫文,神情懇摯,既有文人的幽微細緻,亦有醫生學者的審慎認真。他對香港疫情的看法,突顯了他對生命倫理的關注……

1973年我到浸會學院讀傳理系,傳理系規定,所有學生要選修別系一、兩個課程,翌年我便選讀司馬長風先生的「中國近代史」。半世紀之後回憶這段師生緣,仍然記憶猶新。

自香港回歸,由於種種原因,歷史教育和青年政策被長期忽略,錯過了黃金時機,代價極大。目前正是改變/提升本地青少年素質的大好機遇。在此有賴政府的規劃和推動,以及文化機構的運作籌措,假以時日,必見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