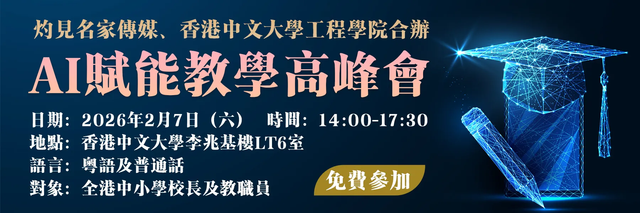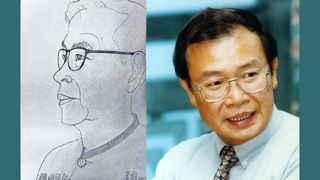「娘……娘……」劉英大步跨進四合院的門坎兒,長長的髮辮左右舞動,朝着西廂放大了嗓門喊娘。
第一回:阮玲玉死了
「阮玲玉死了……娘……」
13歲的劉英在天津塘沽漁村是個異類。眼大、鼻高、口也大,一雙大腳,一米六的身高經常往天主教堂跑。村裏的老人們叨嘮她那大腳那衝勁,哪一點像閨女?
劉英從不理會村人的閒言碎語,她這時已哭成了一個淚人,一巴掌推開西廂虛掩的木門,木門的呀呀聲還在,劉英已經一頭撲倒在床上母親蔡鳳的身上。
「別胡說,娘好好的,沒死!」
蔡鳳早已習慣女兒的突襲,她操着濃厚的天津口音,有氣沒氣地拍打女兒的臀部。1935年5月,蔡鳳已經過了35歲,他19歲嫁入劉家,當時虛報年齡為16歲,那時的玲瓏身段早已不見了,體形膨脹了一倍,然而,五官還是很精緻,畢竟還保留着八分之一俄羅斯人血統,這特徵也遺傳給了劉英。
蔡鳳嫁入劉家五年間生了三男一女,自己也落得一身的婦女病,每天倚賴福壽膏來去除痛症,抖擻精神,為四條漁船的漁工發工資、配置物料、查帳,還要定期檢查灶頭、睡炕內的木材數量是否足夠;份內的工作還包括監管廚娘的烹飪,照顧婆婆、丈夫、四個孩子的三餐;從雞鳴到月升中天,每天只有這一刻,黃昏的陽光把西廂房子拉出一道長長的陰影,雞不鳴、鳥不叫,正是蔡鳳每天最享受的寧謐時光。
今天的美妙時光,卻被自己寵愛的小女兒破壞了。
「誰死了?臭丫頭!」蔡鳳擰着劉英紅紅的小臉追問。
「娘……阮玲玉……阮玲玉死了!」
「什麼?阮玲玉死了?」這消息把蔡鳳從福壽膏的迷惘中嚇得清醒過來。一個多月前,她還與一眾女教友在天主堂看了阮玲玉主演的《三個摩登女性》電影。阮玲玉飾演女主角周淑貞,尖銳地控訴舊社會對女性的束縛,勇敢的反抗,讓蔡鳳看得淚流滿面,劉英也看得哭起來。
「真的嗎?誰說的!」蔡鳳不敢相信。
「真的!Adriano說他從《申報》和《聯華畫報》看到的消息。」劉英收起了淚水鼻涕,一臉認真地回答。
Adriano是塘沽區天主堂神父約瑟夫的養子,身高1.8米,俊俏精緻的五官,加上壯健的體型,真有當年約瑟夫的影子。1928年初米蘭耶穌會派Adriano協助高齡的約瑟夫做布道工作。1930年約瑟夫以75歲高齡返回米蘭。29歲的Adriano全面主持教堂事務,塘沽教眾們暱稱他為安奴。
「安奴說阮玲玉是受到大眾輿論壓力自殺的。」
「誰是大眾輿論?」蔡鳳問。
「大眾輿論不是一個人!你說一句我說一句,這就是大眾輿論。」劉英完整地覆述了安奴的解釋。
「阮玲玉多年受到同居男友生活上的折磨,於是離開了他,認識了另一位愛她的男人,可是前同居男友四處說她不守婦道,上海的報紙就罵阮玲玉通姦,亂搞男女關係,結果阮玲玉受不了大眾輿論壓力,服毒自殺。」
劉英怕她娘不信,又把安奴告訴她《申報》的內容補上:「《申報》『自由談』也說了,阮玲玉大殮當天,靈堂放滿了花籃,殯儀館大廳門前一幅大的白布橫幅,寫着『如此人生』四個大字。」
「男人可以三妻四妾,女人要是膽敢離婚,就會被人家罵,你看多麼的不公平…」劉英小臉漲紅,心跳加速,一口氣把安奴對她說的話,原原本本一字不漏的抖了出來。
「這那是13歲女孩能說出來的話?」蔡鳳聽後沉默良久,興許是想起了自己的身世,嘆了一口長氣,「女人……苦命呀……」猛地把煙筒內最後一口福壽膏煙吸了下去,頓時陷入神志不清的狀態,劉英見慣這場景,不再騷擾娘,乖乖的退出了西廂。
第二回:喀秋莎
3 6.6-5 65 4 32 36- -04 22 3 11 - -(歌譜)
蔡鳳每每在半睡半醒的狀態,腦海總是莫名其妙的響起了這段雄壯的旋律。
7 33 17–6–7 33 1 7 6 (歌譜)
蔡鳳13歲那一年的冬天,是鵝毛雪的一個冬天。天津妓院來了兩位客人。
一位是矮肥的俄羅斯商人,左手一個皮製箱子,右手一個手風琴;陪同他的是一位黝黑高瘦的東北人黑狗子,左眼只有一個黑洞,右眼更見炯炯有神, 像是肥矮人的保鑣也像是僕人,左手右手各持一個大包袱,右肩還背着一把大工鏟,鏟頭閃閃發亮,顯然是保養得很好,還是經常使用的工具。
天津妓院在公共租界,頗有名堂。
自從八國聯軍入京後,北京以至鄰近三省的妓女,紛紛走到天津租界避禍,天津又是東北往北京下江南必經之地,交通商貿匯集,商旅發達,娼妓業也興旺起來。
清末民初的妓院分為三等,最高級的稱為「店」,老闆多為東北、直隸甚至俄羅斯人,負責運營的女老闆叫「假母」,又稱「領家」,即是「老鴇」。領家的居所稱為「良房」,客人進店,由男僕引進,捲簾大呼見客,店內妓女出來與客人打招呼,客人選中某個妓女相陪後,就開始了一整套的妓院社交儀式,包括先行為客人「打茶圍」,先奉「乾濕」,即是瓜子、蜜餞、水果、茶,喝茶期間客人可以要求妓女彈唱小曲,打牌、陪抽大煙,這時「領家」觀察客人是否出手闊綽,客人也在觀察所選的妓女歌藝言談是否符合自己的要求。高檔的妓院,客人通常要來「打茶圍」三四次,培養出與妓女的感情,才能提出與妓女過夜的要求。
天津下等的妓院稱為「狗男女」,沒有高等妓院的繁瑣程序,客人只要相中某個妓女,即可過夜。由於行為像狗一樣急於求歡,所以「狗男女」一詞又被引伸指那些無媒苟合的男女。
矮胖的俄羅斯商人弗拉基米爾(Vladmir),已經是第三次到天津妓院「打茶圍」了,天津妓院的俄羅斯「領家」葉琳娜(Elena)很熱情地招待同鄉,葉琳娜雖然年近40,面龐五官依然精緻,下圍是上圍的一倍,1.7米的身高,看上去像個巨無霸,添加了這位「領家」的氣勢。
酒過三巡,「領家」問弗拉基米爾,你帶着的手風琴會拉嗎?
弗拉基米爾只顧着喝酒,沒有回應。陪酒的俄羅斯金髮女郎安娜也在起哄,說弗拉基米爾根本不懂手風琴,問他是哪裏撿來的?
弗拉基米爾哪裏受得了這般嘲諷,一把拿着手風琴,熟練地拉出了旋律……黑狗子也熟練的伴唱着:「喀秋莎站在海岸上的懸崖,歌聲好像明媚的春光,明媚的春光。」
在「良房」門外候着召喚的蔡鳳第一次聽到這旋律,嚇了一跳,這不正是我腦海中經常響起的旋律嗎?再仔細一聽,歌詞提到了……喀秋莎……她腦海頓時一片空白……也不知道失神多久,忽然聽見室內人召喚自己添加瓜子水果,這時才清醒過來。
蔡鳳清楚地記得,在十歲生日那一天,撫養她的妓院廚工張媽給她看了一張發黃的丁方照片,是一位臉容親切、穿上戎裝的中年婦人照,照片背寫上Katyusha喀秋莎幾個字。張媽說:「這是你的生母,記好了,我替你保管着,等你結婚後才交給你。」
……
蔡鳳捧着瓜子生果盤麻利地返回「良房」,室內已經鬧成一片了。
「你他媽的只會唱喀秋莎,我卻是親眼見過喀秋莎的!」黑狗子酒喝多了在發酒瘋,居然罵起主人,弗拉基米爾並不在意,正把頭湊近安娜,享受女兒香。
「你說說啊!」葉琳娜頗感興趣,安娜也起哄要他詳細說來聽聽。
「1904年……」蔡鳳自少好學,經常得到逛妓院的名士、商人提點,她心中一算:「那時我才四歲啊!」
「1904年……」黑狗子又重覆了這個年份,顯然酒精發揮了作用,讓他又肥又大的舌頭,繞不過這句話。
「知道了,知道了,不就是1904年嘛!往下說!」葉琳娜霸氣地引導黑狗子往下說。

「那一年日俄大戰,爭奪旅順軍港……」跨過了1904年這個坎,黑狗子又可以順溜溜的說下去了。
「剛過完年,港口的俄國戰艦受到日本軍艦的突襲,不到一個月,日本大勝。岸上住得遠一點的人,根本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接着陸地戰又打響,那可慘了!港口外圍山嶺到處炮火轟轟……」
黑狗子喝了一大口黃酒,接着說:「那時我在旅順為俄國人挖煤,臨時被抓去搬運屍體,第一天搬了10具,第二天搬了20具,到了年底,這屍體沒辦法搬完,完整的屍身也愈來愈少,不是斷頭,就是沒有四肢,或是肚皮破開,腸臟流到一地,撿也撿不回。」
「別光說屍體,好嚇人……」安娜插話了,「入正題吧,喀秋莎怎麼了?」
「喀秋莎……」弗拉基米爾推開安娜,喝了大口黃湯搶着說:「她做的大列巴餅真好吃,外脆內軟。」「她會打仗嗎?我可不知道。」弗拉基米爾自問自答。
一眾人把目標轉向了弗拉基米爾。
「日俄戰爭前兩年,我在旅順海軍軍營的飯堂吃過她做的菜……我沒有看過這麼漂亮的廚工,她丈夫也在同一廚房工作,樣貌平平,配不上她,可是能看出來,她很愛她的丈夫。」弗拉基米爾看見大家很專心聽他講話,興致更高了。
「我當年是華俄道勝銀行牛莊分行的經理,與海軍軍營有業務來往,軍官見了我,也得趕緊上前問候,她卻正面也沒有看我一眼,只是整天笑咪咪的看着丈夫。」
「那是她沒有眼光!」葉琳娜奉承地說。
「屍體……到處是屍體……」黑狗子又絆倒在屍體這個坎上了。
「別屍體屍體的,往前說!」葉琳娜再次顯示出俄國女子的厲害本色。
「她一槍……噓……倒一個……一槍一個,203高地……203高地……」黑狗子喃喃自語,明顯地酒量到頭了。
「203高地怎麼啦?」安娜焦急地問,門外蔡鳳也很焦急的想知道。
黑狗子卻突然呼聲大作了,誰也沒有辦法再要他吐出一句話來。眾人這才發現,弗拉基米爾也昏昏入睡了。第三次的「打茶圍」也就這樣打住了。
第三回:日俄大戰
三年後蔡鳳出嫁劉山海,出嫁前夕,張媽按照傳統為蔡鳳梳頭,又將一張丁方大小的肖像照交給蔡鳳,「這是你媽!」
張媽長年在廚房工作,雙手經常濕水,患上了嚴重的類風濕, 十隻手指已經變形成了雞爪狀,蔡鳳從鏡面上看見一對雞爪在她的頭髮上上下下,有一種說不出的難受。
張媽一邊為蔡鳳梳頭一邊說:「你母親是中俄混血兒,中文名叫喀秋莎,是俄國旅順海軍軍營張順生廚師的妻子,我姪子張連生和張順生是同鄉,在同一個廚房工作。喀秋莎的祖父是庫頁島上的俄國漁民,他後來去了海參威與一位中國廚房女工結婚生了伊娃,伊娃長大後又與一名中國廚師結婚生下了你母親,所以你們幾代都是做廚房的。」
「我爸媽是怎樣死的?」蔡鳳焦急地問。
「別焦急,你聽我說啊。」
「日俄開戰,你爸從港口廚房調到山嶺的前線,為守軍煮食,你媽本來是不需要去前線的,可是她放不下丈夫,把四歲的你交給我侄子照顧,自己跟隨丈夫去了前線。」
「聽我姪婦說你爸是被炮彈打中在你媽懷中斷氣的,你媽放下剛做好的大列巴,撿起了地下的槍支,跟日軍打了七天七夜,打到子彈也沒有了,最後……最後……」張媽沒有法子說下去,梳子掉落了,張媽彎腰拾梳,趁機抹去眼角的淚水。
「張媽……最後怎麼了,您可得告訴我,不然夫家問起我娘是怎麼死的,我怎麼回話?」
張媽一想,這也是,咬緊牙關,擠出了這一句:「日軍把你娘的頭斬了下來……撿屍人說怎樣也找不到你娘的頭顱。」
轟的一響,蔡鳳腦袋像被人重擊了一下,《喀秋莎》雄壯的旋律又響起了。
張媽說:「日軍大勝後進入旅順市,在俄軍軍營家眷樓發現我姪子帶着一位俄國相貌的女童,懷疑我姪子是俄國間諜,即場斬首。我姪婦趕忙背着你連夜逃離旅順,在東北地區輾轉走了一年時間,最後才回到老家天津,把你交給了我。」
就這樣,蔡鳳懷着複雜的心情,離開了熟悉的妓院,進入了一個陌生的家庭。
第四回:存亡勢態
蔡鳳不愧是喀秋莎的女兒,有着強烈的生存意志,短短五年間,就把封建守舊的劉家各成員治理得貼貼服服;她五年生四胎,第一胎就是男嬰,解決了劉家無後的憂慮,第二年生了劉英,接着的三年裏又生了兩位男孩,蔡鳳在家族裏的地位自此無人能撼動,加上蔡鳳能寫會算,把家族的漁船船隊管理得井井有條,又適時地聘用臨時工,開墾了幾百畝良田,族中長老主動請她當大當家。
蔡鳳的減壓方法,就是去教堂做禱告。
按照劉家家規,兒女滿一周歲就帶去教堂受洗,蔡鳳也因此與約瑟夫熟絡起來。
1928年的聖誕節,約瑟夫在教堂內播放20多年前的日俄戰爭紀錄片,這是安奴從米蘭帶來的,黑白影像不清的畫面也可以像觀眾感受到戰場上的慘烈狀況,蔡鳳抱着六歲的劉英,兩母女都眼泛淚光。
影片播放後,蔡鳳找了一個機會小聲的問約瑟夫神父:「你有聽說喀秋莎這個名字嗎?」
約瑟夫神父登時以不可思議的表情看着蔡鳳:「你說什麼?喀秋莎!」
「喀秋莎是我母親!」蔡鳳在約瑟夫神父耳邊說。
"Dio ti benedica",神父不自覺的用意大利語說了一句祝福語,還親吻了蔡鳳的額頭。
神父早年在俄國遠東地區及中國東北地區遊歷時,經常聽聞有關喀秋莎的事蹟,俄國詩人又編寫出喀秋莎的歌曲,激勵了人民堅決與軍國主義鬥爭。
蔡鳳趁機把內心的一連串問題向約瑟夫請教。
「日俄之間的十年宿怨……」約瑟夫說:「是這樣的, 1894年日本在日清甲午戰爭中取得了整個遼東半島,但是俄羅斯聯同德國、法國一起向日本施壓,逼日本退還遼東半島,那時日本的海軍艦隊數目,遠遠不如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陸軍人數也不足,只好把吞到口裏的熟鴨子吐出來。」約瑟夫畢竟年紀老邁氣力不足,說到這裏,停了下來。
熟讀亞洲歷史的安奴接力說:「從1894年到1904年的10年間,日本用清朝的甲午賠款,建造了許多許多戰艦,成為亞洲海軍實力最強的大國。到了俄國強佔旅順大連,日本就認定對帝國構成存亡事態,於是不宣而戰,一舉殲滅了俄羅斯的太平洋艦隊,取得了海上的優勢。」安奴可不像約瑟夫那樣安靜的敘事,說着說着就手舞足蹈、興奮異常,畢竟還是20多歲的小伙子。
約瑟夫看出了蔡鳳的疑惑,補充說:「我知道影片上死傷的多是日軍,不是俄軍,因為影片上的是日俄之間的陸上戰爭。」
安奴馬上補充,因為他兩年前在日本遊歷,聽到了很多關於這場戰爭的細節。「負責陸上戰爭的是日軍第三軍司令乃木希典,他開始用的是傳統的軍事戰術,是用敢死隊強衝203高地碉堡,再進行近距離搏殺。但是俄羅斯軍隊這時已經發明了速射炮,一分鐘可以打出240發子彈,火力足以讓日軍無法接近碉堡,打了幾個月下來,日軍傷亡慘重……」
「那麼日軍是怎樣贏得戰爭的?」蔡鳳問。
「日本帝國的陸軍和日本帝國的海軍是有矛盾的,彼此並不互相支援,後來海軍看見陸軍的死傷太慘重了,加上俄國遠東地區援軍即將開到,於是海軍把軍艦上的28厘米大炮拆卸下來,用軌道推上高地,近距離對高地碉堡炮轟,這樣才把堅固的碉堡工事打垮,日軍敢死隊才能攻進去,贏得這場戰爭。」安奴說。
神父約瑟夫也不甘示弱,說出了讓安奴信服的數據:「這一場陸戰中,日軍死亡27000人,俄軍死亡人數也有7000人,被俘虜的軍人32000人,在整場日俄戰爭中,俄軍死亡人數79000人,日軍死亡人數高達9萬人。」

「日俄之間的血海深仇,100年都化解不了。」約瑟夫頗有感慨的作出了準確的預言。
在約瑟夫無言的時刻,安奴及時作出了總結:「說來也有神的旨意,乃木希典在旅順一戰立下大功,晉升為伯爵,他的兩個兒子卻死在這場戰爭中。1912年明治天皇駕崩,乃木希典和妻子一起自殺來答謝皇恩。」
教堂外落着毛毛的雨夾雪,最是寒人;教堂內安奴新近帶來的留聲機播出溫暖的聖誕頌歌曲,提示聖誕的來臨。
神父開始用意大利語為亡魂禱告,蔡鳳聽得淚水漣漣,她身旁六歲的劉英,長長的眼睫毛也沾滿了晶瑩的水點。蔡鳳心想:「這個丫頭到底聽懂了多少?」
蔡鳳跪地合掌禱告:「親愛的天父,讓我和劉英這小女孩免受戰禍,得享你的平安和喜樂……」
教堂外的雨雪變成了大雪紛飛,為喀秋莎、為日俄戰爭中的亡魂,舉起白幡……
蔡鳳與約瑟夫的一段對話,發生在1928年的冬天,不到三年的時間,日軍再以帝國「存亡勢態」為由,發動九一八事變,全面侵略中國。1940年,蔡鳳40歲,在日本軍刀的陰影下撒手人寰,與母親喀秋莎團聚了。
1940年,劉英18歲,風華正茂,她想學外祖母喀秋莎,拿起槍枝,為自己的理想奮鬥。可是……吃人的禮教、家族的責任、可畏的人言,都讓劉英在餘下的27年歲月中,節節敗退。
她結束生命的時候,也許會想起阮玲玉靈堂上的四字橫幅:「如此人生」。
這都是後話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