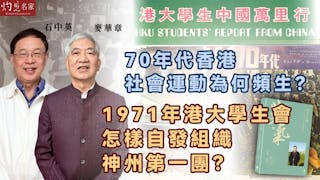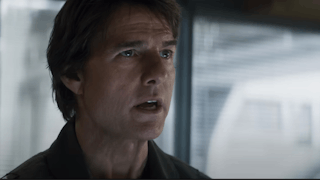本人最近的新作《世界級大都會──港深雙城的演化經濟地理學》中比較詳細的從一個城市演化的角度,分析了港深如何在不同制度卻又是鄰居的情況下,成長為這樣一個兩大比鄰都會的世界、獨一無二局面的過程。這個「雙城記」雖然主要是對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出現深圳特區以後這一段歷史的回顧,但最終希望找到的,還是今後發展的可能性。而我認為形成最有利於香港、深圳和國家發展的方案,首要的就是保持各自在大灣區、中國以至世界所扮演的角色。
大灣區概念 不是要消滅競爭
為什麼要在這個時點來討論這樣一個命題?因為筆者注意到,自從有了粵港澳大灣區這個概念和相應的國家戰略規劃後,一些人和媒體把加強香港與內地的關係,協調區域的發展等同於「一體化」。比如,內地有諮詢機構提出建議,成立一個跨境的管理部門,統一經營和管理香港和深圳兩個機場。類似的還有提議,在大灣區範圍成立一個統一的港口集團,經營大灣區境內所有的貨櫃碼頭。提出這種構思的,應該不是出於幼稚,而是在長期的習慣思維渲染下默認,一體化,或者說由一個機構管理多個有一定競爭關係的企業或者城市,就可以消除競爭帶來的負面影響,就必然是合理的優化過程,不需要論證。
事實並非如此。提出大灣區的目的是增加城市間的協調,但並不是要消滅競爭。更不應該被看作是減少一國兩制為香港帶來的獨特性。鄧小平先生提出「一國兩制」50年不變,以及在香港邊境建立深圳經濟特區,恰恰是他看透了特定的制度環境的必要性。我把這兩個特殊的城市的特殊制度稱之為「比較環境」。
港深兩個具有與中國內地和英美一般制度都不同的、兩者之間又不同的比較環境,構成了一個從歐美發達社會到中國內地所實行的制度之間的兩級漸變的制度空間。香港是在「一國兩制」下,中國與西方制度兼容程度最高的地方;而深圳是中國內地與香港兼容程度最高的地方,同時在整體制度上與內地一致。用兩個城市形成這樣一個中外制度兼容過度帶,是鄧構思的精妙之處,因為它假設了香港在制度上與國際自由主義經濟體兼容,同時通過在深圳建立與內地不同的「先行先試」改革開放實驗室,不斷調整其制度、法規、經濟和社會管治和運作模式,從而完成與世界市場經濟的銜接,而且不用貼上「XX主義」的政治標籤。
過去的40多年嘗試,證明上述「兩制雙城」作為一種中外兼容機制,行之有效。之所以行之有效,就是因為香港與深圳的不同,即前者主功能為對外兼容,後者主功能是對內兼容。

香港對外兼容 深圳對內兼容
提高這一系統的效能,不是合二而一地將不同制度的城市一體化,而是各自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同時通過制度創新,不斷提高兩者之間的相容性,形成嵌入式的融合。融合(integration)不同於一體化,它強調的是相容關係,並不要求合一的體制,也不要求「融」掉哪一方。歐盟內國家之間所形成的關係就是一種融合。強調融合的目的,是讓各方通過更協調的方式發展,並基於多元共存的前提,擦出更多的創新的火花。
我強調和倡導「嵌入」二字,就是這種協調融合的方式。例如,支付寶和微信支付進入香港後,與PayMe和八達通的關係,就是嵌入式的融合。大家共存,為消費者,包括跨境消費者帶來了各種好處,而這種嵌入更推進了這方面的競爭與進步。類似地,八達通與深圳地鐵合作出一種新的電子卡,讓兩地銀行支付系統並存在一卡內,而內地的部分又可以用於20多個內地城市的公交地鐵系統。當然,類似的設計不應該限於這些消費支付系統,而應該在企業的跨境經營、政府服務(如海關、區域規劃、環境保護等)、物流和人員跨境流動管理等多方面實現。在企業的跨境經營方面,蕭耿教授倡議了幾年的「雙總部」設計就是一個可行方案。
嵌入式的融合,對香港融入大灣區發展和珠三角城市充分利用香港的優勢都有好處。而最重要的是,這種方式可以繼續保持中國與世界之間保有一條,經過香港特別行政區和深圳經濟特區這兩個特殊制度環節的通道,即我在新書中所稱的「雙向雙城門戶」,完成國家需要、但通過內地城市直接與外部交往的通道不可能完成的事項。這些事項不僅僅是經濟上的,也包括文化、學術和社會等方面的交流和相互學習。只要中美不徹底脫鈎,這個通道的重要意義對國家、對大灣區和對香港都是不容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