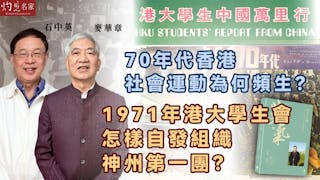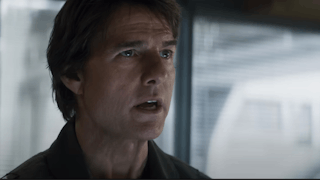封面圖片:法國名建築師波贊巴(Christian de Portzamparc)設計巴黎的「音樂城」(Cité de la Musique)(flickr)
最近在台北買了一本書,名叫《巴哈蓋房子》,讀來饒有興味。兩位作者可謂珠聯璧合:李清志是一位建築設計的教授,高晟是長笛演奏家和電台節目主持人,兩人文章的結集成了該書的附標題:「建築與音樂的對話」。
建築是我的「新歡」,音樂是我的「舊愛」,我既喜新又念舊,所以願意延續這本書的精神寫這篇雜文,不過卻只能作獨白式的「自我對話」。
該書對我最有吸引力的是前半部的幾篇重頭文章,從巴哈音樂和歌德式教堂、馬勒的第九交響曲和日本建築師北川原溫的死亡意識、美國作曲家柯普蘭(Aaron Copland)和建築大師萊特(Frank Lloyd Wright)的本土風格,一直論到「普普」(Pop)建築與貓王搖滾、爵士樂與 Art Deco 的時代關係,內容豐富,讀來振奮不已。
如果倒過來從建築來思考和音樂的關係又如何?建築設計是否受到音樂的影響?他她們是否也熱愛音樂?當蓋瑞(Frank Gehry)設計洛杉磯的狄斯尼音樂廳時,他的構思有多少來自音樂?表面看來,他特有的那種捲蓋式的弧線似乎更是「立體畫」(Cubism)的變形,但我卻想到現代「非調性」(atonal)的音樂。當法國名建築師波贊巴(Christian de Portzamparc)設計巴黎的「音樂城」(Cité de la Musique)時,是否和作曲家布烈茲(Pierre Boulez)討論過?談的是什麼?
建築與音樂中的精確與詩意
這一系列的問題又引起我的胡思亂想,甚至開始買些建築文化的書籍來讀。2008年9月我到意大利參加威尼斯的建築雙年展,路過羅馬旅遊,偶然在一家書店中見到一本小書,作者是鼎鼎大名的意大利建築師庇亞諾(Ranzo Piano,日本大阪機場就是他設計的),或許他的姓氏Piano和鋼琴或音樂上的「弱音」是偶合,但我猜他也喜歡音樂。在這本名為《建築師的責任》的書中,他提到有一次到巴爾馬城的音樂廳聽阿巴多(Claudio Abbado)指揮馬勒的第三交響曲,大為驚嘆,他說這不僅是一首純淨的詩,而且更認為和好的建築一樣,「都是為了尋回同樣的願望:一種精確性、一種數學原則或幾何圖案,同樣的精準,或同樣的不馴」。這句話表面上說的是庇亞諾聽阿巴多詮釋馬勒交響曲的印象:既精準又有詩意,並非全指馬勒第三交響曲的樂曲本身結構。然而句中最後一個字卻令我思之再三:「不馴」(意大利文 disubbidienze 原意是「不服從」),它的意涵到底是什麼?對什麼「不服從」?
庇亞諾在書中又提到了另一位意大利當代作曲家 Berio 的作品,說他的作品在結構上既嚴謹又「不馴」,最愛講求肌理動態、和色彩,在本書同頁他又說:「建築是一種先鋒藝術,它在接受挑戰中成長,也不停地挑戰它得以存在的真實。」這句話令我思索了大半天,總算半知半解地悟出一個道理:原來「精準」和「動感」、「嚴謹」和「不馴或不和」之間的矛盾可以造成緊張的關係,這種「麻煩」,就是創意,音樂如此(甚至在巴哈的對位嚴謹的音樂結構中也潛藏「不和」的音樂),建築更是如此,建築大師的作品之所以能超越普通工匠的水準,就在於其受人委託設計的建築物中另涵他物——一種不按理出牌的想像空間,它並不完全按部就班,但這種想像力或創意並非憑空而來,而是和建築師個人的經驗與人文知識的積累有關,有時候更要從其他藝術領域中找尋靈感。
甘於服務 摒棄想像
至此我不禁又想到香港大部分的公屋和豪宅,有幾幢是富有「想像力」的建築?也許風格早已不在地產商考慮之列,蓋房子只不過是經濟實效的一環。所以不少香港建築師才認為自己是「服務」階級,作地產商的奴隸。講求實效的「工具理性」說法我早已司空聽慣,其實功能並不全然決定形式,反之有創意的形式照樣可以產生新的功能和實效。香港一般住屋的設計之令我厭煩,恰是因為它缺乏想像力和人文素養,看來如出一轍,一個模型:幾十層高樓的地基必是大理石圓柱(以表現豪華?),地下必是停車場或商場,地面上設計一個小花園(有什麼用?擺飾?排場?我看不見有人在此憩息),然後是走廊、玻璃門、電梯……進得房來,空間卻小得可憐,在設計上非但沒有好好利用「逼」出來的數百平方尺空間,卻偏偏加上一些庸俗而無用的大小門檻和陽台,外加兩三個廁所;廚房呢?小得可憐。一切都是為了生意,何來創意?一種設計成功了,其他的競相仿效。
我不相信香港建築師中沒有創意人才,說不定更有像蓋瑞和庇亞諾式的將來大師,問題是:他她們都是整套經濟和市場體系下的犧牲品,最多也不過是這個龐大地產機器中的一個小環鏈,談什麼創意?
原刊於《亞洲周刊》,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