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真免費之路似乎仍路遙遙。而且,師生比沒有明顯改善、學位化不會發生、學校營運經費不會顯著增加,校舍亦難有改善。另一方面,很多雙職家長殷切需求的全日制學額,亦不會隨新措施而有大幅增加。總之,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仍只是目標,新措施只是向其邁向一小步,政府需要努力之處仍多。

承認創造性破壞和競爭在短期內可能會很難,但它們是唯一可靠的手段,可以長期提高每個人的生活質量。這將增加消費者的教育選擇,並推動政府辦學質量改進。

「不要輸在起跑線上」或者「別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是內地幾乎流行了10年的一句話。內地正經的評論,可以說是齊聲討伐,但是媒體與民間卻愈傳愈烈;苦口婆心不敵「愛兒心切」。這兩年,這句話也在香港流行起來,甚至有學術機構糊里糊塗地用來作為研討會的標題。

有部份的非牟利幼稚園能夠做到免費始終是好事,問題是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為經濟帶來何等程度的利益,尤其是免費兒童早期教育涉及大幅增加公共開支,作為問責政府,實需要向公眾解釋清楚。

忘記名校想要招什麼人,幫助孩子專注地學習、專注地發展興趣,做一個真正有趣的學生。

個半世紀以來,每當政府損害公民自由,我們總會聽到這樣的辯護:“But even Lincoln did that!” 這也是一些人這麼喜歡為林肯樹立權威的原因之一。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作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着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閑居了。第一條繼續求學之路,我們可以不討論。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

你們畢業之後,可走的路不出這幾條:絕少數的人還可以在國內或國外的研究院繼續作學術研究;少數的人可以尋着相當的職業;此外還有做官,辦黨,革命三條路;此外就是在家享福或者失業閑居了。第一條繼續求學之路,我們可以不討論。走其餘幾條路的人,都不能沒有墮落的危險。

究竟未來的中越關係演變如何,越南是走近中國,抑或遠離中國,除看美國的作為外,筆者認為主動睦鄰權,仍然在近水樓台的中國。

「希望跟以前在絕望邊緣掙扎的自己說,以前的堅持努力沒有白費,我超越了自己,所以現在腿都快抽筋了」 ——奧運會女子100米仰泳銅牌得主傅園慧

陳坤耀教授過去執掌嶺南大學十多年,把一所老牌學院成功轉型為小而精的博雅大學,在政府資助的八家大學中獨樹一幟,這次他出山拯救頻臨倒閉的明德學院,是很合適的人選;李焯芬在港大創辦佛學研究碩士學程,大受歡迎,向隅者眾。他在珠海開辦同樣的課程,邀請早年執掌港大佛學研究中心、現寶蓮寺方丈淨因法師主持,成為珠海的第三個碩士課程,估計很有號召力。

2014 教育局網頁文章《語文學習支援》將廣東話定義為「一種不是法定語言的中國方言。普通話並非大部份香港學生的母語」,但「以推行普教中為長遠目標。」 這些意見,可說是以普通話取代廣東話教中文鳴鑼開道。

令港人感到不值的是,為什麼香港科研學術成果一流而產業落後?關鍵是,港府對高校撥款機制過度傾向基礎研究,忽視應用研究。現在港府提倡科研發展,不得不因應施政而有所調整。

除了魯迅、梁啟超,還有錢基博、梁漱溟、胡適、豐子愷等一眾學者、作家、畫家,在怎樣做父親這一方面,各自呈現出了獨特氣象。

考試猶如一把尺,很大程度上能有效地量度每個人的知識水平,並且作出分野,是其「利」;惟考試不能計算一個人的獨特才能及性格優點,如正確的價值觀、待人接物的技巧、對事物的好奇心等等,此其「弊」。

歷代更替之因由,如何才能在當前打造安居樂業的社會?作為中國人應如何延續中華文化?

芬蘭人認為幼稚園的主題是玩,是生活學習,不是上學做練習,所以幼稚園沒有功課,沒有學術課程,和學校是兩種不同的概念,這和香港,小小年紀便不停的學習很不同。

我的夢想校園依然還是在做夢階段,不過做夢也是圓夢的開始,因此要說我打算辦學也沒有錯,只是還在構思階段而已。

教育的考慮很少,關心的往往只是「我如何可以收到高分學生?」也不在乎「高分」是否就是「高素質」?

大部份優秀的香港學生只會選擇有錢途的課程,例如醫學、法律、精算、財務等等,驅使本地大學的教育課程只能吸引成績只是平平的學生修讀。在此情況下,中小學教師的平均質素又怎麼會高呢!

香港中文大學深圳校區的建立反映珠三角地區近年來經濟高速發展對人才的需求大量增加,大學希望能為中國培養一批有國際視野,擔當社會責任的專業人才,為國家和地區的經濟與社會發展作出貢獻。

「這個時代的最大謬論,就是以為法律不但要是公正的,還必須是慈善的。人們以為法律不但要保障每個公民自由而不傷人地各展所能,自發上進,人們還要求法律直接促進人民的福祉、智慧和道德。這就是社會主義的糖衣誘惑。但我要強調:法律的這兩個用途是互相矛盾,水火不容的。我們必須二擇其一。」

從日常生活中取教材,然後再仔細分析背後原因,給予他們不同角度,這樣才有助他們思考和分析能力的發展。

「國民教育的根本,實源於國史教育」,由此出發,一步一腳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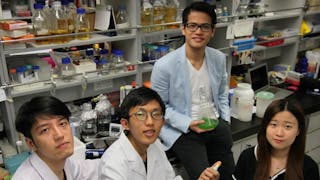
蘇樂文坦言在比賽初期,雖然已決定要開發低成本、較易吸收的 DHA,但團隊對 DHA 的認識並不深。「

華德福教育強調在「玩」中學習,隨大自然的韻律生活,在「故事」中激盪想像空間,在「藝術」中滋養細緻的美感,在「戲劇」中探索自我,孩子們「走出教室」體驗自己與世界的關係。

港人應該參照新加坡的語文發展經驗,及時作出高瞻遠矚的語文規劃,調整教學內容和安排,強調拼音輔助教學,使語文知識密切配合未來的需要。

世界依然困擾重重,環境難以持續,不公平、不公正、不安、焦躁處處,令人畏懼。你如何把恐懼轉化為促動力,成為未來的想像者,和困難的解決者──承擔各種不可能的挑戰和任務──不輸給風雨?

中國人本着文無第一,武無第二的思維,排名自然是愈高愈好,特別是香港若希望作為亞洲區教育樞紐,欲想吸引多些國際生,以致國際級教授,排名絕對是其中一個重要參照。

抓緊眼前歲月 如火鳳凰 讓牠灰飛煙滅 修成正果 那才算無悔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