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代的金銀器告訴世人,貴族時代物質生活的富庶一面,深刻展現着中國古代文化與四方交融的氣度。

今天士大夫階級勢力的崩潰已過了一世紀,蔡老師所承傳的文人琴氣質還存在嗎?

「紅學」研究當然不是肇端於馮其庸,也不以馮氏的研究而終結。事實上不同研究者研究成果的點滴積累,造就了小說有一個可通讀兼文字水平卓越的版本,這既是必須、也是難能可貴的事情。

如今戈揚已經離開了這個世界,高瑜則失去了自由,代表共和國兩代女記者的良心就此湮滅了。

紅磡曾是重工業區,今天已無遺跡可尋,只有民間廟宇繼續為居民提供心靈慰藉。每年農曆正月二十六日的觀音開庫,觀音廟(一級歷史建築)最為熱鬧,裏裏外外都擠得水洩不通。

「咸通九年」的鎏金鶴型花飾鐺,標誌着唐代鎏金工藝步向器物細緻的階段,為唐朝拼發最後的文化光芒。

若能使一般陷於現代社會心理病態的人們,在我們講的文字言語以外去體會,能夠求得一個解脫的答案,建立一種卓然不拔,矗立於風雨艱危中的人生目的和精神,這便是我所要馨香禱祝的了。

而今觀之,太平天國可說是時代產物。清末政治腐敗,外強欺侮,苛捐雜稅,民不聊生。而低下層生活更困苦,被逼挺而走險,落草為寇者大不乏人。

生肖之説,可能源自印度《文字學纂要》。

香港並不缺少創意,只在「務實」的刻板要求中失去了天馬行空的空間。

「共享空間」,「互利互惠」的理念似乎已成為文化事業的新趨勢,相信在不久將來,更多藝文共享空間會如雨後春筍般在香港十八區出現。

蔡伯勵推算特首選舉,從流年來說,屬雞的為本命年,理應較強,屬虎的平穩,屬兔的犯太歲會略為受影響。

君子問凶不問吉,蔡伯勵首先講丁酉雞流年最差的生肖是兔,以1951年及2011年是正好「天剋地沖」。

對於各行各業而言,擇日開市是每年的習俗。

他憂慮社會的分裂、民主的變質、兩岸交流的變數、中華民族的前景;他的看法實在是代表了絕大多數沉默者的心聲。

「你的歌聲很好聽」,唯獨那一刻是女性的話,其他時候主角是喪失性向的身體,猶豫在森林以外,直至遇上安珍卓尼,她變成第三者──既非自己亦非他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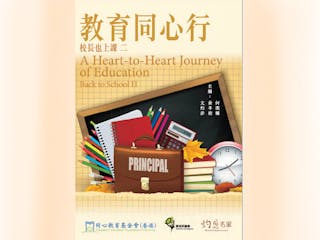
本書延續前作的教育深度思考,再次得到19位作者獻上作為給香港教育的獻禮。

-

封面圖片:小野著作《瓦版物語》(作者提供) 編按:方漢奇先生堪稱中國新聞界泰斗,先後出版《中國近代報刊史》、《中國新聞傳播史》等。本文是作者於2016年12月1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方漢奇新聞思想研討會暨從教65周年紀念會」上主題發言的講稿全文。內容精彩,本社將上中下三篇刊出。敬請關注。 上篇:方漢奇先生與中國新聞史學(全文按此) 中篇:不朽經典著作《中國近代報刊史》(全文按此) 下篇:日本學界如何看待「瓦版」新聞與研究方法論? 正是基於各國的新聞產生及其發展過程不盡相同的分析角度和認識,小野先生不僅和同年代的歐美新聞史學家一樣,贊同和認可中國新聞史學家有關邸報的研究成果,也在努力和摸索近代型報紙出現之前日本是否有其獨特的「新聞(報紙)類似物」或「新聞信」的存在。在小野先生及其弟子們的共同努力下,終於發現了日本在德川初期也曾發生過將新聞印成單張,或印成小冊子的印刷物。這就是今日日本新聞史學家津津樂道的「瓦版」新聞。由於販賣者當時是沿街邊讀邊賣的,「瓦版」新聞也被稱為「讀賣瓦版」。小野先生認為其性質與德國沿街販賣的flugblatt(德文原義是「飛紙」,即flying page)具有相似的性質和功能。 「瓦版」新聞寫入日本新聞史冊,說明了日本新聞學家並不樣樣以西說作為衡量本國新聞發展史的唯一依據和標准。恰恰相反,怎樣努力發掘本國確切有力的史料,如何從中辨析本國新聞發生史的特征及其與歐美的差異,是新聞史研究者被賦予的重大課題和使命。也惟其如此,亞洲(其他非歐美源流的國家亦然)的新聞史學家才會獲得歐美學界的尊重。 當然,對於「近代型報紙」與舊有的「新聞類似物」、「新聞信」之間是否有其連續性的問題,日本新聞史學界也曾經有人提出質疑和探討,但很快便達成共識。早在上世紀50年代前半期,小野先生的高足內川芳美先生便從近代新聞史研究方法論的角度,對兩者予以辨析。他表示,將兩者「斷緣」來研究,有助我們對兩者差異的釐清和認識,但他並不輕易否定兩者之間的連續性。(有關詳情,我將另文詳述。) 摒棄舊有方法無可厚非 同樣的,在大眾傳播學引進日本,成為顯學的上世紀60年代,日本新聞史學界也有人關注其帶來的衝擊,並提出新聞史學者是否應拋棄舊有的研究方法論的問題。 針對這樣的疑問,最早回應此話題的也是內川先生(他也是中國改革開放後首位向中國學界介紹大眾傳播學概念的外國學者)。他指出,要從大眾傳播史角度來研究的看法無可厚非,但如果欠缺對個別媒介史具體深入的研究和高質量的成果,作為研究大眾傳播全過程的大眾傳播史(儘管這並非等同於各媒介史研究的羅列和總和)原本就不可能存在。 換句話說,內川先生認為,只有當個別的媒介史研究有進展並取得高度受評價的成果,大眾傳播史才具有成立和發展的必要條件。他當時表示,他尚未看到一部令各方滿意的大眾傳播史。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謹此介紹日本學界對類似學術課題與研究方法論的對應方案,以供參考。 至於有關中國「新報」(近代型報紙)與「邸報」(或中國版的「新聞信」)或「新聞類似物」)的連續性與非連續性的問題,我在拙著《中國近代報業發展史1815-1874》(增訂新版)的自序中,曾有長篇的論述,希望能起拋磚引玉的作用,這裏不再贅述。 大家風範與史家正氣 綜上所述,可以看出中日新聞會史學家在研究「新聞發生史」時,都曾面對「新報」與「新聞類似物」如何區分的近似難題。 我長期在日本從事中國新聞史研究,儘管我那微不足道的研究成果在日本學界獲得一定程度的認可和評價,但我迄今仍然牢牢記住內川老師在博士論文答辯會上曾對我說過這樣的一句話:「你的學術成果的真正考驗不在日本,而是中國的新聞史學界。」 有一天,內川老師寄來了他到中國訪學,考察時帶回的一篇有關我的一篇研究論文被翻譯成中文並被鄭重推薦的復印件。他以欣喜的口吻在伩中寫道:「你的學術成果已獲得方漢奇先生等中國新聞史學家的肯定。」 在內川老師看來,中國新聞史的最高權威就是撰寫《中國近代報刊史》,倡建中國新聞史學會創會會長方先生及其同仁。中國新聞史如何書寫,應該是中國新聞史學家說話算數,歐美或日本的「新概念」、「新思維」固然可以,也應該引進和參考,並予以積極對話,但卻沒有必要亦步亦趨或者為迎合西學而削足適履。 我生在新加坡、求學於日本,無緣成為方老師的入門弟子,但通過對方老師著作的大量閱讀及有幸常近距離的接觸,我多少領會到方老師的大家風範與史家正氣。 古代報紙研究猶如畫鬼 記得有一回,一位年輕的老師對方老師研究的「古代報紙」困惑不解,脫口指出這是一個「偽命題」,後來覺得不妥,又擔心冒犯了大家,請我代向方先生解釋他並無惡意,只見方先生幽默地回答道:「研究古代報紙,猶如畫鬼。畫鬼容易畫人難。因為誰也未曾見過鬼,鬼可任你胡畫。」 方先生的真意當然不是認為自己研究的「古代報紙」猶如畫鬼的偽命題。不過,儘管方先生講課或聊談時談笑風生、輕松活潑,但遇到黑白是非或者應該透徹分析的問題時,他的文字是十分犀利,立場是十分堅定的。 我特別愛引用方先生對早期傳教士模仿京報的冊子式出版報刊,並在封面上引用孔子語錄的如下評語: 「這份報紙(按:指《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封面是用黃色的毛邊紙印刷的,外觀很像國內報房出版的黃色京報。……我認為,這和在它的封面上印有孔子說的『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那句話一樣,都是一種包裝。用孔子的話,是一種思想上的包裝;用黃紙做封面,則是一種發行上的包裝,目的都在迎合中國讀者的習慣。一個是思想上的習慣,一個是閱讀上的習慣。」 我也特別同意方先生1996年到大英圖書館看報,獲悉英國准備派人到中國交涉如何歸還西什庫教堂內屬於英國的藏品問題時的如下感觸: 「這使我想起了某些人的奇怪的邏輯:『你的是我的』、『我的還是我的』,我倒很想問問那位赫德先生,你們打算什麼時候把你們從中國巧取豪奪的那些東西還給我們呢……」 我認為這就是史家的正氣。沒有正氣的史家,就不可能是真正令人敬佩的史學家。 […]

太古樓是香港一條擁有逾80年歷史的教友村,建了私人屋苑後已沒留舊貌,昔日的村民亦各散東西。隨着時光消逝,今天知道太古樓的人愈來愈少。

所謂改變世界,就是要世界變得更美好。

封面圖片:《中國近代報刊史》書影(豆瓣讀書) 編按:方漢奇先生堪稱中國新聞界泰斗,先後出版《中國近代報刊史》、《中國新聞傳播史》等。本文是作者於2016年12月17日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的「方漢奇新聞思想研討會暨從教65周年紀念會」上主題發言的講稿全文。內容精彩,本社將上中下三篇刊出。敬請關注。 上篇:方漢奇先生與中國新聞史學(全文按此) 中篇:不朽經典著作《中國近代報刊史》 下篇:日本學界如何看待「瓦版」新聞與研究方法論?(全文按此) 接下來我想談談個人拜讀方先生學術著作的一些體會和感受。 談起方先生的學術著作,誰都不會忘記方先生1981年出版的上下兩冊《中國近代報刊史》(山西人民出版社)。正如中外新聞史學家所公認一般,這是一部自1927年戈公振《中國報學史》(上海商務印書館)問世以來條理最為分明、論述最為翔實、最具權威的中國新聞通史。也許是出自「擺脫意識形態」的當代潮流,近來有些年輕研究者不假思索地將方先生的這部巨著,與1966年曾虛白主編、上下兩冊的《中國新聞史》(台灣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台北)相提並論、等量齊觀,簡單地將兩者歸入為各受意識形態主宰而書寫的新聞史。我不贊同這樣簡單和草率的論斷。我個人認為,評定一部學術著作,最重要的是考核其學術的含金量及其影響力,不能望文生義,輕易地將之貼上標簽。由於這是一個大話題,今天不想深入開展。我希望新生代的有心人,能真正撥出時間與精力,對此課題認真核實與比較,並得出更為公允和有說服力的學術評價。 當然,我同意,不管是戈公振的《中國報學史》還是方先生的《中國近代報刊史》的書寫,都刻着時代的烙印和存有其時代局限性。特別是《中國近代報刊史》,出版於改革、開放後不久的1981年,既是積累了作者長期以來的潛心鑽研和總結的研究成果與心得,但受制於當時的大環境,也難免還有待補充、修飾和加強的論點和論據。針對這一點,我知道方先生是坦然同意的。在私人的交談中,我就曾多次征詢方先生是否有意出版修訂版事宜,方先生風趣地回答道:「就讓此書成為古董吧。」 將這部巨著稱為「古董」,當然是方先生的自謙之言。平心而論,時至今日,此書仍不失為治史者必讀的經典著作。這與當下一部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純為應付「教材」或評職稱而編寫的新聞通史,是截然不同的。 如何看待新聞發生史和「古代報紙」? 也許是因為我在日本求學時期師從平井隆太郎教授(日本新聞學奠基人小野秀雄教授戰後的大弟子)的緣故,我對小野和平井兩位老師關心的」新聞發生史」一直保持着濃厚的興趣。1972年我提交的日文碩士論文原題就是:《關於19世紀華字新聞紙產生之緣由(日文原文為「發生事情」)與特征的考察(1815-1856)——以〈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和〈遐邇貫珍〉為中心》;1986年提交的博士論文之原題是:《近代型中文報紙的形成過程與確立——從1815年〈察世俗每月統記傳〉創刊至1874年〈循環日報〉的誕生》。 探討「近代型中文報紙」(即「新報」)的「發生」緣由、特征乃至「形成過程與確立」,無論如何都繞不開對「新報」之前中國固有報紙的理解和界定的這一大關。在接觸以方先生為代表的中國大陸學者的論著之前,我基本上是沿着戈公振《中國報學史》的說法,將之定位為「官報獨佔時期」。但在細讀《中國近代報刊史》及改革開放後陸續出版的幾部中國新聞史著作之後,我同意方先生等的看法,「官報」並不足以涵蓋「近代型中文報紙」以前中國的所有報紙,因為宋朝已有民間出版、嚴受官方取締、查禁的「小報」。到了明清,已有官方的民間報房的存在,儘管報房皆受官方的嚴密控制和管制。從這角度看,「近代型報紙」以前的中國報紙雖然不等於一部邸報史,但從總體和本質上看,卻與」官報」並無太大的差異。針對這時期的報紙,方先生和他同年代的中國大陸新聞史學者皆統稱之為「古代報紙」,我在接觸方先生等的著作之後,也接受「古代報紙」的概念和看法,並反映在我的論文和著作中。 不過,平心而論,我在使用「古代報紙」這四個字時,多少是有些抵抗感和不安感的。問題不在於對「報紙」的定義,而是在於對「古代」這兩個字的年代界定。畢竟,邸報問世以來的唐宋明清與」古代」的概念並不太匹配。也許在未來,在更多學者對」古代報紙」(姑且稱之)有更深入研究和探討的基礎上,新聞史學界能對此提出更恰當的名詞,或對此作更合理的闡釋與修訂並達成共識。 為了進一步了解中國固有的報紙及其源流,我最近重讀了方先生的著名論文《從不列顛圖書館藏唐歸義軍」進奏院狀」看中國古代的報紙》,及方先生1978年撰寫、1980年出版的「內部用書」《中國古代的報紙》(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報刊教研室),深受啟發。前者對「世界上現存的最古老的一份報紙」——「進奏院狀」(公元887年),進行了全面的梳理和考究。後者共分四章,分別闡了一、古代的封建官報——邸報;二、宋朝以後的小報;三、明清兩代的報房及其出版的京報;四、勞動人民及封建的革命宣傳活動。全書有理有據,頗有說服力。 古代報紙和近現代報紙的區別 針對「古代報紙和近現代報紙的區別」,方先生在上述研究「進奏院狀」論文的結語中,有著如下的說明: 「是的,唐代的邸報就是這樣!它就是當時的報紙!當然,確切地說,是原始狀態的報紙。它有點近似於西方中世紀的新聞信,然而卻比西方最早的新聞信還要早上好幾百年。所不同的是,新聞信主要是為早期的西方資產階級傳達經濟情報服務的,而早期的邸報,則主要是為封建地方政權了解朝廷消息,鞏固和維護他們的統治地位服務的。 報紙作為一種新聞手段,從誕生、發展到現在,它不是一下子突然形成的,而是逐漸形成的,形成之後,還有一個逐漸完善的過程。唐代的邸報,正處於這個過程的前期,它僅僅具備報紙的雛形,還很原始,還很不完善。研究它,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了解報紙發展的歷史軌跡。 『古代報紙』和現代報紙畢竟是有區別的。我們只能實事求是地承認這種區別,不能用現代報紙的模式硬套和苛求古代的報紙。」 這裏可圈可點的論點有二: 其一是,強調唐代的邸報是「原始狀態的報紙」,近似於西方中世紀的「新聞信」,而卻比西方最早的新聞信還要早上好幾百年。 其二是指出「古代報紙」和「現代報紙」存有差異,不能用現代報紙的模式去硬套和苛求古代的報紙。 放眼世界新聞史,各國新聞史學家對這兩個論點並未存有異議。就以研究新聞發生史聞名的小野秀雄先生來說,他在其論著中介紹中國唐代的邸報及宋代的朝報時便指出: 「中國唐代首都長安系位於亞洲的都市、無論是在政治方面和文化方面的地位,都與歐洲的羅馬不相上下。新聞現像滋生於此地並非不可思議。據唐代隨筆記載,在有『中興之祖』之稱的玄宗時期就有所謂的『邸報』,報道宮廷中的動態及政府公告……時在8世紀中葉。三個世紀之後宋朝繼承唐制,也發行官報,稱為『朝報』。每五日發行一次……『朝報』是世界上最早的官報,同時也是世界上最初的定期刊物。」 由此可見,小野先生對唐代『邸報』和宋朝『朝報』在世界新聞史上所佔的地位,與中國學者的看法是近似的。他並非原封不動地將歐美的新聞發生史的概念搬過來理解和審核中國新聞史。 (待續) 講者簡介: 卓南生 新加坡旅華學者,北京大學、廈門大學、日本龍谷大學等多處任教,更任北京大學新聞學研究會導師兼副會長暨中國新聞史學會名譽顧問。

「搞新聞史離不開有關的史料。沒有必要的史料,新聞史的研究就成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是難以為繼的。」

遠在1300年前左右,正當中國唐代初期,觀世音菩薩的精神與教化,同時隨着中國佛教文化而傳播到日本、韓國,以及東南亞各地,至今已達千餘年之久,所以他又是東方文化精神的座標。

「十二相屬起於何時,諸書皆無明文。」

穆罕默多夫去年突然病逝,官方報道語焉不詳,如果權力不能順利交接,恐怕國內茍安的局面又成流水。

適應力強弱,是決定你自己適合當數碼遊牧民族的一大因素

宋代那樣一個環境,一個女人要成為一個成功的作家是非常不容易的,比起明清時候一個女性作家想出一本詩集或文集,李清照要難上好幾倍。

或者,中央警署可以改建成一個監獄博物館,取一個跟福柯著作同名的名字「規訓與懲罰」,內中陳列當年曾坐過牢的文人和志士的資料。

既然人工智可以能贏了一個棋手,為甚麼不能贏一個作家?這個挑戰或許不是一個遙遠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