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結婚生子的事本來天公地道,但罕病接二連三降臨在兒女身上,無法可施,只好全情地愛,致力至成為睏熊。

段正淳能渡己,但不能渡人。自己的快樂,別人卻哀痛,所以他的品格,亦如他的武功一樣,至死亦未及第一流境界。不過,在濁世之中,仍不失為一號人物,而成為濁世佳公子的偶像。

香港青年音樂協會「源弦樂聚薪火傳」45周年誌慶音樂會邀請了二胡名家黃安源父子共演《故鄉之歌》新曲,樂曲將為世界首演;門票今日公開發售,中樂樂迷不容錯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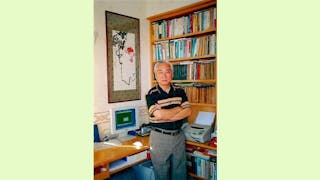
香港60、70年代是讀舊書的好時年,大陸台灣的文學禁書盡在香港,許定銘跑勻大小書店搜購,皓首窮經,終於修成正果,成為「書神」。

當年,我曾經困惑手中的洞簫,應該要吹出什麼樣的音色?洞簫音樂應該要有什麼特性?我自己應該走什麼路向?

今天的中國還不是一個智力構建很堅實的現代大國。我們固然想要培養大量能夠創新和創價的人才,但是往往「有心栽花花不發」。

張亮認為,欣賞藝術不一定穿西裝打領帶,正襟危坐;任何地方都可以是藝術表演方場地,而大館正為藝術走入民間而努力。

蘇東坡有的是那樣體貼的賢妻,能在未有需要時已為將來有需要時籌謀,「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需」,真是世情的絕配了。

所謂「四法」,是指三代權力繼承,法天法地法質法文,據法而確立帝舜、夏禹、商湯、周文的王權,他們得天授權而為聖人立為王,這便是「王法」,以「王法」為原則,繼承先祖軒轅黃帝之命而立為君。

Balli Kaur Jaswal指出,國際知名印度裔作家的作品,多從男性角度出發,忽視了女性在爭取自由時,面對的不只是東西文化和年齡代溝的障礙,還有男作家不能感同身受的隱形性別歧視。

《時務報》創刊於光緒二十一年丙申七月初一日(1896年8月9日),報採旬刊形式,逢初一日、十一日、廿一日出版,每冊20餘頁,約3萬字,用連史紙石印,頗清晰美觀,自此成為維新派的正式言論機關。

羅香林認為,研究是一個生命,由內到外,由近至遠,一一分析。香港的名稱由來,乃至石排灣、張保仔、魔鬼山、大埔等等,這些地方的故事和歷史,都由羅香林一一補白。

從小,教科書一直強調,香港開埠以前是一條不知名的小漁村,這大概是我們集體回憶裏完全相同的標準考試答案。然而,若只是小漁村,為何數百年間西方國家一再嘗試攻佔香港不同地域?

向後看的目的是為了向前看。記錄苦難是為了不讓苦難再度發生,記錄歷史是為了不讓歷史悲劇重演。這正是我出版這本書的初衷和願望。

阮大勇經常跟年輕人說:「風格不是創造出來的。刻意創造是創造不成的。」建立自己的風格,需要吸收好的東西,但切勿盲目跟隨他人的路數,否則即使模仿十足,也是別人的東西,沒用的。

我們對於人的抑鬱了解太少了。或許很多大理論都來自抑鬱的思緒:排斥、專橫、種族清洗、悲壯的舉動?

一眾作家寫西西,下筆不見沉重,是與西西作品遙遙呼應了。

「第一部小說《龍頭鳳尾》裏的主要人物是江湖人物,而新書《龍‧續》的主要人物是警察。大家可能有人知道我喜歡寫三部曲,換然之,第一部是黑,第二部是白,那第三部就是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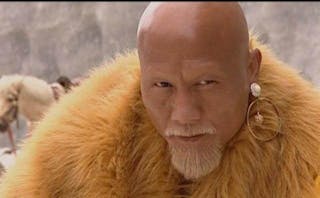
好人只有一個「好人」的模樣,壞人的壞法便千變萬化。壞人中有大奸大惡,有小奸小惡;有陰險偽善,有自尊自大,霸道張狂;有由正入邪,有由邪入正。

一般粵劇都是生離死別,很多哭哭啼啼的場面。鄭國江寫大戲時,堅持一個重要的理念:希望自己寫的劇本,令大家看得開心。看完之後,帶着愉快的心情離開劇場。

法國政府去年在70號山頭豎立紀念碑紀念加拿大陣亡將士,名單之中第一次出現華人姓氏,引起各方好奇。經過一番努力,終於確定Frederick Lee是加拿大華人Chong Lee的兒子。

以菲林拍攝時,每按一下快門,當中都包含更多的心機,使人更專注而認真地去留意細節,珍惜每一張相片,這就是蘇慶強鍾情菲林攝影的最大原因。

後起的現代大國是美國,在歐亞大陸之外。除了十九世紀末從西班牙手中接管了菲律賓之外,沒有在「東方」參與過殖民地的爭奪。

18年前李歐梵教授和李玉瑩女士結婚時,著名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寫給他倆的一首七律,有「歐風美雨幾經年,一笑拈花出梵天」之句,可謂準確預言了兩人的姻緣。

人生不易,以最深切的感受,參透人生的苦楚。

2018年10月24日至11月19日,香港中央圖書館將舉行全球水墨畫大展──教育篇,展出200幅水墨大師畫作及20幅水墨動畫供市民免費參觀。

作品與評論之間的連繫,可謂千絲萬縷,張秉權指觀眾是戲劇演出的一個必須部分,沒有觀眾,作品便是失去意義。觀眾認真去看戲,將觀後感寫出來,其實是將戲劇的生命延長了,所以劇評也是一種創作,有獨立存在的價值。

「法」的法治原則不單是一種法律觀念,而且還是社會運作的基本原則。西方Rule of Law的「法」,可以稱為「非人治自然法」。但是,不同民族的歷史淵源不同,對自然規律會有不同理解。

嚴復一生的著譯事業,實肇始於近代形式的報刊,其影響是頗深遠的。論者已予指出,他「不愧是中國近代著名的報刊活動家。」

中大哲學系榮休教授關子尹記得老師講過:「台灣一日不解嚴,一日不回去」。所以,勞思光直到1987年解嚴後,才接受台灣清華大學之邀,到台開始其新的學術生命。關子尹說,老師是一位表裏如一的大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