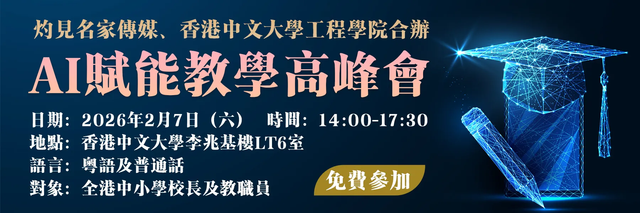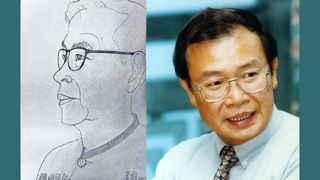問:老師對於當今中國婦女處境的洞見實在深刻,想必這與你身為女性,同時又是一名創作者有關,前者確保了真實經驗,後者提供了反思維度。你的不少詩文都涉及女兒,你對她們深沉的愛意與平等的尊重,讓我明白了女性的獨立自主,與家庭形式及母親角色並無衝突,主體性來自對責任的承擔,而承擔的方式當然可以充滿柔情。母愛中包含的寬恕力量,與詩所追求的超越性,以及人性中的美與至善一致;你為社會上各行業與各階層的女性樹立了榜樣,啟發她們如何從自己現有的位置出發,爭取身體和心靈的自由。能請你圍繞母女關係的主題,再分享一些寶貴的經驗嗎?
答:其實,母女關係沒有那麼複雜、那麼抽象,它是滲透在日常生活中的平凡點滴。不過,這些平凡點滴在一位母親心中卻是美麗的奇蹟。我的小女兒五歲的時候,對周圍的世界一知半解,好奇心又非常活躍,頻頻提問之餘,還喜歡運用想像力填補認知的空白。她口中的一些奇想,我聽來甚覺有趣,看似毫無邏輯、甚至在外人聽來,粗拙冒犯的詞句,卻道出了觸及事物本質的真意。
這就像作詩時,借助比喻或象徵來描繪無法直接訴諸言語的情感和領悟那樣。從這個角度來看,寫詩也是一個返璞歸真的過程。比如小女能夠一語道破上帝和慈禧太后,分別作為宗教集權和政治集權的象徵符號之間的共性。又比如,她在上帝和猴子之間,選了猴子做人的祖先,原因是猴子和她一樣喜歡吃香蕉。
相比之下,成年人卻容易為意識形態所綑綁,喪失最直觀的感受力。我將她這些充滿生命力的話語,保存在散文〈童言集〉裏。愛的流動是雙向的,母女關係並不意味著只有母親在一味地付出,她也能夠從女兒那裏獲得滋養。所以我很感謝小女兒,她教會了我不少重要的東西。
長女結婚的時候,我寫了一首名為〈祝福〉的詩,其中借了美國詩人斯諾德格拉斯用過的古愛爾蘭典故──「女兒是心中的刺」。要形容母女之間血脈相連的情感羈絆,沒有比它更精確的比喻了。我仍記得初為人母的那種喜悅,見到自己孕育了一個新鮮活潑的小生命,宛如重獲新生,感到世界一下子變得五彩斑斕,未來也充盈著無窮的可能性。然而,女兒誕生的時刻也是一個分離的時刻,是一種創傷。不論是對於她們,還是對於我而言,都必須接受對方已是獨立於自身的存在。我必須將女兒交還給她們自己。比如遷入西貢之前,我也事先問過女兒的意見。我希望她們按照自己的判斷選擇人生的道路,也相信她們有能力對自己的選擇負責,而我能做的,就是為她們送上由衷的祝福。因此,即使那根名為「操心」的刺常在我胸口隱隱作痛,但我感到,就連這種痛楚也是甜蜜的。
母愛是超越了一己私心的大愛。想起兒時體弱多病,母親常說:「不要生病了,讓我替了你吧。」後來,我也在女兒面前保證,「年紀老了也不會死」。天曉得這是我所作過的最無力的保證,但卻可以使一個全心全意信賴的小心靈得到安寧。母愛不知界限,希望能其所不能,也不受時空約束,代代相傳。

問:除了創作、研究和教學之外,你的翻譯工作也成績斐然,為文化傳承和人類的精神文明作出了寶貴的貢獻。能否請你談一談從事翻譯工作的心得,為後輩們提供一些經驗和指導?
答:讓我談談從事翻譯的經驗吧。翻譯本身是一門精深的學問,我在此只能簡明地談一談要點,指出一些方向,最關鍵的還是要願意花時間去研習和實踐。
從大學時期在期刊上發表翻譯文學作品開始,我就不曾放下譯筆。起初大都是英文作品漢譯,直至1994年移居加拿大後,才開始中文作品的英譯。翻譯為我打開了窗子,解除單語的束縛,設身處地感受其他語言文化的人如何看世界、如何思維,也擴闊了視野和思想領域,使我的生命豐富、性情謙和。在兩文三語通行的香港,翻譯不但有其實際的需要,從事翻譯或看譯品,還可以開拓心靈,多了解和包容他人的觀點,正是和諧社會的潤滑劑。
譯事三難:信、達、雅
我從前開翻譯理論課,第一課總是跟班上同學一起讀一回〈《天演論》譯例言〉,旨在打破迷思,不致厚誣古人。嚴復從來沒有說過信達雅是翻譯的標準。他的原話是:「譯事三難:信、達、雅」,「三難」就是很難滿足的三個要求。信達雅不是三者分立,達和雅都統攝在一個信字之下。換句話說,我們可以借助「達」和「雅」來理解「信」的涵義。
「達」是達意和傳達,即把原文旨義充分而正確地傳達給讀者,使他看得清楚明白,而非只是行文通順流暢那麼簡單。譯者須透徹了解原文涵義,才能準確表達;行文上也不必緊隨原文的形式,尤其是對於文意艱深的原文,譯者種種經營都是為了使讀者看得懂。可見「達」是為「信」服務的。
嚴復明確界定了他譯文的「雅」是指先秦文體──使用漢以前的字法和句法,而非現代所理解的風格優美或藝術性。因為他認為文體變化與時代的文明程度成正比,戰國隋唐是學術全盛時期,因此文體也發展到高峰,最適宜於表達精理微言。所以「雅」的目的是求「達」,進而服務於「信」。
譯者再創造
文學翻譯作為一種「再創造」,其實有兩個理解的角度。首先,傳達者要用語言寫出或說出心中所想,往往感到不能盡意;接收者限於自己的經歷、識見、語言經驗,對信息也不會全面了解。就算單語的傳意也不可能達到百分之一百的程度,何況跨越兩種語言和文化呢?因此,譯者如果追求完美,就不會提起譯筆,翻譯的目標不是譯文與原文對等(equivalence),而是近似(approximation)。
如果以譯詩為例,「再創造」就意味着讓一首詩在另一個文化裏重生:通過譯者對原作的了解和對譯入語的掌握,並按照譯入語讀者當時當地的接受情況加以調整,然後創造出讓他們可讀的詩篇。因此,對比原作和譯詩,挑剔或找尋原作有什麼是譯詩沒有的這種負面批評,毫不足取。要知翻譯是一種選擇,為了保存某些東西,就要放棄另一些,這是必然的;每個譯者的着眼點不同,自然有不同選擇。
同一首詩,不同的譯者便給予不同的詮釋,不同的再創造。因此,譯詩基本上是原作者和譯者合作的成品,要抹殺譯者是不可能的。
卞之琳認為,譯者應該在嚴守本分的基礎上充分發揮自己的創造自由,通過譯本的風格來傳達原文的風格。譬如莎士比亞的語言豐富而多姿多彩,極富創造性,充分表現了伊利沙伯時代英語的蓬勃生命力,可是有些母語生澀的人卻以陳腔濫調、死的語言來翻譯,誤以為這些僵化了的用語就是道地的中國話,叫人不忍卒讀、不忍卒聽。
譯詩如親歷卞之琳創作過程
卞之琳的譯本往往對風格掌握得恰到好處,對語言有敏銳、精微的感覺力,輔以對原著及其文化背景透徹的理解,對譯入語得心應手的運用,才能製造相當的藝術效果。這樣創作出來的譯著,不啻為獨立自足的藝術再創作,也是原著在另一個文學領域中的再投生。
另一個角度源於我翻譯卞詩的切身體驗,再創造指重新經歷一遍詩歌誕生的過程,譯者彷彿掉進了作者的大腦,或者說,是作者的魂靈順着詩句爬進了譯者的頭腦裏。用這種角度看待翻譯,是不是非常奇妙?那像是專門為譯者準備的一份禮物,原來每一首詩都貯存了一段時光,一段重現記憶的口述史。因此,每一首詩都像一個小小的永恆,它的盡頭一扇雕花彩漆的窗戶,推開窗,最初的陽光便照了進來。
作為卞詩的研究者,我曾以為對詩中的一字一句都了然於心,而為了把它用另一種文字表達出來,我迫使自己再度審視它的顏色、聲音、涵義、脈絡,彷彿親身體驗了一次卞之琳創作詩歌的過程,對他的認識又貼近了、加深了一層。
翻譯工作補充了我從前的研究工作,讓我認識到卞之琳多麼重視聲音效果。他在詩中反覆邀請讀者細聽各種聲音:從自然界的風聲、雨聲、潮聲、蟲聲,到人間的鐘聲和駝鈴;直到他發表的最後一首詩,詩人還在午夜遙聽街車環行。

訪談後記
登門拜訪曼儀老師,是在一個炎熱的午後。剛走進門廳,就為那古雅沉靜的氣氛暗自屏息,彷彿闖入了遺落在時間外的夢境,恐驚擾了在傢俱盆景、書冊字畫之中休憩的神靈。
見過曼儀老師,我才體會到,她的詩文是她的心靈,也是她的肉身。她娓娓述説與師友交遊的往事,目光是那麼柔和,笑容又是那麼純淨。聆聽的人也在恍惚之間,跟隨她潛入記憶的河流,一窺水底斑斕的彩石。飽覽過後,就清爽地離去,無所執亦無所憾,曼儀老師的面容上只有寧靜和幸福。
她像嬰兒一樣幸福。對於何時創作舊詩,何時創作新詩的提問,曼儀老師以直覺回答,「心裏想到什麼,就寫下什麼」;關於翻譯韻文的技巧,她只輕聲說到,「沒有想那麼多」;對於印象模糊的年份或細節,也坦誠回答「不知道」,或「記不清了」。頗具學養與聲望,而能似曼儀老師這般消融自我的人,世上實不多有。曼儀老師的性情似山,也似水;她大智若愚,也大巧若拙。
後來,曼儀老師回臥房歇息了。她的背影像一片薄薄的雪花,穿過世事萬花筒,向深林中一汪湖泊翩然飛去,不多留一字蹤跡。
〈空觀塵世影,自在玉瓶心──張曼儀教授訪談錄〉三之三
原刊於《華人文化研究》第十三卷第一期(2025年06月),經訪談者授權分三篇轉載,標題為本社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