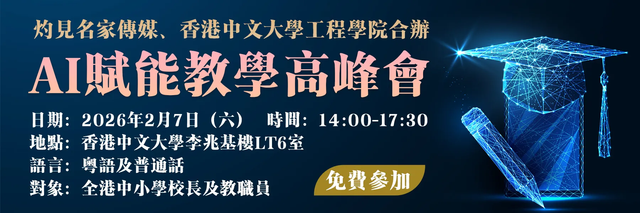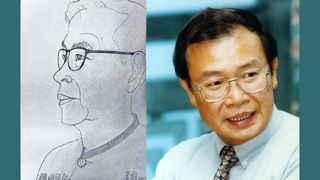編者按:張曼儀教授(1939- ),生於香港,原籍廣東番禺。1962年香港大學文學士畢業,負笈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期間,獲頒首屆胡適紀念獎學金,考取英文及比較文學碩士,其後又在英國華威大學取得翻譯學博士學位。自1967年起,在香港大學任教翻譯及現當代文學近30年,現為香港大學中文學院榮譽副教授。上世紀50年代末開始從事文學創作、研究和翻譯,著作包括《靜靜的流水》(合著)、《瀟碧軒詩》、《現代中國詩選:1917-1949》(合編)、《卞之琳著譯研究》、《揚塵集》、《揚塵二集》、《翻譯十談》;英文中譯譯著包括《塞伯短篇小說選》、《奧亨利短篇小說選》、《莫札特之死》(合譯)、《現代英美詩一百首》、《愛情詩文》(合譯)等。其英譯卞之琳《雕蟲紀歷》(The Carving of Insects,與倫戴維合譯)獲美國筆會2007年度翻譯獎。有關佛學的譯著有 The First and Second Buddhist Councils: Five versions(合譯)、英譯禪詩集A Full Load of Moonlight: Chinese Chan Buddhist Poems(合譯)、The Sutra of One Hundred Parables、Pure Land Poems of the West Studio: Contemplating the Pure Land。此外,多篇有關翻譯的學術論文在國際刊物上發表。
訪談日期:2025年6月6日下午2至4時
訪談地點:張教授住宅

問:曼儀老師你好,很感謝你願意接受本次訪談。首先,可以談一談你的家庭背景和求學經歷,以及你在此期間與師友的交往嗎?
答:我母親的老家在廣州,外公帶着家眷來港經商,開了一家金舖。她是虔誠的佛教徒,每天早上總鋪一張蓆子,跪在神壇前,誦過佛經,才吃早餐。由於慈悲為懷,深得親友和鄰里的敬愛。我兒時常隨她去佛堂,早結善緣。父親是從穗遷港的第二代,懂英文,讀、寫、說都不錯。他沒有宗教信仰,卻很包容,奉公守法,勤謹謙和,處處替人着想,常給我作弄而不以為忤。我是他們唯一的女兒,又是孻女,加以幼年多病,特別得到父母愛惜。活在父母的寵愛之中,我的童年幸福快樂,只可惜當時未知感恩,亦未思回報。
我出生才幾個月,第二次世界大戰就爆發了。這段艱難歲月,我們沒有受到很大衝擊,只是我困居家中,十分寂寞。1945年戰爭結束,二哥從寄居外婆家中回來,我就有了玩伴。我愛給他講故事,邊編邊講,永遠說不完。我開始發現語言的隨意性,有時故意不遵守約定俗成的規範,自己創造些新詞來玩。
同年9月,我入讀尊德女子小學二年級,開始讀「四書」、《古文評註》等古籍。至高小時,偶然從坊間購得《離騷》及詩詞集,雖一知半解,卻也讀得津津有味。之後,我進入聖方濟各唸初中,高中時升讀聖心書院;預科時學校不設中文科,為報考香港大學的公開試,遂往吳天任老師處研習中國文學。
我記得當時吳天任老師的住處建在天台上,我每個星期都會到他家裏聽書,和他的兩個兒子也漸漸熟悉起來,大家的關係愈來愈好。於是老師在授課之餘,也教我們寫舊體詩,我因此與舊體詩結緣。我入讀大學以後,仍與另外三位同學一起,每個星期去拜訪吳天任老師一次,聽他講詩。等老師講完詩,我們會把自己寫的詩給他看,他也會耐心地指導我們。等到大家變得更熟悉了,就一起去旅行,回想起來還是很開心。這樣美好的學詩時光持續了三年之久,一直到我赴美國留學才停止。
另一位讓我印象深刻的老師是劉百閔。我在港大讀書的時候,他對我很好。我去拜訪時,他總讓廚師做許多美味的點心來招待我。我還記得他上課的時候,總會把所講的內容清楚地寫成板書,這樣一來,即使他有口音,同學也能夠理解了。
在中學及大學時代,我寫的多是散文,另兼及小說、新詩和舊體詩。我很懷念那時與文友的交流活動,一班年輕人編《靜靜的流水》散文集時,經常在銅鑼灣的紅屋餐廳聚會,還去過道風山旅行。念預科時,我的一篇小說取得徵文比賽的冠軍,就用一半獎金買了文藝書籍,捐給灣仔小童群益會圖書館。我念初中時,經常到這間圖書館借書,便借此機會來回饋。

問:方才一進門,就留意到了餐桌旁這兩幅周策縱教授的題字,猜想其中也許藏有一段深厚的情誼,能請你分享這份禮物背後的故事嗎?
答:那是1978至1979年間,我赴美國威斯康辛大學「學術休假」時的事了。在此之前,我與幾位朋友合編了《現代中國新詩選》,於是送了兩套給周策縱先生。他說正好一套擺在案頭,另一套放在枕畔。作為回禮,他也送給我這兩幅字。
周策縱先生是非常scholarly的人,而當時同樣在威斯康辛大學的劉紹銘則比較practical。他知道一位女性獨自在陌生的地方生活之初,可能會遇到不少問題。我出發以前,就收到了劉紹銘寫來的信;當我抵達美國,他又趕來接機,並邀請我暫住在他家中,一直到我找到住處為止。而且,因為威斯康辛大學校區距離我的住處較遠,他還經常開車接送我。
問:聽聞老師在威斯康辛大學休假期間,開展了卞之琳的詩歌和翻譯研究。你與卞之琳先生數十年的相遇、相知和相交,結下了深厚的情誼。這天涯遇知音的緣分,無比珍貴,宛若清歌一曲,雋永悠揚。能不能請你分享與卞之琳先生之間的動人回憶,以及研究卞詩的經過和心得呢?
答:與卞之琳的通訊以至論交,的確是一段難得的因緣。它起於詩文,卻似一道陽光,透入我生命中那些具體而纖細的瞬間。卞之琳對我的啟發,是觸及性靈的;他的為人、治學、翻譯和創作也是一體的,需要耐心的揣摩和領悟,才能體會他沉靜之中的深邃,謙和之下的睿智。
與卞之琳以及他的詩認識的機緣,要追溯到1962至64年間,我在哥倫比亞大學念研究院的時候。當時我在學校的東亞圖書館兼職,稍有閒暇,就愛在書庫裏尋寶。我早前的興趣主要在於舊詩,但有一回找到卞之琳的《魚目集》,細讀之後,發覺新詩也有點意思。可是內地、港、臺和海外,對待卞詩頗為冷落。
到1967年,我跟一班朋友合編《現代中國詩選》時,就自告奮勇,負責卞詩的編選和評介。踏入70年代,我又在香港大學講授的現代文學課和翻譯課上選講了他的詩歌和譯作;最後,在1978年秋天,終於可以利用休假的時間,正式研究卞之琳著譯。
卞之琳向來不在作品中直接談自己,我起初只能通過別人的訪談和卞回憶師友的文章,了解一點他的生平。正因如此,能與他本人取得聯繫,在研究工作上是一個大振奮。1979年12月,我從香港直飛北京,那是與卞之琳的初次相見。他如溫煦的冬陽,耐心親切地為我解答困惑、找尋材料。而在後續的專訪,以及整個漫長的研究歷程中,我對卞之琳的正直和誠懇愈發欽佩。
他一向對自己的作品挑剔甚嚴,而我的研究卻將他早期不成熟的作品示眾,用他的話來説,是「鞭屍」;而即使如此,他也從不隱瞞對自己不利的事實,使人生敬。於是,我甘願花微薄的心力寫完了這部評論,且不問它在學術上的貢獻,於我自身,也算是了卻了一個心願。

至於心得,就很難用三言兩語講清楚了。得之於心,存之於情,而卞之琳說,「至情無文」,「至文無文」。談起卞之琳的詩,最受推崇的,往往是作者能用象徵主義技法巧妙地帶出哲理。開始接觸卞詩的時候,最能引起我的興味的,也是詩中的玄思。而卞之琳總說:他沒有想得那麼遠、那麼玄,他不過在抒情(廣義的)罷了。
現在我漸漸體會到他話中的真切性。感情強烈到一定程度,就有可能突破思維原本的局限,在剎那間與物象結合,構成獨特的喻體或象徵;一個嶄新的世界也會在這些物象中展開,引起思想情感無限的激盪。而這種「無限」所包孕的可能性即是玄思所在。因此,我愈來愈重視卞詩的「情」多於「理」。
我不知道《卞之琳著譯研究》在學術上能不能有一點點貢獻,但過程遠遠重於成果,對我個人而言,研究卞著帶給我最大的滋養,不在文字,而在於文字背後啟發生命的精神。
問:你分享的心得太精彩了,原來感性有時能比理性走得更深、更遠,因為前者是象徵的生命之源,是那個動力因,而後者是結出的果。你是真正將卞詩的內核化於心了。由此我聯想到在卞之琳先生的《山山水水》中,林未勻乘輪船過三峽時,彷彿經歷了一次重生,獲得了內外相融、身心合一的領悟,能否請你談談對這個片段的理解,它是否可以解釋「至情無文」和「至文無文」呢?
答:那我就從這本被作者親手燒毀的《山山水水》談起吧。這本書是卞之琳唯一的長篇小說,寫1938年到1941年皖南事變期間,知識分子對抗日戰爭的反應和由於戰爭引起的變化。卞之琳在自序裏提到,小說的整體結構和情節呈現螺旋式的發展,亦即事物看似繞了一圈回到原點,其實已經在另一個平面上了。從僅存的殘篇上來看,象徵的運用體現了這本書的「詩」質。而象徵的目的是揭示真理,在書中具體呈現為:知識分子梅綸年參加開荒勞動,領悟到集體行動能克服個人的私心,言生於行又沒於行,正如浪花起於海又溶於海,這就是「至文無文」的意思。卞之琳借綸年充滿想像力和洞察力的眼睛,帶我們領略了無文之境──海所象徵的本體。
說回你感興趣的林未勻在渡三峽時,所感受到的宛若新生的喜悅。與前面提及的綸年透過象徵抵達真理相比,這個片段呈現了另一種用「詩」傳達「哲學」的方法──抒情。未勻見到巨幅水花與船相撞,頓覺峽中充滿喜悅。她想起了紀德在《新的糧食》中,將喜悅當成德行來讚頌,而這喜悅對應著詩文所寫的三峽的悲苦,古代行路的艱難襯托出今日交通之便,可見她的喜悅背後有歷史的維度,古與今因為她的喜悅成為了共時的存在。
正因如此,未勻才能一直向前,紀德所謂「完全擺脫過去的牽絆」,並非指遺忘過去,而是領悟到過去和未來都包含在此刻之中,當下即蘊藏了無窮的可能性,因而對面前展開的未來充滿了信心。由此可見,如果能全身心投入過程之中,像赤裸的孩子一樣,全然將自己托付於旅途,那麼一切界限都會隨天際移動,每一個瞬間都會是新生。林未勻在「喜悅」的情感中跳出自身,跟自然、與人類的歷史和文明共振,這樣的情感體驗已經超越了理性的範疇,所以卞之琳才說,「至情無文」。
不論是「至文無文」,還是「至情無文」,這個「無」都包含了「無我」的意思。卞之琳創作《山山水水》這部小說,也許正是為了正視歷史、正視現實,向自身之外的他人投以普世的關懷。
〈空觀塵世影,自在玉瓶心──張曼儀教授訪談錄〉三之一
原刊於《華人文化研究》第十三卷第一期(2025年06月),經訪談者授權分三篇轉載。
延伸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