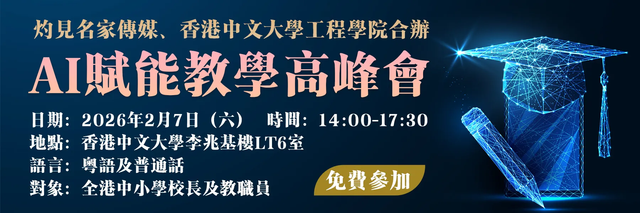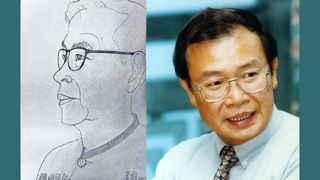問:這與你所強調「過程」的意義也一致吧?對結果的過分關注,會切斷人與周圍事物之間的感應和聯繫,將她作為個體隔開,令她無法從他人與世間萬物那裏,收獲本就包含於生命的餽贈和啟迪。縱觀老師的寫作之路,從創作之初便情有獨鍾的舊體詩和記錄少女心事的新詩,到用詩文抒發對流年的追憶、對世人世事的哲思,再到一顆明淨淡泊的禪心,題材頗豐,卻又是清風柔骨一以貫之。《文心雕龍.知音》有言:「照辭如鏡矣。」你的作品溫純如水、潤澤萬物、生生不息,亦是你本性的映照吧。小思老師認為,你與卞之琳先生「人生理念似有前源契合」,這是否意味着卞詩的內核本就蘊藏在你的本性之中?不論是在治學、創作、翻譯以及為人,你無不重過程而輕結果,也可以稱作是對「至情無文」和「至文無文」的「躬行」?
答:我在前面的回答中提到過,與卞之琳的論交跟我的成長分不開,至於「本性」的問題,其實很難有一個定論。我可以用終身從事翻譯,以及後來稍涉佛學所得的領悟來解釋。一方面來說,人的認知能力是有限的,不論對人還是對己,全然的理解是不存在的。譯者如果追求完美,要求譯文與原文百分百相似,首先就不會提起譯筆。這也與佛學暗合。佛家說人生是苦,那也沒有不對,可是巴利文dukka一詞蘊含更深層的哲學意義:缺憾、無常、空、不實有。人生的苦就是源於這個深層的意義。有了這種認識,就不再強求完整和圓滿,反而可能因破除執念,而看到自我、他人和世界的多種樣貌,理解到「苦」其實也是不實有的。
另一方面,只要人尚且存活於世上,本性也就無法凝定下來,而是會隨着環境和際遇不斷變化。從翻譯的理論和實踐,我確信過程遠比成品重要。人生亦何嘗不如是?在生命的旅途中,不斷探索新事物,產生新思考,從而發現自己的新面向,是很有趣的,比如我其實也有不太「溫柔」的一面。社會上的許多制度並不完善,不但無法確保民眾的基本權益,甚至還可能危及他們身心的勢力。同樣,在商業化浪潮中,貪婪和狡獪等負面價值,有時會被披上文化的包裝傳播。身為一個學者,一個有能力看清市場和社會運作邏輯的人,應擔負起相應的責任,將社會各方面的隱疾揭發出來。而在這種時候,嚴厲就是必要的。
總之,好好活着就是了,不必追問終極為何,那已超出了人類的智慧範疇。人生在世,一天客塵未去,還會有喜怒哀樂,還會發之於文字。而等到客塵滌盡,本性自當回歸清淨。清淨之所,文字也不復存在,「至文無文」就是這個意思。

問:「至文無文」需要借助象徵來解釋,「至情無文」卻可以從人生的無數瞬間中尋獲,透過感受來直接經驗。雖然此情發生的時刻,人因完全融入當下而忘卻了言語,但對這份情感體驗的記憶卻留在我們的身體裏,它的短暫、獨特和美麗,會激起我們用文字去銘刻的衝動。聽聞老師在加國與佛學結緣,隨後着手翻譯原始佛教的佛典以及中國古典文學中的禪詩,後來又創作了不少禪詩。不知你在創作禪詩時,是否也懷着與「至情無文」相似的心境呢?
答:所謂心境,映照的其實也是外面的風景,或者說內外原本就是一體的。禪詩也是如此,看似出自內在的了悟,實則與環境,或者說人生境遇緊密相連,外顯於內,內發於外。
這裏就要提到匡湖居了,那佇立於西貢水之湄的南國佳麗,它帶給我許多靜悟的剎那、難忘的時刻,當這些瞬間在心中激起波浪,一首詩就誕生了。一日清晨雨過,我到園中餵魚,朵朵睡蓮向陽光揚起紫色的圓臉,一撒下魚糧,錦鯉即從四面八方齊來噬食,顯得滿足歡快。
我回到斗室習禪坐,心凝形釋,似活在時間之外,永恆之中。在禪悅中,一首詩浮現腦際,我坐起將它記錄下來。我寫下的,是許多人眼中再平凡不過的時刻,它日復一日地,貫穿於我的生命之中。但於我而言,那個時刻飽滿且神奇,彷彿已經包含了生命的全部所求;魚的快樂和我的快樂交融在一起,又是那麼和諧、美麗。在禪坐的靜定中,心澄明如鏡,映出了世間萬事萬物的流動,而我一動不動,等待它們從肉身穿過。我所做的,不過是把心中的景象化為紙上的墨跡,文字雖無法把當時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的喜悅重現,卻能將記憶作為種子埋下,至於未來能否開花結果,就聽憑造化了。
藉着去朋友家團拜的偶然機緣,我們一家才有幸遷入匡湖居,一住就是七年,後來移居加拿大期間,我仍懷念着在匡湖居住的日子,於是回國後又在此地住了三年,直至外子中風才搬回市區。曾經在這詩情畫意的環境中生活過,已經感到很幸福。所謂緣聚緣散正是如此:珍惜美好的往日,更安心活在當下。放下對人、事、物的執著,是佛學和禪修中的重要課題,換句話說,是學習怎樣懷著感恩的心情吿別。
近十幾年來,身邊的師友相繼辭世,自己的健康也每況愈下,很難不去思考關於死亡的問題,這自然也體現在詩作裏。我寫過一首名為〈蘭花〉的詩,曾發表在《禪修之友》上。這首詩很簡單,只記錄了蘭花的盛開和凋零;而在我眼中,盛開和凋謝的過程都是圓滿的。
除了匡湖居以外,志蓮淨苑也是我修習佛學、領悟禪意的重要場所。我剛從加拿大回到香港時,曾在志蓮淨苑進修佛學課程。另外,我還在那裏結識了阿那律陀長老。他來自斯里蘭卡,請我幫忙口譯中國的佛經,並由志蓮淨苑的蕭式球老師記錄下來。當時,我一周會去三次,從早上10點口譯到下午1點,然後就隨蕭老師在志蓮淨苑吃素菜午飯,很是美味。
我還想起一件趣事,當時阿那律陀長老很得到大家的尊重,信眾見到他都會五體投地,而我則懵懵懂懂,跟他一直都是「平起平坐」。後來我隨志蓮淨苑的朋友去斯里蘭卡拜訪過他,他知道我不吃辣,還叫我不要在外面吃飯,吩咐廚師做些不辣的菜在他那裏進食。如今他已經圓寂了。

問:老師的禪詩看似清淡短小,描寫的又是生活中的尋常物事,沈靜如山澗幽蘭,毫無張揚之意,實則寄寓了深遠的哲思,直抵生死之間的河界;你能從一滴水中看見汪洋,從一片葉裏悟到菩提。你寫〈玫瑰海棠〉,照見從明豔到淡褪的容顏,以及與眾生共存的生機;終將回歸土地,便化作繼續哺育有情世界的春泥。正如生中包含着死,死也延展了生。寫〈聽聽身體怎麼說〉,是對看似正確的養生論的質疑,進而提出了一個「驚世駭俗」的觀點──死是否也和生一樣,是人類身體本能的訴求?在科技醫療高度發展以及慾望過度膨脹的當代,對生的眷戀是否演變為了一種執念?
你聽到身體疲憊的低語,它渴望一場深長的休憩,渴望掙脫軀殼,化為地、水、火、風。而到了寫〈定〉這首詩的時候,心已不隨外物之變而波動,這是生者能達到的、最接近死亡的境界,因為自我已徹底消融了。去除「我執」後,人才能達到「中空」的狀態,一如詩中那隻靜止在時空中的渾圓的瓶子。人在年輕的時候覺得世界像一個萬花筒,自願或不自願地捲入其中。其實那些不過是幻象,用以抵抗對「空」和「定」的恐懼罷了。而分離、放手,甚至死亡和解脫的關鍵,就是接受人生無常的空性,就像詩中的那隻瓶子,它的內裏一無所有,卻仍是圓滿的。除了詩歌以外,老師也創作了不少散文和小說,其中包含了你對女性處境的關注和反思,可否請你就此談一談?
答:我的小說《四姐》,描寫了一位一生受困於傳統制度而不自覺的女性。首先,我們不能說四姐沒有自己的想法和感情,只是這些想法和感情,無不來自傳統教條的規範,而她也不加思考地領受了。換句話說,她的自我意識沒有覺醒,一輩子就已經過完了。沒有自我,對他者也就無所求,無所求也無所得,對世界自然也不會有太多的留戀。四姐所象徵一類「無私奉獻」的女性,也就是刻板印象中的妻子和母親,一生都在寂寞的長夜中行走,她們無法替自己作選擇、作決定,也就無法迎來真正的光明。
而在那些制度已經消亡的當今社會,婦女是否得到了解放?我去理髮店洗頭的時候,會翻翻堆在面前的雜誌。那些刊物上的小說,大多是千篇一律的愛情故事,女主角外在亮麗,內在性格卻很模糊。有一回我翻到幾篇小說,題材都是關於濶人的情婦。令我吃驚的是,女性筆下透出這樣的論調:與其獨自捱盡在社會上謀生的艱辛,不如為濶人所蓄養,樂得衣食無憂。這豈非將幾十年來婦女掙扎贏取的一點自主精神一筆勾銷了,回復以往仰仗男人鼻息的日子?
可見五四運動以來,婦女並未徹底解放,根本原因在於制度。婦女看似得到了接受教育和就業的權利,實則是挑起雙重的擔子,白天朝九晚五,夜晚依舊要照顧家中老少和柴米油鹽。正是這種現實處境,讓情婦主義改頭換面,復出江湖。一方面是不平衡的社會制度,另一方面是保守主義用鮮衣美食設下的圈套,再加以市場對女性裝扮和儀態的推崇,也難怪婦女的主體性步步失守,在身體、乃至在精神上淪為附庸。
這種現況是一種社會結構性問題,但婦女自己也要爭氣,在主流價值體系改變以前,我們首先要將自己視為一個有思想、有感情、有各方面發展需求的完整的人。一些電視節目刻意將家庭主婦的形象塑造得幼稚且愚蠢,企圖愚惑公眾的認知,催生出種種偏見。更危險的是,這些偏見可能反過來影響婦女的自我認知。所以不論外在環境如何,女性首先要尊重自己,才能防止進一步的欺凌,得到別人的尊重。
〈空觀塵世影,自在玉瓶心──張曼儀教授訪談錄〉三之二
原刊於《華人文化研究》第十三卷第一期(2025年06月),經訪談者授權分三篇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