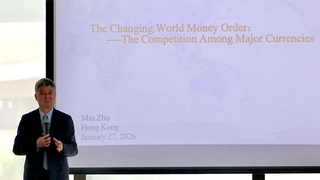幾千家藥廠藥商互相競爭,不但沒給患者帶來物美價廉的實惠,反而弄出一個藥價持續虛高的局面。進入醫藥世界,人們看到手法多樣、數額巨大的「回扣」行為幾乎已經成為該行的行規。如此的「市場化」令人失望,反其道行之的取向重新抬頭,似乎是題中應有之義。
其實,除了經濟學的黑板,天下本沒有純粹的「市場」。作為完成交易的一種制度或機制,真實世界的市場從來依賴於資源利用的權利界定。簡單地說,權利界定是什麼樣的,市場就是什麼樣的。由此,本系列評論才集中研究我國醫療服務和藥品產供銷領域裏,種種權利的實際界定狀況。

改變權利現狀需注意費用約束
很明顯,沒有高度集權、又不受有效監督的國家藥監局的藥品審批權,我國藥廠競相付給藥監管制當局巨額「批件回扣」的行為,就是無法理解的。同樣,沒有醫院醫生的處方權,藥商付給巨額「處方回扣」的行為,也就無法得到解釋。這說明,人們對某種市場狀況的不滿意,總可以到實際的權利界定狀況中去找到問題的成因。
不過,要進一步改變那令人不滿意的市場現狀即權利現狀,我們還要注意更為複雜的費用約束。
舉一個例子,國家藥監局的集中審批權當然是所有「批件回扣」行為的根源。但是要解決問題,卻面臨多種多樣的選擇。是用集中的監督權對付集中的藥監權?還是由多個中央行政部門「分享」藥監權?或者更多依賴於地方分權的、而不是中央集權的藥監體系?或者無論中央審批還是地方審批,一概大幅度縮小藥品審批的範圍?還是橫下一條心,乾脆把藥品作為普通商品看待,除了以普通商法和刑法節制,完全取消藥監權的設置?
諸如此類,涉及的不單單是「怎樣做更理想、更合乎潮流和理想模式」,而且是在種種現實條件的實際制約下,怎樣選一個體制運行成本較低的醫改方案。其實,醫療問題和其他民生問題一樣,非從顧準先生當年反省過的理想主義天上落回到經驗主義的地上,才有可能探索實際可行的改善之道。

醫療服務供不應求 予醫生壟斷權
醫院醫生的權利狀況何嘗又不是如此?我的分析,不過把在「醫」方手中的大權作一分為二的處理。一方面,由於知識方面的分工,醫院和醫生擁有醫學專業知識和判斷的壟斷權;另一方面,由於合法行醫的準入門檻過高,醫療服務的供不應求又授予醫院醫生一種供方的壟斷權。兩種壟斷權的叠加,決定了當下我國的醫院和醫生、尤其是好醫院和好醫生,在整個醫療服務和藥品供應方面的「權高位重」,具有極高的相對稀缺性。
但是現行醫療服務的價格管制體制,偏偏又不承認醫院和醫生極高的相對價格。當然可以不承認,但實際上擁有壟斷地位的醫院和醫生很容易就「矯正」相對價格的出錯。
講過了,反正對疾病的診斷、治療方案、以及藥品和設備的利用,橫豎離不開醫學專業知識和專業判斷。價管體系不承認醫生專業知識和判斷能力之價,醫院和醫生就一定有辦法尋找其他途徑來實現其相對價值。所謂「藥價虛高」、過度醫療、醫療服務差等等現象,從根本上看,不過都是相對價格嚴重歪曲之後的派生物。
相對價格反映資源的稀缺程度
不少人否認「相對價格」對資源動員的決定性影響。他們以為,還不是「市場經濟那一套」?!只要宣布醫療服務和醫藥是特殊行業,不容許搞市場化,什麼相對價格不相對價格的,不就再也不管用了嗎?反正只要搞政府主導的醫療衛生體制,發命令、講道德、守紀律、抓正反典型,外加增加財政撥款,即便相對價格不對頭,也是無關宏旨的。
這種認識大錯特錯。我的看法,相對價格要大體反映資源的相對稀缺程度,是在一切經濟體制中都發生作用的經濟機制。違背了,人們的行為就一定歪曲,資源的配置也一定要出問題。這套邏輯,不是叫市場經濟管用,不叫市場經濟、叫計劃經濟或政府主導經濟,就不管用的。
以政府本身的資源動員為例。遠的不提,單說近年我國公務員先後數次大幅度加薪,到底是為了什麼?還不就是連政府也不能擺脫相對價格機制的作用嗎!要是公務員的相對報酬(全部收入都算在內)嚴重偏低,根本就無從保證公務員職位對人材的吸引力。這並不意味講政治、講理想、講責任,沒有用,都有用。但是,只要相對價格不對頭,政府就沒有充分動員人力資源補充公務員隊伍的經濟基礎。
有趣的是,過去多少年公務員的薪水可以基本不動,但市場大潮一來,特別是九十年代以後,再不給公務員加薪就頂不住了。道理何在?比之於其他受市場力量左右的人工價格,公務員的薪資水平相形見絀就是了。
記得1998年的時候,當面聽到中直機關一位老友的感嘆,「現在我們連打字員也騙不來囉!」──相對價格是相對的,其他由市場決定的人工發生了變化,終究要影響到政府公務員方面去。至於後來公務員的收入是否調得偏高,區區在下已經為文闖了禍(見「公務員的收入偏高了」),此處不重複。
千萬不要認為,市場裡的相對價格真是由「看不見的手」制定的。錯了。所有價格都是看得見之手所為。街市上的小販,每個人的腦子裡都設有一個「物價局」;市場裡的公司,定價活動分明是有組織、有意識的行為。只不過小販和公司都沒有強制力,不能定下一個價格強迫他人接受,非要在無數買家、賣家的討價還價過程中不斷修訂自己的出價而已。支配這一切活動的力量,雜亂無章之中似乎又有跡可尋,是「看不見的手」的由來。

政府處理相對價格恐愈發困難
反過來,也不要認為擁有強制力的政府就可以胡亂定價。我不會忘記,號稱「計劃經濟」的時代,糧棉概由國家統購,政府一口價從不容農民和市民還價。可是那個年代的糧、棉比價定得稍有不妥,計劃盤子就全部亂套。原來,無權「還價」的農民是可以「還量」的。無非糧價相對棉價偏高一點,多種糧食的積極性就增,種棉花的就減。
所以我的印象裏,真正有經驗的計劃官員,對相對價格無不心存敬畏、如履薄冰地謹慎加以處理。政府處理相對價格的本事一般不如自發的市場,原因是再賢明的計劃官員也難以及時處理千千萬萬商品、服務和要素的供求訊息。
回頭說醫療。我的看法,叫什麼制也要面對相對價格的問題。不是有建議說乾脆把醫護人員悉數納入公務員範疇,由政府庫房開支全部養起來,然後「收支兩條線」地開展醫療服務嗎?試試看吧。不過沒有理由把新體制的甜頭想得那樣大,因為目前尚由各家醫院院長分散對付的相對價格難題,到時候可要集中由政府主導了。
打聽了一下,北京市先行試驗的社區醫院的醫生年薪,定為41000元。行內人評價說不低,但不知道政府庫房可以支持多大的面。我認為更大的問題,是以後調整的及時性如何?大體2004年以來,市場裡人力資源之價變動頻頻,政府集中處理相對價格,僅此一項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困難就是了。
原刊於人文經濟學會微信平台,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