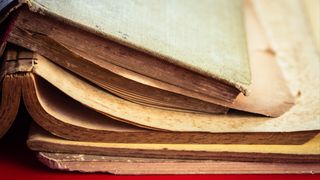文(mɐn11-55)
粵語有同一字同一義,讀書音讀陽平(第四聲)而語音讀陰平(第一聲)的特殊現象。如「乞兒」中的「兒」(語音讀ji55)、「狼戾」中的「狼」(語音讀lɔŋ55),還有義為「一元」的「一文」中的「文」(讀書音「mɐn11」語音「mɐn55」,頗多人索性將此字寫作「蚊」)。
文、緡 誰是本字?
說到這個「文」字,有同道認為當以「緡」為本字,亦有兩個寫法都接受的,如內地學者麥耘、譚步雲編的《實用廣州話分類詞典》一書,就在其「貨幣單位」項下有這樣兩個條目︰「緡(文) mɐn-1<音蚊,饃因切>」、「緡(文)雞mɐn-1 kɐi1<緡(文)音蚊,饃因切>」。雖則此書的「凡例」明言「詞頭用字取社會上慣常使用的寫法,不一定追求本字、正字,但必要時用括號注出另一種寫法或本字」;但是當編者以「緡」為字頭,然後用括號注出「文」於其後,我們自然可以相信編者比較接受「緡」這個寫法。
如果說「緡」在社會上是較慣常的寫法,那就完全遠離事實,因為大概大部分人都不太認識這個字(就以與金錢有關的義項來說,此字粵音可以有兩讀︰「mɐn11」[音同「民」]與「fɐn55」[音同「分」])!其實以「緡」為「mɐn55」的本字之說甚誤。詹憲慈《廣州語本字》卷二十九的「一文雞度」條,已指出「銀錢一文者,銀錢一枚也」,可見義為金錢面額的「元」的「mɐn55」,詹氏已認為當以「文」為本字。至於「緡」,雖也與金錢有關,卻與「文」有異,不能與「文」混為一談。現在辨其相異處如下。
「文」是日常用度
先說「文」。《漢語大字典》「文」(wen2)條︰「量詞1.用於計算銅幣的基本單位。南北朝以來,銅錢圓形,中有方孔,一面鑄有文字,故稱錢一枚為一文。如一文錢;分文不取。《宋書‧徐羨之傳》︰『可以錢二十八文埋宅四角。』《水經注‧漸江水》︰『漢世劉寵作郡,有政績,將解任去治,(此溪)父老人持百錢出送,寵各受一文。』唐 褚遂良《諫魏王泰物料踰東宮疏》︰『東宮料物,歲得四萬段,付市貨賣,凡值一萬一千貫文。』」筆者又於北魏 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一書中見「文」字作「錢一枚」用。該書卷五《種槐柳楸梓梧柞》第五十云︰「種柳……一畝二千六百六十根,三十畝六萬四千八百根。根直八錢,合收錢五十一萬八千四百文。」
現在再說「緡」。《漢語大字典》「緡」(min2)條︰「穿錢的繩子。《廣韻》‧真韻︰『緡,錢貫。』《史記‧酷吏列傳》︰『出告緡令,鋤豪強并兼之家』張守節《正義》︰『緡,錢貫也。』《漢書‧武帝紀》︰『初算緡錢。』舊注引李斐曰︰『緡,絲也,以貫錢也。』」又《王力古漢語字典》「緡」條︰「穿錢的繩;成串的銅錢,一千錢為一緡。《漢書 武帝紀》︰『初算緡錢。』」
綜上所述,可見「文」是日常用度,指一個錢幣;而「緡」則是本義為「錢貫」,而引伸義為「一千文」的大額金錢。「一緡」是為數甚多的「文」,而「一文」(一枚硬幣)本身不可能叫作「緡」。
《水滸傳》證據
我們再看一看下面兩段《水滸傳》的文字,就可以知道粵語的「mɐn55」確來自「文」。
《水滸傳》(七十回本)第六十一回︰「薛霸罵道︰『你便閉了鳥嘴!老爺自晦氣,撞着你這窮神!沙門島往回六千里有餘,費多少盤纏!你又沒一文,教我們如何擺布!』」又同回︰「(燕青)行了半夜,肚裏又饑,身邊又沒一文;……。」上引文字中的「沒一文」和「身邊又沒一文」,跟粵語「周身無(冇)mɐn55」(身上沒有一個錢)一語並無二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