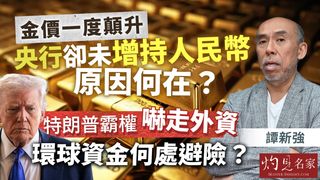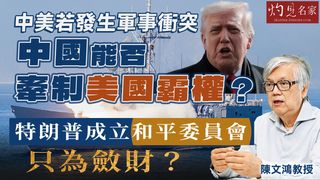的士業界最近要求政府使用公帑收回的士牌,原因是歸咎政府未有嚴厲打擊網約車平台,令業界蒙受巨額損失。香港中文大學亞太研究所高級研究員羅祥國反駁此一說法,認為政府現沒需要設立賠償機制,也看不出的士業界因政府政策失誤而蒙受虧損。
過去十年,的士牌價由700多萬元高位至近期跌穿200萬元關口,累跌幅度超過七成,引起業界擔憂。部分車行代表及團體建議政府以每個牌400萬元均價回購,冀能保障車主權益。按現有1.8萬個的士牌,涉資達720億元,但這項建議遭到立法會議員及公眾非議。
李家超指的士已享有不少 特權
行政長官李家超於周二(10日)回應傳媒提問時表示,使用公帑時必須「極度謹慎」,市民對的士服務未達要求,有很多聲音、意見,業界必須重視公眾看法。他強調現時的士已享有不少「特權」,包括設有專用的士站、可以隨街接載客人和指定禁區下車。
羅祥國表示,為的士牌設退場賠償,前提是政策出現改變,令的士營運商蒙受所謂損失,但他暫時看不到有這樣的政策失誤。他舉例政府因興建道路或其他公共設施,而要收回私人土地時會作出賠償,理由是業主無法再耕種、居住和使用該片土地,對業主造成經濟損失。
由於的士牌仍有市價,他說政府收回的價格就必然高於市價,否則的士商可以市價直接在市場出售,但他分析的士業者聲稱的「損失」並非政策失誤造成,他相信政府不會因此作出賠償。
羅祥國指出,政府在的士市場框架下引入網約車衍生了三個問題,第一是的士、出租車和網約車服務能否滿足市場,第二是的士服務水平是否受公眾詬病,第三亦是最重要的是如何處理Uber服務的問題。

call Uber早成港人生活習慣
他解釋,Uber早於2014、15年已經落戶香港,迄今call Uber已成為港人生活習慣的一部分,更是年輕人常用的出行工具,「但它在香港法例下是一個非法經營的模式」。作為網約平台,它邀請私家車參與經營,卻沒有的士收費經營的牌照,提供服務的司機也沒有職業駕駛測試。
Uber進入中國、新加坡等市場的時間與香港相若,但這些地區很早就明確不容許沒有牌照的網約車營運,所以Uber早已退場或與當地網約車企合併,但香港政府遲遲沒有建立好網約車的監管體系,時間長了更難加強管制,對此羅祥國認為「有點可惜」。
去年5月批出新的網約車隊牌照,料最快今年9月推出服務,中標的5家公司是以現有2000個的士牌照營運,並沒有私家車參與,2000的士約佔現有的士總數兩成多,而政府訂定的網約車目標暫為3500部。羅祥國指,「如果按照新加坡將的士與網約車數目比例訂在六與四,香港潛在網約車的數目仍有增加的空間。」
究竟2000個新的網約車能否滿足市場需要?政府持有大數據,可能對情況更清楚,而羅祥國估計需要觀察兩年才能判斷,若然不夠,屆時可以批出更多的士或網約車牌照。

香港網約車模式非常接近新加坡
他指出,去年香港批出網約車隊牌照的政策實際已非常接近新加坡。新加坡不僅規定網約車公司需要營運牌照,旗下司機也需要考取職業司機牌,提供服務的網約車本身也需要牌照,「即是公司、人和車都要攞牌。此外,網約車與當地的士一樣有期限,所以期滿後需要公開競投。」
問題來了,未來網約車在港營運需要取牌,而Uber的經營模式卻不用取牌,這顯然有格格不入之處。
近日訪港的Uber全球公共政策主管Andrew Byrne接受《明報》訪問時表示,同意規管應以網約車與的士公平競爭為原則,網約車平台、司機及車均須取得營運牌照,規管要求可與的士看齊,唯期望當局勿限制各類牌照數量,交市場自由調節。
Uber接受與的士、網約車同等監管
對於Uber作妥協的建議,據報運輸及物流局回覆傳媒提問時沒有正面回應,但稱該局正全速推進訂定規管網約車平台的立法建議,目標是在今年內敲定有關平台、車輛和司機,三方面的牌證要求等細節,政府會不時跟不同持份者會面,收集意見及建議。
羅祥國提到,新加坡的士牌的有效期為10年,期滿後政府可以拿出來再競投,如果的士的牌有年期限制,而牌照會隨有效期逐步臨近屆滿而跌價,某程度可杜絕牌照的炒賣活動。
另外,根據倫敦、新加坡及中國現時網約車政策,網約車不能像的士可以在街上兜客,只能通過網上預約,但網約車最大好處是可以提供多元服務,車種大小亦有不同選擇,例如5座位、7人車,以及其他配套服務,收費亦較的士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