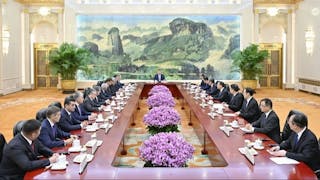今天的國際政治舞台上,在作為西方世界核心的美國,人們最為關切和討論最多的,無疑是所謂的「自由世界秩序」所面臨的嚴峻挑戰及其前途問題。二戰之後,美英兩國緊密合作,確立了人們所見的「自由世界秩序」(liberal world order)。這個秩序形成的背景,便是歐洲國家之間進行的一戰和二戰。這個秩序的首要目標,是要確保以後不再出現導致一戰、二戰那樣的國際條件。
美英主導下的這個「自由國際秩序」是具有特殊含義的。這裡所指的「自由秩序」,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國家內部「自由秩序」向國際社會的延伸。這個秩序所強調的各參與國內部要保護公民的人權,即內部秩序;在國際層面,這個秩序強調的是1648年歐洲版的威斯特伐利亞(Westphalia)秩序,即這個秩序是建立在法治和對各國主權與領土完整的遵從之上的。同時,這個秩序也是開放的,即這些總體原則適用於全世界,各國可以基於自願原則參與這個體系。
在實踐層面,也在美英主導下建立了各種國際機構以增進和平(如聯合國)、推動經濟發展(如世界銀行)和促進投資和貿易(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後來的世界貿易組織。
更為重要的是,正如很多美國學者所指出的,無論是這個秩序的產生、維持還是發展,都離不開「美國霸權」這一要素,包括美國強大的經濟軍事力量、其橫跨歐洲和亞洲的聯盟、用於威懾他國侵略的核武器等等。也就是說,「自由世界秩序」的存在,不僅僅是因為民主國家所共同接受的理念(即軟力量),更在於美國和西方所擁有的硬力量。
自由和非自由世界秩序的對立
也同樣重要的是,「自由世界秩序」的存在,還有賴於一個「非自由世界秩序」的存在,即以蘇聯為核心的非西方集團。這一前提至關重要,因為它意味着:第一,在冷戰期間,西方的「自由世界秩序」在地域上是有局限性的,只限於西方集團;第二,這一「自由秩序」的存在的理由,就是為了應付另一個「不自由的秩序」;第三,正是因為這個「不自由秩序」的存在,「自由秩序」內部的成員國願意放棄一部分主權,給美國來主導和統籌成員國之間的關系;第四,西方集團和蘇聯集團對「世界秩序」有全然不同的理解。
很荒唐的是,這個「自由世界秩序」今天所面臨的問題和挑戰的起點,便是這個秩序的全面勝利,即蘇聯的解體和冷戰的結束。儘管蘇聯和其為核心的蘇聯集團的解體,有其內部復雜的因素,但從西方的角度來看,這完全是西方自由秩序的勝利。這一判斷對西方尤其是美國的內外部行為產生了巨大的影響,至少可以從這幾方面來看。
第一,冷戰的結束導致了西方普遍認為,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是人類歷史所可以擁有的最好、最後的制度,西方無須對這一制度進行任何改革了。福山(Francis Fukuyama)的「歷史終結論」在西方名噪一時,就是西方這種樂觀情緒的真實反映。在冷戰期間,因為有一個「非自由秩序」的存在,西方政治人物還可以經常用外部的「威脅」,來對內部的一些問題達成共識。美國非常典型,政治人物總是用所謂的來自蘇聯和共產主義的威脅,來理解和解決內部所發生的政治問題(例如國內的社會運動)。在缺失一個明確外部「敵人」的情況下,西方內部黨派政治環境反而惡化,多黨民主經常演變成福山所說的「互相否決」政治。
第二,冷戰結束之後,在美國(西方)忽視內部問題和挑戰的同時,其外交政策則是另一番情景。因為對西方自由民主過度自信,美國開始花大量的人財物力,在全球範圍內推廣西方式民主,無論是通過各種形式的「顏色革命」,還是通過類似於「大中東民主計劃」那樣的政治軍事手段。
第三,美國和西方開始背棄建立在威斯特伐利亞秩序之上的主權國家理論,發展出所謂的「後主權國家理論」,對別國隨意進行所謂的「人道主義」的干預,無論是通過軍事手段還是其他手段。北約對前南斯拉夫的軍事干預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第四,美國因此開啟了一些學者所說的「新(美國)帝國模式」。無論是推廣民主還是人道主義干預,都是帝國擴張的手段和工具。
但所有這一切導致了帝國的擴張過度。帝國的擴張首先是地緣政治意義上的。蘇聯集團解體之後,美國西方很快佔據了前蘇聯的地緣政治空間。其次,通過上述各種手段,迅速把其地緣政治向全世界各地延伸。帝國的過度擴張對美國造成了巨大的問題,主要表現在地緣政治優先,經濟基礎跟不上,帝國成本過高,維持很難。擺脫了前蘇聯陰影的東歐國家,本來非常歡迎美國和西方的到來,但不久這些國家發現,美國和西方感興趣的只是它們的地緣政治意義,而對它們的社會經濟發展既無興趣,也無能為力。
這些新興民主得不到鞏固,傾向權威主義的右派政治經常回歸。其次,在很多區域(尤其是中東地區),美國的軍事干預不僅沒有促成西方式民主的出現,反而造成了無政府狀態,極端主義甚至恐怖主義盛行,成為區域乃至世界不穩定的一個重要根源。再次,即使是美國的傳統盟友的態度也發生了變化。
在很多問題上,美國不顧盟友的意見開始走單邊主義路線,早期表現在對伊拉克的軍事行動上,近年來表現在巴黎氣候協定、伊朗核協議等方面。同時,因為缺少一個類似蘇聯那樣的真正可以對西方構成威脅的「敵人」,美國的盟友開始不那麼樂意向美國付「保護費」。所有這一切使得美國要維持其霸權地位步履艱難。

自由世界秩序面臨嚴峻的局面
如果說美國所說的「自由世界秩序」有三個組成部分,即自由主義、普世性和秩序的維持,今天這個秩序的所有這三方面都面臨嚴峻的局面。
第一,自由主義意識形態在撤退。無論是歐洲還是北美,主要民主國家都面臨高漲的民粹主義。各種政黨都在借助政治極端化而急劇擴展它們的社會基礎。在英國,脫歐公投的成功表明,政治精英失去了共識,而把如此重要的決策交給並不了解事情的大眾。
這一方面意味着從傳統代議民主向直接民主的轉型,另一方面也意味着政治精英政治責任感的消失。圍繞着如何脫歐的政治紛爭,更是加深了英國各方面的危機。更重要的是,在自由主義核心的美國,總統特朗普本人從來沒有停止批評和攻擊被視為自由民主基礎的自由媒體、法院和執法機構。如上所說,東歐國家尤其是匈牙利和波蘭的政治人物,對新生的民主不那麼感興趣,權威主義開始盛行。
第二,美國構造「帝國」的意圖,就是把自己的原則通過「自由」的名義適用到其他國家,但事實上剛好相反。儘管經歷了數十年的全球化,但今天的世界很難說是一個整體。全球性多邊秩序建設的努力失敗了。美國本來可以是「自由世界秩序」的主體,但美國本身從這個秩序撤退,從維持者轉變成為破壞者。「美國優先」導致了美國保護主義的崛起。全球層面新的貿易談判要不無效,要不遙遙無期。正在變得越來越重要的互聯網領域,則根本不存在人們可以達成共識的「規則」。同時,人們所看到的要不是區域秩序的興起,要不是區域秩序的解體(尤其是中東地區)。簡單地說,儘管美國花費了巨大的努力,但所謂「自由世界秩序」不僅沒有擴張,反而變得更加脆弱。
第三,「自由國際秩序」本身難以為繼。在西方看來,現存「自由國際秩序」變得軟弱不堪的主要原因,在於其他大國的崛起和大國競爭的回歸。當北約使用武力干預前南斯拉夫時,西方認為這是正義的「人道主義干預」,但當俄羅斯使用武力改變了歐洲的邊界(克里米亞)時,則被西方認為是侵犯了基本國際規則。崛起的中國更被視為「修正主義」,對「自由國際秩序」構成最嚴峻的挑戰。這也就是美國把中國和俄羅斯視為是「自由世界秩序」的「敵人」的主要原因。
自由世界秩序的前景
二戰之後,英美之所以能夠確立西方所接受的「自由國際秩序」,有其特殊的歷史條件。首先,美國是被「邀請」成為西方世界領袖的。歐洲列強從一戰到二戰互相廝殺,戰後沒有一個國家有能力成為領袖,或被其他國家接受成為領袖,美國因此被「邀請」成為它們的領袖。其次,美國當時已經成為最強大的國家,有能力為西方社會提供公共品,尤其是馬歇爾計劃。其三,因為同屬西方,霸權從英國到美國的轉移是和平的。
這個秩序為世界提供公共品並且具有開放性,為大多數國家所認同和接受。更重要的是,這個秩序強調的是國家主權和各國之間的平等性,這是所有國家所追求的。不過,這個秩序具有先天缺陷。首先,西方國家已經解決了與主權有關的問題,但很多發展中國家沒有解決這個問題。例如在亞洲,很多與主權糾紛的問題是西方殖民地遺留下來的,到今天一些亞洲國家,仍然承受着殖民遺產之痛。
也就是說,儘管非西方國家認同這個「自由世界秩序」,但很難用這個秩序的原則,來解決它們所面臨的實際問題,尤其是關乎主權的問題。其次,「自由國際秩序」內部成員國的等級秩序問題。在美國主導的同盟等級森嚴,成員國迫於美國的強大和外在「敵人」的存在,沒有能力或者沒有意願挑戰美國,儘管不時有不同的聲音出現。
冷戰結束之後,當美國西方把內部的「自由秩序」原則,毫無節制地延伸應用到國際關系的時候,這個秩序最深刻的危機便發生了。這也是今天世界所面臨的局面。
未來世界秩序會是怎樣的呢?很顯然,鑒於美國西方今天所面臨的內外部困境、新興大國的崛起(中國、印度等)、老牌強權的繼續(俄羅斯),美國西方很難在推廣擴張「自由世界秩序」方面有很大的作為,尤其是在把西方內部自由秩序「國際化」方面。一個更有可能的場景就是美國西方的收縮,「自由世界秩序」重新回到以主權國家為基礎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即一個多元世界秩序。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艾利森(Graham Allison)最近也提出了類似的概念。在美蘇冷戰期間,美國總統肯尼迪提出了「保障多元並存的世界」(world safe for diversity)的概念,主張美國和蘇聯的和平共處,建議美蘇在一個政治體系多元、價值與意識形態完全相反的世界中和平共存。這個概念和上世紀50年代中國提出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具有類似的精神,即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
不過,從現實主義來看,是否能夠回歸和維持強調主權國家的「威斯特伐利亞秩序」,仍然取決於國家間的力量對比。任何一種世界秩序都是國家間力量對比的反映。從價值上說,美國西方的「自由世界秩序」的擴張衝動不會改變,只有當其遇到同樣力量的時候,才能停止擴張。從這個角度看,國際政治權力鬥爭永遠不會停止,和平是國家間權力制衡的產物。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