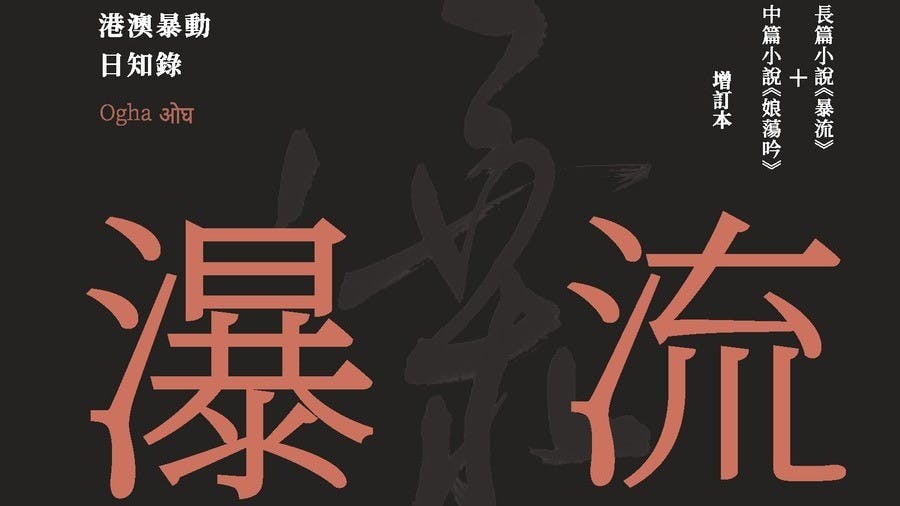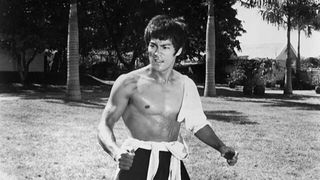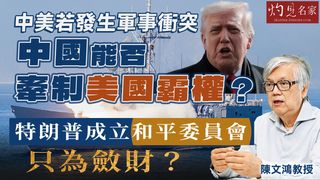《瀑流──港澳暴動日知錄》是陳永健先生兩本創作背景為1967年前後,葡殖澳門和英殖香港雙城,先後受到中國文革影響和殖民統治矛盾而發生兩場重要政治社會運動——澳門一二三事件及香港六七事件的中長篇小說合集。
與作者的緣分始於好友周蜜蜜。
一天,她跟我說:「你知不知道香港首部關於六七的30萬字長篇小說出版了?」因為過去十多年,自己一直致力在香港推動1967年的歷史研究和文藝創作,欣聞此消息,當然想多作了解。她說:「因為小說是藝發局贊助的。藝發局邀請我給他的小說寫個序。因此,便很清楚這本書的內容和出版了,也和作者相識。」
於是,就在蜜蜜的引介下,我們茶敘了。
局外人
陳永健給我的印象是位瘦削的斯文讀書人。原來他在上海出生,長於澳門,曾長期從事傳媒工作,1990年移居加拿大,隨後回流香港,並致力於張愛玲及珍.奧斯汀(Jane Austen)的作品研究。《暴流》不是他的第一部小說。他幾年前已寫就了一本關於澳門一二三事件的中篇小說《娘蕩吟》,訴說了七個不同背景的人在大歷史中不由自主「飄流」的故事。
而《瀑流》則是他寫作該中篇時所誘生的續作。他坦言,自己是澳門人,是澳門一二三事件的親歷者。但香港的六七事件,自己只算是局外人,但吸引他的是:與澳門毗鄰的香港,在一二三事件的漣漪後,發生了這麼大型的社會運動,當中有這麼多的市民被捕、入獄,又有這麼多的軍警、市民死亡。於是,他花了很大的精力做資料搜集,其中也包括自己和朋友促成出版的《傷城記》、《火樹飛花》、《印象六七》等。

席間,彼此相談甚歡。我很高興有局外人對香港六七事件有興趣,並自發地申請到藝發局的資助,出版這本以此大歷史事件為背景的創作。其實,當自己2010年起,推動六七事件的歷史補白、學術研究和文藝創作(包括書籍、舞台劇、音樂劇、紀錄片、故事片等)時,曾受到一些有心人的詆譭,質疑自己是幕後黑手,要「漂白六七」、「美化YP」云云。但現在值得高興的是,藝發局這個半官方機構,居然能夠贊助這本書的出版,可見六七議題在香港已不再是禁區,已成了一個百花齊放的文化生態園。
兩件事
不久,陳永健又告知,他的《娘蕩吟》和《瀑流》將會合併為一本增訂本,想邀請我寫個序言。而且他還告訴我,周蜜蜜已經應允替他的增訂本撰寫書評。既然「媒人婆」都上轎了,自然就不好推托了。因我真很欣賞陳先生將這段被人故意遺忘的歷史,變成一個虛構的文藝創作,一個開放式的歷史小說。
此外,更吸引我的是,他這個合輯,實際上是將澳門1966年的暴動與香港1967年的暴動,視作一整體而聯繫起來,足見兩件有密切關係的事件,對這兩個城市命運的重大改變。而這,也某程度呼應了我這位曾經的「六七少年犯」,在甲子求索自己當年如何被捲入五月風暴的成因。
在和眾多學者的交流和切磋後,我認為香港六七事件——戰後香港政治的分水嶺——的出現,是離不開新中國成立後,50至60年代港澳發生過的四次大型暴動,我簡稱為「三加一」,「加一」指的是澳門一二三事件,而「三」指的是香港1956年的右派「雙十暴動」、1966年天星小輪加價引發的暴動,最後當然是1967年的「左派暴動」或稱「反英抗暴」。
而香港的六七暴動,實際是始於一個11年前的「右派暴動」,一年前的一個「中性暴動」,緊接着四個月前澳門歷史拐點的「氹仔暴動」,最後才是香港的左派暴動,它是由這個脈搏走出來的。我的這個論點,也得到已故好友——歷史學者、美國史丹福大學陳明銶教授的和應。我倆認為,很多人只留意到1967年前後澳港兩地發生的兩個暴動的因果互動,卻忽略了兩城從此走上了截然不同的命運。因港英當局在此前已有兩次處理大型暴動的經驗了。
而澳葡政府的「跪低」,令澳門率先變成一個「半解放區」,激發香港左派向澳門取經效法的雄心,更令港英政府決心要鐵腕鎮壓可能發生的任何動亂,遂由工潮、到政治化的社運、到類似城市戰爭式的長達八個月的「白色恐怖」和「紅色抗暴」。

據當年曾參與鎮壓左派暴動的好友林占士警司憶述,港英在澳門暴動之後,已經馬上成立了防暴隊。它不是一般警員的編制,而是英軍編制。隊目成員特意物色多種族裔,好像他自己是中英混血的,還有南亞裔、歐裔等,他們在4月新蒲崗人造膠花廠工潮之前已在集訓。所以談六七,就不應忽略這個「三加一」的背景。
虛中尋實
初讀陳永健的兩部作品,文字流麗,且有紮實的史學背景,能讓讀者在虛中尋實,虛中融情。我尤其欣賞小說定題為《瀑流》。顧名思義,它首先是一強勁的水流——渺小的個人在大歷史之中,誰不是被強勁的水流推着走?而且在佛教中,「瀑流」梵文為ogha,即為煩惱之異名。四種「不善煩惱」(欲瀑流、有瀑流、見瀑流、無明瀑流)的流而不返,構成人世間的諸多煩惱「亂流」。而在革命激情、敵我分明的年代,這四種人生煩惱之矛盾就變得更尖銳了。作者在談到書名緣起時提到:
據天文學現象顯示,龍捲風的「漩渦狀氣流」是由下而上的卷動,而瀑流的「下沉氣流」則由上而下的擊降。這也符合書名的寓意,則當年黨中央造反派及四人幫策動的文革瘋潮,一度由北而南的席卷港、澳,徹底改變兩個殖民區的政治生態。這個60年代三生三旦的世情故事,亦可視為「大陸文革」與「港式傷痕文學」的一次偶遇。
或者謹引《大公報》在其百年史中,曾轉述中國總理周恩來在1967年底為「反英抗暴」做的總結:
第一,英國人用暴力鎮壓工人和左派群眾,負有重要責任;香港群眾反對英國人的暴力鎮壓,是合理的、正義的、英勇的;錯誤是在於領導人把事件擴大為一場動亂;第二,香港左派領導人的錯誤在哪裏?周恩來說,「是受極左思潮所利用」這句話說得含糊,因為當時林彪和「四人幫」還掌握權力,周恩來這句話,其實是說香港左派領導人受林彪和「四人幫」利用。第三,周恩來說,這次錯誤,「香港有責任,北京有責任,主要責任在北京」。(註)
由此,讀者可以思考,1967年前後港澳的兩場政治社會運動,是否完全就自上而下?或由下而上的「瀑流」,又曾否發生過作用呢?
古人言: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鑑,可以明得失。相信若細讀這本史詩式的小說合集,讀者必有所得着。
是為序。
2024年4月4日
甲辰•清明
註:方漢奇主編,《《大公報》百年史(1902-6-17─2002-6-17)》,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頁433至4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