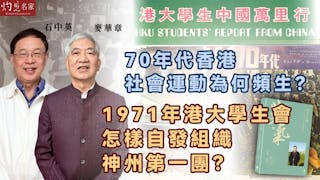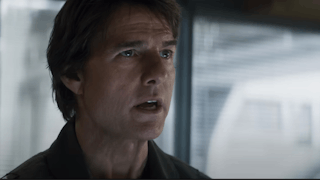承接前文:〈人之初,性本善?──從心理學看本地的「孩子」心理〉
盧梭將兒童本性予以理想化,猶如純潔無暇的天使,可以對抗和救贖世俗,在趨於墮落的社會中保持天性中的善良。但要知道,他即使有偉大理想和悲憫情懷,但卻沒有什麼教育經驗,一生中也只當過不到一年的家庭教師。他的教育理念並不只是扎根於現實社會,還有充滿理想主義式的主觀臆想和盼望。
隨着心理學認知的推進,該理論受到某程度的質疑。自佛洛依德開始,很多心理學家把研究目光集中在不染世事的兒童身上,包括榮格和弗洛姆在內的心理學家,認為兒童心理的發展是「生物性和社會性共同作用的結果」,而前者佔了很大比重,從而歸納出兒童具有「自我中心化」的心理模式。
什麼是「自我中心化」?
對此心理狀態,法國心理學家皮亞傑(Jean Piaget)的分析相當清晰:
「兒童以他自己的感知和動作,乃至情感和想像、觀念,從自己的視角或立場來看待和理解周圍世界中的一切」,「在無知中就把自己當做權衡世間的一切標準」。
因此,在兒童思維裏充滿了簡單的因果聯繫和必然判斷,包括對偶然性的回避,對必然性、因果性的強調,使得他對萬物的價值判斷偏向兩極,認為事物之間只有善惡之分,不會存在灰色不明的空間。
而德國心理學大師阿德勒(Alfred Adler)是如此描述孩子:
「我們不要忘記,孩子看問題和我們成人不同,他們傾向於把世界劃分為對立的兩極。如果要理解兒童,我們就不能忘記這個非常重要的事實,即兒童有一種把世界劃分為兩個對立部分的強烈傾向(上或下、全好或全壞、聰明或愚蠢、優越或自卑、全有或全無)。
阿德勒更指出,不單是兒童或青年,連成人也依然具有這樣的認知方式,我們可以認為,那些習慣把世界分為尖銳對立的兩個部分的成人,仍然保留着他們兒時的思考方式,即二元對立的認知方式。」
對於這類對立的、或非此即彼的認知方式來思維的人(包括兒童和成人),阿德勒用了一句格言來形容──「要麼全有,要麼全無」(”all or nothing”)。他認為如此理想並不可能實現,但是「卻有人如此安排自己的生活,忘了在兩個極端中間還有許多選項。」

在研究過程中,他發現具有這類思維的人有以下特徵:
「我們發現擁有這種思維方式的人,主要是兒童,一方面有着強烈自卑感的煎熬,另一方面發展出做為補償的過分野心。歷史上有不少這樣的例子,例如凱撒。許多兒童的怪癖性格,例如偏執和固執都可以追溯到這種『全有或全無』的認知方式。這種特徵在兒童的生活中俯拾皆是。」
他們過於關注自己,總是沉溺於白日夢和幻想,並在這些白日夢和幻想中,自己變得很偉大,或很厲害。在這些夢裏,現實消失了──他們是君臨一切的英雄,或是握有生殺大權的暴君,或是救苦救難的烈士。
「我們經常發現有些兒童不僅在幻想之中,也會在現實行動中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如果他們還未完全喪失自信,一旦機會出現,他們就會扮演這種角色。」
以上是心理學大師們對於盧梭「兒童純真論」的質疑和補充,這裏絕非否定盧梭的觀點(盧梭的教育觀點是無比偉大,震撼人心的,需要另闢篇章),只是在過度注重天性和純真之外,找到兒童心理深處的另一面相,令我們可以更為全面的審視兒童和青年,甚至那些依然保留着兒時思考方式的成年人。
米蘭·昆德拉的洞察
在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的小説《笑忘書》(The Book of Laughter and Forgetting)中,就相當傳神地呈現出「兒童自我中心化」的面向,以及所導致的悲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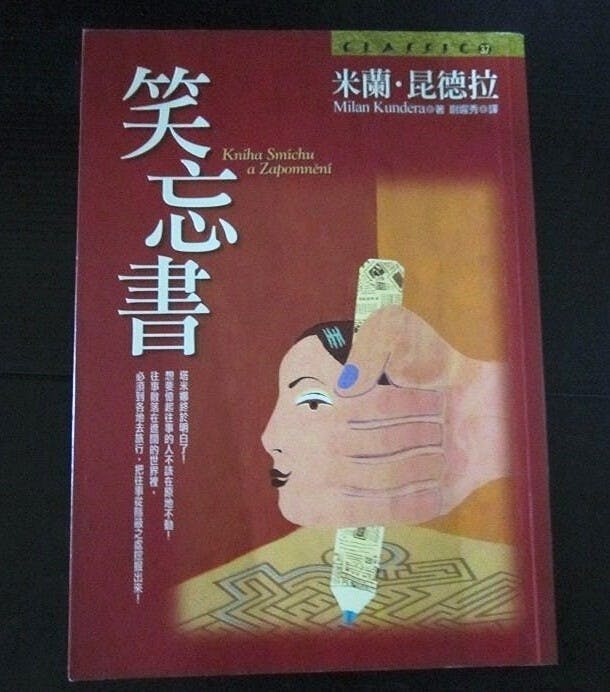
故事的主人翁泰咪娜來到兒童島,這裏的孩子善良天真,友善好客。但當泰咪娜沒有遵從他們的遊戲規則時,孩子們就對她施以暴力,逼迫她重覆地用他們的方式來玩那個跳格子遊戲,「跳格子,單腳跳,然後另外一隻腳跳,然後雙腳跳,她還要把是否踩線看得很重要。她要日復一日地跳下去」。泰咪娜無法忍耐,多次逃脫未果,最後在孩童純真眼眸的注視下溺死水中。
昆德拉說,「泰咪娜是在天使的笑聲中死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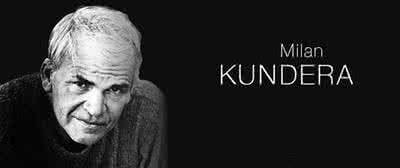
在這個隱喻中,昆德拉從從孩子的天真裏看到了令人震驚的恐怖:孩子單純要求世界都服從於他,對外在於他的東西拒不接受。
昆德拉將此延伸至現實中「價值廢黜」的現代社會,人們企圖在對「兒童」的詩意建構中尋找失落的伊甸園,來安放自己的破碎靈魂,但這個「樂園」是虛偽的,「它天真美好裏暗藏着專制的恐怖。」
他進一步認為,在某個歷史階段,成人社會的運行也會出現兒童島上孩子們的心理機制。在面對現實世界中複雜情況時,成人也會無意識地希望世界變得「單純」些,能善惡分明,「有一套穩定正確的價值評判體系,以減輕價值判斷和頭腦分析上的負擔。」
以上洞見,如果將之套用在3年前香港激進青年人的種種心理和行爲,以及某類大人們的種種反應,倒是相當吻合,值得我們在此理論框架上,進行更深入的反思。
具體論述,請看下篇文章。
青年心理 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