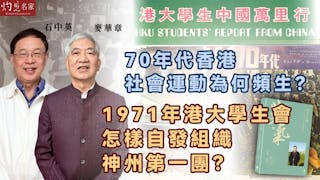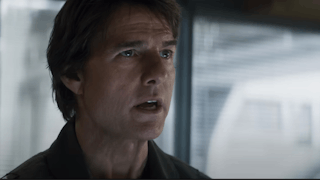編按: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早前與新力量網絡聯合舉辦「香港回歸二十年研討會」,分兩部大主題研討,講者陣容鼎盛。第一部分題為「回歸二十年成與敗」,講者包括中山大學港澳珠江三角洲研究中心教授陳麗君、香港教育大學副校長呂大樂、國立台灣大學社會學系教授何明修、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第二部分題為「中國的未來」,講者包括美國加州克萊蒙特·麥肯納學院政府學教授裴敏欣、民主黨前立法會議員何俊仁、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教授徐斯勤、香港大學金融學院經濟學講座教授王于漸。呂大樂教授就「回歸二十年成與敗」作出主題分享,以下是他當天的演講內容:
我認為討論「一國兩制」的成與敗,必須首先了解「一國兩制」本身是一種三方勢力下妥協的產物,故此無論中國、英國或香港,必然沒有任可一方能完全滿意,沒有一方能單方面以主觀意志決定一切而毋須讓步。今天已經距離當初起草《基本法》已有三、四十年之久,對年青一代而言,確實難以想像當年我們究竟要妥協什麼。香港前途問題,真的是如Richard Hughes所言是「借來的時間」。大家若然不提,彷彿一切都能繼續下去,但當你置身於1979年的香港,1997似乎又真的很遙遠,一切似似乎都能繼續,就連時任港督麥理浩,也抱着類近心態去北京,就是因為1982年前若未能解決香港前途問題,則跨越1997的樓宇按揭將無所適從。
從英國解密檔案中可我以看出,1979年英方欲獲得繼續管治香港的權利,而當時鄧小平向港督麥理浩強調兩點:
一、請香港投資者放心;
二、國家主權必須嚴肅看待。
麥理浩回港後只提及前者,向港人大派「定心丸」,但卻對國家主權一事絕口不提。
回歸後一切如常?
當時中英雙方均有其考慮,英方考慮在冷戰的大環境下,要如何恰當地把一塊前殖民地交給一個威權國家;而中方雖然是嚴肅看待主權問題,但若收回一個失去「馬照跑,舞照跳」的香港,對國家發展又有何用?
香港的想法就顯得簡單多了,就是真的「想不到要回歸中國」,想當初香港民眾大多是為了逃避共產黨而走難來香港的,但轉過頭又要重新面對共產黨的管治,這恐怕也是紅旗下成長的新一代香港人所不能想像。
當時的妥協本質上就是為香港人留下一個可以接受的環境。 所以在此妥協下,中國亦要接受治下出現一個行資本主義制度的特別行政區,亦不能在香港成立黨支部監督香港,控制特區言論,及以用大陸法律治港。
香港當時也要面對的困境是:維持英國管治的現狀是難以實現的,現在想來有趣,似乎當時亦有人認為經濟現狀的不變,似乎就能補償政治上的改變,但事實上當時的轉變並不大,我們那時普遍相信,回歸不會出現重大政治變動,不過是在1997年7月1日換枝旗,而其他則會一切如常。
現在回想仍覺得80年代的香港很神奇,我們那時曾經就英國西敏寺制還是美國總統制較適合香港而研討,亦談及政治問責制的實行,甚至為行政立法的矛盾討論,但不知為何,最後都無疾而終。但其實當年的一切討論都是以維持現狀作考慮,最怕的是一個改變的香港。故此,我認為「一國兩制」最佳的比喻,就是人們把80年代最美好的事物急凍起來,放進雪櫃直到97年再拿出來解凍,接着居然可以神奇地再用上50年。
然而,在面對政治環境改變,周邊地區關係轉變,以這種「不變」的思維來面對改變,顯然是不足夠的。以1979年的預估來應對2047年的挑戰,本質上就不可能,更何況當年的「一國兩制」是為了滿足戰後嬰兒潮世代的考慮,而非滿足今天新一代截然不同的追求。中間存在的缺口是當年所不能預期的。
金礦?負累?
事實上,「一國兩制」最初就是針對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種制度,就如《基本法》中就私人產權細緻描寫到政府不能在賠償時用任何藉口改變賠償的價值,這顯然是立法者參考了1952年在上海的「五反運動」中,政府巧取豪奪商人財產的事情。還有不准中央抽稅,不准奪去香港財政儲備等等,《基本法》中關於中央地方關係都是基於恐懼共產黨會奪去市民的身家性命財產,但今日回望,發現中國的社會主義早已非當初,反倒是要害怕內地資金透過市場來支配香港,例如買地、買公司;另外區域融合亦非當初《基本法》的考慮。縱觀《基本法》,可以發現對於人口流動亦都是假設了內地對香港人口的單向輸出,但我們很快發現內地經濟起飛,雙向流動才是對港人有利之舉,但人口流動的規模卻往往是難以控制的,致使香港眼下每年接待超過4,000萬遊客,這個別人眼中的金礦早已成為我們的負累。
另外,《基本法》的前瞻性也確實不足,當年中英雙方都沒有想到未來要如何發展中港關係,致使雙方關係發展相當「奇異」,即使早前習主席訪港,還是強調一句「蘇州過後無艇搭」。其實中央治港的手段由以前到現在也就兩種論述:有着數(有好處)及血濃於水,也即物質利益與愛國心,只不過回歸前強調五十年不變,不影響香港利益;今日以背靠祖國崛起為吸引,但若這經濟物質利益無法實現,就會由一個極端拉到另一個極端,即強調民族主義血濃於水的先天因素,似乎只要喚醒香港人潛藏的愛國心,就萬事皆可解,我認為在物質利益與高度感性的民族主義之間是一片空白,亦即缺乏以一顆平常的心看待中港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