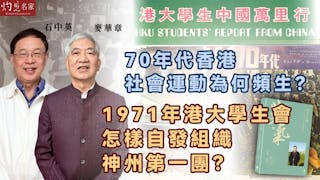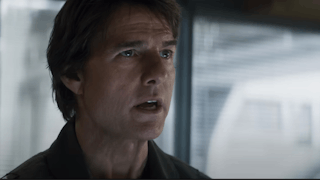外交是內政的延伸。民粹主義、反全球化、種族衝突、政治歧見等因素,不斷加深着美國內部的認同政治紛爭。美國政治人物也急速地把認同政治延伸到了中美關係,使得美國對中國的認同政治戰,升級到白熱化的程度。
認同政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視自己為常態,而與己不同者為非常態,因此在把自己高度道德化的同時,把對方妖魔化。同時,如同認同政治在美國內部表現為高度分化,美國也同樣用美國內部分化的方式,針對中國的內部進行分化。
美國對中國內部分化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即漢族與少數民族之間的關係(利用新疆西藏問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之間的關係、中國共產黨集體和其領導集團的關係。近來隨着香港和台灣問題的日益突顯,美國也開始搞中與華之間的分化,即把中國大陸視為中,而台灣和香港視為華。
在對中國的認同政治戰中,美國不僅強化着其意識形態的話語,但並不滿足僅僅停留在意識形態層面,而進入到具體的政策操作層面。再者,強化意識形態層面的政治認同的目標,便是論證其具體政策的合理性。道理很簡單,一旦在認同政治層面把中國妖魔化,美國對中國實行什麼樣的政策都是合理的了。這種認同政治不僅是針對美國國內的民眾和國際社會,也試圖影響中國民眾。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6月25日在德國馬歇爾基金會的布魯塞爾論壇上,發表了題為《一個新的跨大西洋的對話》的講話,重申了他6月19日在哥本哈根民主峰會上的論點,呼籲歐洲盟友共同應對中共政權所帶來的挑戰,說不是美國對抗中國,而是世界須要對抗中國。
他說,儘管美國與歐洲在意識到中國這個威權政權的崛起,及其對自由社會的影響的問題上都很緩慢,但是中共政權所採取的一系列行動,使美國與歐洲都覺醒過來。蓬佩奧說:我今天要傳達的信息是,為了維護我們的自由社會、我們的繁榮和未來,我們必須共同努力,繼續大西洋兩岸的這種覺醒,以應對中國的挑戰。
他說:有關美國應該緩和與中國的緊張關係的論調,是無稽之談。我們不接受這種論點。在自由與威權之間是沒有妥協的。我不希望我們的未來由中共來塑造。現在的問題並不是美國迫使歐洲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做出選擇,而是中國在迫使歐盟在自由世界與中國的威權願景之間做出選擇。他說,他看到歐洲大陸對中國有着更加現實的看法。
他提出美國要聯合歐洲來共同對付中國,說美國接受歐盟外交事務負責人博雷利提出的成立美國與歐盟對華對話機制的提議,並且會儘快建立這個機制。

6月24日,美國白宮國安顧問奧布萊恩在訪問亞利桑納州時,借着對20多名企業高管對話的場合,發表一篇近30分鐘的對華政策演說,批評中共在中國的極權主義及對世界輸出意識形態的擴張計劃。他說,美國過去因為忽視中共的意識形態而天真地與其往來,但這個時代已經終結。他預告美國將祭出更多制裁,還將徹底揭露中共的全球擴張計劃。
奧布萊恩表示,美國自1930年以來外交政策最大的失敗就是誤判中共,天真地以為與中共來往,會促使它變得更加自由。而美國之所以會誤判,是因為美國忽視了中共的意識形態。奧布萊恩譴責中國政府盜竊知識產權、打擊人權、咄咄逼人地擴張、掩蓋冠狀病毒在武漢的起源、利用社交媒體進行宣傳和傳播虛假信息,以及驅動這一切的意識形態。
他說:特朗普政府將揭露中共的理念與陰謀,不只針對香港或台灣,而是針對全世界。他誓言:特朗普總統明白永久的和平,來自自身的強大。美國是世上最強大的國家,我們不會向中共低頭。
奧布萊恩在演說中,細數特朗普政府已對中國所採取的七大反擊措施,包含對華為公司的禁令、國務院將九家中國官媒列為外國使團、針對與新疆問題有關的21個中國政府實體及16個中國公司祭出出口禁令、因世衛受中國控制而終結與世衛的關係、限制解放軍背景的學生簽證、暫停美聯邦退休基金對中國股票投資計劃,以及由美國國防部列出多家被解放軍操控的公司清單。
而這一系列的舉措只是剛開始,旨在修正過去40年單邊的不公平關係,(這些錯誤)已經嚴重影響了美國的經濟及近期的政治安全。如同特朗普總統對中國不公平貿易所加的關稅一般,更多制裁措施將出台。

美國搞認同政治目的
在實施對中國的認同政治戰的時候,把所謂的中國影響力清除出美國,成為了美國的當務之急。認同政治戰的核心是影響力,而美國把中國在美國的媒體,視為是對美國的直接滲透。美國不久前將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CGTN)、中國國際廣播電台(CRI)、《中國日報》發行公司和《人民日報》的海外代理美國海天發展公司這五家中國媒體機構,認定為外國使團之後,美國國務院6月22日又將中國中央電視台(CCTV)、中新社、《人民日報》和《環球時報》列入名單。國務院說,這些媒體受中國共產黨控制,不是獨立的新聞機構。
的確,如同美國外交政策所顯示的,美國搞認同政治的目的是塑造一個認同政治國際聯盟,共同應付中國。這些年來,美國隨着其內部社會政治衝突的突顯,在國際上顯得力不從心。
特朗普上台之後,美國加快了從國際舞台上退縮。儘管美國的盟友都希望美國繼續扮演國際領導角色,但這並沒有減緩美國從國際退群的速度。不僅如此,特朗普政府還屢屢對同盟施加壓力,要求他們在維持和美國的同盟方面承擔更多的費用。
所有這些使得美國的盟友對美國另眼相看。在這次冠病疫情中,沒有一個美國的盟友向美國尋求幫助。這是美國進入世界體系一個多世紀以來,從來沒有發生過的。過去,美國總是其盟友尋求幫助的首要考量,而美國也大多為其慷慨解囊。美國在國際舞台上角色的變化,使得美國的盟友開始改變對美國的看法,並且直言不諱。德國總理默克爾6月26日在接受英國《衛報》等歐洲六家報紙聯訪時說,不要認為美國仍想當世界領袖;如果美國自願放棄世界大國角色,德國須深切反思。
美國對自己的國際地位的變化,並不是沒有深刻認識。至少從奧巴馬當政之後,美國開始了減少對國際事務的承諾。這些肯定是要影響其國際地位的。同時,美國大大低估了中國崛起的速度和中國崛起的走向。美國政治人物希望中國變成另一個西方國家,這是可理解的,因為沒有一個西方式的民主國家可以挑戰美國;一旦成為民主體制,美國總是能夠找到干預這個國家內政的有效方法。
因此,在這樣的情況下,認同政治成為美國對華政策的一個有效方式。在美國看來,之所以有效,是因為兩個方面的原因。第一,在國際層面,儘管認同政治表現在意識形態領域,但遠比意識形態廣泛,因為認同政治不僅包括傳統的種族、民族、宗教等因素,也包括民主、自由和人權等在內的社會世俗價值觀,更可引申到文明之爭。
如果這樣,美國便可以結成廣泛的政治認同國際統一戰線。的確,正如前面所討論的,美國高官和國會議員近來一直在向其盟友和世界兜售這樣一個概念,即他們是否和美國站在一起對付中國,並非中美之間的選擇,而是專制與民主之間的選擇。早些時候,美國官員也直言不諱地把中美衝突視為是文明衝突。第二,如前面所討論的,認同政治可以通過分化中國內部,促成中國內部的變化。

作用與反作用的模式
美國對中國的認同政治戰,會把中美關係導向何方呢?
在很大程度上,中美兩國之間的關係已經演變成為物理世界的作用與反作用的關係,無論哪一邊有什麼樣的動作,另一邊必然機械地反彈過來,從而進入了自由落體模式。自冠病疫情發生以來,美國的任何舉動必然導致中國的強烈反彈。
這種作用與反作用的模式儘管可以理解,但對中國實際上是非常不利的,即中國容易陷入美國所設定的認同政治議程。兩國抗疫明明是兩國內部的事情,因為抗疫是否成功,受到影響最大的是本國的老百姓的生命,而不是另一國的老百姓。美國因為各種因素抗疫不力,試圖推責中國,毫無理由地把疫情傳播和中國政治制度聯繫在一起。即使在美國國內,反對推責中國的聲音也不小,因為推責中國解決不了美國的疫情傳播問題,拯救不了美國老百姓的生命。
但很可惜,被視為是中國的強有力的回擊,很快在中美關係之間上演了制度之爭、價值觀之爭和生活方式之爭。美國認為自己的政治制度、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受到了中國的威脅,而要從各個方面進行針對中國的保衛戰。至少在民間層面,中國也具有類似的認知,導致了高漲的民間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對美國爭鋒相對,以牙還牙。
人們把這個局面與美蘇冷戰期間兩國意識形態冷戰類比。的確,除了核武器互相威懾之外,美蘇兩國最激烈的戰場就是在意識形態領域,即美國所說的自由資本主義和蘇聯共產主義之間的對抗。不過,就美國所展開的對華認同政治戰來說,中美在這個領域的情況,可能要比美蘇冷戰期間的情況更為糟糕。畢竟如果美國人相信文明衝突,這種衝突並不存在於美蘇關係中間,但存在於中美關係中間。
實際上,就認同政治的範疇來說,美國可以把這種衝突擴展、擴散到任何一個領域。這裏的核心在於,一旦美國通過認同政治把中國妖魔化,美國對華實施怎麼樣的政策都具有了道德的高地。
中國如何找到其他更有效的方式,來應對美國的認同政治呢?如果美國搞認同政治,中國也搞同樣的認同政治,兩國必然陷入認同政治的惡性循環模式。今天的情況就是如此。
經驗地看,中國其實可以有更有效的方式,即包容方式。包容也是中國世俗文明最主要的特質,這個特質也使得中國文明吸納了包括佛教在內的外來文化。但即使人們不討論久遠的過去,1949年以來的經驗,也足以說明包容方式的有效性。
建國之後,中國曾經實行向蘇聯一邊倒的政策。和蘇聯決裂之後,中國也經歷了高漲的反美民族主義浪潮。但毛澤東三個世界理論的提出,表明他的務實政策,即國家政策不為已有的意識形態所制約。儘管當時美蘇處於兩個意識形態的對立面,但毛澤東的務實政策,促成他把美蘇兩國同時視為霸權主義。
儘管處於第二世界的國家都是資本主義國家,與中國本身的意識形態相對,但所有第二世界的國家都是中國交往和合作的對象。在基辛格博士秘密訪華之後,中國更是和自己的意識形態的對立面的美國結成了準同盟,共同應對蘇聯帝國主義。
鄧小平的不爭論更是包容方法的體現。針對當時意識形態領域進行的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之爭,鄧小平提出了不爭論,認為市場經濟只是一種制度手段和工具,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都可以使用。之後,中國有機地把市場經濟和社會主義融合起來,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理論,引導了中國數十年的高速經濟增長。
鄧小平之後的很長時間裏,儘管中國努力抵制西化,但從來沒有停止與西方對話。即使在民主、自由、人權等等問題上,中國也一直抱着求同存異的態度,和西方保持對話。經驗表明,只要通過對話,很多領域都是可以達成一定的共識的。畢竟,實際的中國並非西方認同政治中的中國,更何況中國和西方之間存在着巨大的共同利益。
一句話,在美國開始把中美關係導入認同政治戰的時候,中國不得不思考如何避免讓美國人牽着自己的鼻子走的問題。
原刊於《聯合早報》,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