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化底蘊之建立絕非一朝一夕,需要正確的態度,亦需要時間的浸淫,但前提必須要先了解自身的境況,認清「花果飄零」的慘淡現實,有此自知之明,才能夠補己不足,踏步向前。

許多文化人都曾在香港創辦文藝雜誌,但現存的已不多;現在居然還有人戮力創辦新雜誌,包括三聯的《讀書雜誌》。一群資深出版人與作家對此有什麼看法?他們又如何看待香港的出版業與市場環境?

10年匆匆過去,我還在過着難以調控的忙碌生活,未能忘卻營營。不知脫離了肉身束縛的黃兆傑教授這10年過得怎樣呢?

看完整篇故事,總想不通金庸幾十年後開筆寫文藝小說寫一個「生得醜,毫不可愛」的小丫頭,而寫得這麼傳神和用心。真是高深莫測之至。

台灣作家柏楊《醜陋的中國人》一書,1986年在中國大陸出版後旋即掀起「柏楊熱」,後此書被禁,直至2004年才可再次出版。遺孀張香華近日斷然拒絕摘文選入台灣教科書,並向兩岸出版商聲明將永遠停止發行此書。

江迅1994年移居香港,加入《亞洲週刊》擔任資深特派員,以他在內地文化及新聞界的深厚資歷,很快就嶄露頭角,闖出名堂,很多獨家報道挖出鮮為人知的內幕消息。

吳老說過:「經常和年輕人在一起,自己也會變得年輕快樂。」而我身為年紀最輕的「黨員」,竟有幸親炙各位老師比我更年輕的心境,這段意想不到的因緣,就是我日後的一帖長生不老之藥。

倪匡是香港著名作家,據說在香港能搖筆桿寫稿賺大錢的只有金庸和倪匡,不知是否事實,但筆者相信極了。

新冠疫情持續快兩年,各行各業受影響,舊書買賣也無可避免陷入困境,然而天無絕人之路,舊書巿場最近走出一條生路,城中幾位書商各自開設了網上拍賣群組,引致本地愛書人深夜難眠,也出現不少啼笑皆非的現象。

這個故事架構與《福爾摩斯探案》有相似之處,但莫理斯聰明之處,是加入大量真實可考的地名、人物、歷史事件及掌故,可見莫理斯查閱資料之勤,不只是跟着福爾摩斯的「化身熱潮」說故事也!

曾幾何時,香港的「小報」數量多如繁星,它們之中有些閃爍生輝,有些稍縱即逝,沒有留下痕跡。其實,小報在香港報業史上佔很重要地位,可惜至今缺乏有關香港小報的學術研究,遑論要寫一部香港小報史。

聞名華人世界的武俠大師金庸辭世轉眼3年,香港除了設立一個金庸館外,並無其他紀念活動,實在寒酸,也太對不起金庸對社會的貢獻,本人謹此倡議香港政府設立「金庸文學獎」。

芝泉老人後來戮力以赴三造共和,竟不能與後世共推移。康有為詩云︰「但見花開落,不聞人是非。」芝泉老人晚年落居帳棚中,於外間是非早已還諸天地,留下詩文名為《正道居集》不過明志而已。

芝泉老人已是一介平民,為袁家園林遭人踐踏沒收,親筆致蔣介石函,希望能保護袁世凱遺產。他在手札中說「保障人權即整飾綱紀之要務,綱紀實而國家未有不治者」,他的寬厚與用心是兼而有之的。

雖然拙著未有被批評為「不知所云,離題萬里」,但筆者反覆思量,不如再寫一章,臚列出《射鵰英雄傳》中多不勝數,並以兩大啞謎──「調轉」和「合而為一」構成的情節和武功招式。

我一直認為,諾貝爾文學獎,毋須太認真看待。這不是故作驚人之語而是常識:不管是諾貝爾還是布克獎,文學獎不是奧林匹克運動會一類優勝劣敗的競技場。

本港著名作家、資深傳媒人、《亞洲週刊》副總編輯江迅13日(周三)離世,享年74歲。

石依琳(Lam)認為「人生,不是想過而是走過的路,不關乎是否崎嶇。」

唐人宜更賞唐詩,色麗音和造語奇;欲學中文佳礎在,古今賢母教兒時。

各詩所附之原韻及譯文實為《原韻譯唐詩新賞》最大特色,此亦可見作者陳耀南教授對聲韻之掌握。每首標示韻部,為別家所無。

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由以「難民」主題貫穿作品、來自英國的坦桑尼亞小說家古爾納(Abdulrazak Gurnah)獲得。

胡曉明的父親、人稱「電梯大王」的胡法光博士,今年97歲,是菱電創辦人兼名譽主席,是活躍本港政商界數十年的傳奇人物。《胡法光傳奇一生》記錄了胡法光的家學淵源、英國實習的經歷、留港發展的歷程。

他喜歡誰,就說出來,成為了詩的泉源,他把粗言俗語也入詩,他不是要做詩聖詩仙,他要的,就是每天喝茶下棋、賽馬寫詩「過日晨」,就已經心滿意足。

在魏徵面前,一邊是掌握生殺大權的君王,一邊是危機四伏的國運,他始終堅持嚴正的立場,絕無寬貸討好之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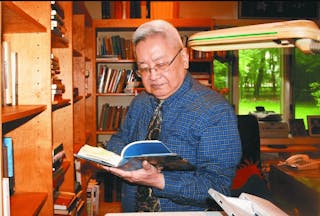
與余英時教授首次見面,是1980年代初的事,地點在台北市聯合報大樓。當時,聯合報創辦人王惕吾(1913-1996)董事長請他吃午飯,邀我參加……

古文需要反覆閱讀,不可能一遍就讀懂了,更做不到完全領會。對於我們每一個人來說,提高文學閱讀的能力和修養,都是一輩子的事情,不可能立竿見影,當即生效。我的願望是編撰一冊古文讀本,讓它陪伴着年輕朋友成長。

「熟讀唐詩三百首,不會吟詩也會偷」,第一天讀唐詩,老師已說過這句鼓勵說話,可惜到現在我還是詩的門外漢。政壇元老黃宏發厲害得多,他退休後不斷吟詩,已成唐詩專家,還把100多首唐詩翻譯成英文。

隨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寫作意識的重視和發表渠道的暢通,這類學林敘事相信還會有更蓬勃的發展,這當是指日可待的。陳煒舜教授近年來積極投入當代學林人物的追憶與記述,為當代學術界留下第一手的文獻史料。

1922年新學制頒布後,除了印行語體文教科書外,內容也兒童文學化起來。文體兼採童話、小說、詩歌等,着重兒童的閱讀興趣。

書寫的年代已逐漸遠去。文人的信劄、手跡已成為歷史陳跡。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潘耀明做過現代中國作家研究,編過文學書和文化雜誌,與文化人接觸和交往特別多,也收集了一些文人墨寶、手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