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接上文:〈要穩定社會必須培植中產階級〉
簡單地說,我們還沒有解決傳統工業革命所帶來的社會問題,即我們沒有能夠造就一個龐大的中產社會。
比較而言,這已經為我們的社會治理帶來了巨大的挑戰,例如在其他東亞社會呈現出「先富後老」局面的同時,我們則面臨着「未富先老」的情況。更為嚴峻的是,今天我們已經快步進入了人工智能社會。這對我們的社會治理構成了新的挑戰。
我們知道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經濟基礎也決定社會秩序。在漫長的傳統農業社會,社會秩序歷經數千年,但因沒有革命性技術的產生,社會秩序只有量變,而沒有質變。近代以來,技術革命不斷導致經濟革命,經濟革命不斷導致社會秩序的變遷,從工業社會秩序到後工業社會秩序再到訊息社會秩序。今天,人類開始進入人工智能時代,人工智能對一個國家的任何一個個體及其經濟、社會、政治體系,乃至對國際政治都產生着愈來愈深刻的影響。
修正普遍賦權
我在2014年出版的《技術賦權:中國的互聯網、國家和社會》一書中,結合中國的案例,開始探討互聯網對社會的影響。當時還處於博客時代,但互聯網已經對人類社會的方方面面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儘管當時的互聯網對國家和社會的影響也表現為正、負兩方面,但我的結論比較樂觀,認為作為技術工具的互聯網具有「普遍賦權」的功能,既賦能政府,也賦能社會的各個群體。
但是,至少就今天的現狀來說,「普遍賦權」這一觀點需要得到修正了。高科技發展到人工智能的階段,其賦權的能量的確愈來愈巨大,但其賦權表現為絕對的不平等和不均衡,這種不平等和不均衡不僅表現在一國之內,更表現在國家之間。從經驗看,在一國之內,人工智能對國家、對公司、對個人的賦能呈現極度失衡狀態;對國家間來說,人工智能僅僅分布在少數幾個大國,大多數國家並沒有能力擁有人工智能。
近年來,我一直在關注人工智能對社會的影響,形成了一些看法,不妨在這裏再說一下。概括地說,人工智能對社會的影響需要從兩種結構性因素來分析,一是人工智能所呈現出來的技術結構,二是技術結構所造成的治理結構。

人工智能的技術結構特徵
這個層面分析人工智能時代高科技所呈現的結構性因素,以及這些看似互相矛盾的因素對社會群體所能構成的傷害。簡單地說,人工智能時代高科技呈現4個技術結構特性。
一、技術能力的高度集中性(highly concentrated)
即人工智能的技術能力是高度集中的,集中在少數幾個大國的幾家大公司。就世界範圍內看,中、美兩國擁有大部分人工智能技術能力,其他國家也擁有一些,但難以與中美兩大國匹敵。再者,就中美兩國來說,美國目前擁有更多的技術能力。今天,儘管美國公司一直在宣揚中國在人工智能領域對美國公司構成了巨大的競爭壓力,但是無論從理論、還是經驗層面看,人工智能領域有意義的競爭都發生在美國的幾家大公司之間,而非中美之間。從技術端到數據端,從大模型到應用,中國和美國的差異依然巨大。儘管最近中國DeepSeek的崛起打破了美國之前所處的幾乎壟斷地位,但需要意識到DeepSeek是基於開源的基礎之上產生的,誰都不能保證DeepSeek何時會被再超越。
在西方發達國家和地區,對基於傳統技術之上的產業的反壟斷已有一套成熟的方法。一般都是通過分解一個企業以防止其取得壟斷地位,從而為創新和新企業的產生創造制度條件。但是,對高科技企業如何反壟斷迄今依然是一個巨大的問號。傳統分解企業的方法可行性不高,因為高科技企業都基於互聯網之上,如果分解,就不符合訊息產業的發展邏輯。從針對微軟公司的反壟斷案來看,現在針對高科技企業的反壟斷基本上採用以「開放」替代傳統分解的辦法。但問題在於,這種「開放」替代的實際效果反而使得這些訊息產業變得更加龐大。
就人工智能產業來說,美國如今的發展已經達到了相當發達的程度,但至今還沒有聯邦層面的任何監管體系。可以說,如果找不到有效的反壟斷機製,那麼這個產業的集中度只會愈來愈高。實際上,特朗普再次執政之後,對人工智能領域採取「去監管」的政策,而這種「去監管」的政策會把人工智能產業發展的集中度,推到一個新的高度。

二、管控的高度集權性(highly centralized)
就是說,管控人工智能使用能力的角色是各國政府或各大公司(即平台)。由於基於互聯網之上的人工智能涉及國家間的關係,涉及兩種相關但又不同的安全問題:技術本身和技術使用的安全(safety)問題、國家間的安全(security)問題,即一個國家對另一個國家是否構成威脅的問題。
基於對安全的需要,管控的高度集權性不可避免。這也就是為什麼自互聯網產生以來人們對「互聯網主權」的討論從來沒有終止過的原因。儘管「互聯網主權」很難實現,但各國還是千方百計地來掌控互聯網,使其體現出一定程度的「主權性」。
再者,國家之間的互聯互通僅僅通過一個國家一個接口或者幾個接口的方式進行,這種關聯方式也為高度集權性創造了技術條件。此外,這種集權性也可以表現為企業形式。儘管在內部事務上,一些美國企業擁有了某種程度的對抗國家的權力,但在國際層面,無論是主動的還是被動的,企業便是國家的代理人。
三、商用者的高度壟斷性(highly monopolized)
如同前面所討論的邏輯,無論商用者是政府還是企業,都很容易趨向於高度壟斷性。從經驗看,即使使用者是個人,對於人工智能的使用也呈現出高度壟斷性質。舉例來說,無論在哪裏,今天的互聯網和社交媒體領域都被各個領域的「大V」(網紅)或者大V所構成的小團體所壟斷。這些大V及其團體往往集聚和壟斷了大部分資源,享有物質意義上和話語權意義上的不相稱的權力。他們往往被視為是各個領域的「精英」,任何東西(宗教、思想、價值觀、謊言、謠言等),一旦具有了「商用」價值(即只要有人信),他們便會趨之若鶩,毫無底線地追求流量,把某一事物的商用價值推到極端。
四、使用者高度分散性(highly diffused)
使用者高度分散性,即最底端的互聯網使用者。互聯網可以說是迄今為止最具有民主性質的技術。因為人是會說話的動物,人們必須溝通。這也就是基於互聯網之上的社交媒體今天如此普遍的一個原因。但是,這種技術的可得性也導致了個人的「原子化」。哲學家漢娜·阿倫特(Hannah Arendt)曾經對西方極權體製下的個人「原子化」做過深刻的討論。
但是,今天的情況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今天被視為高度「民主化」的互聯網技術導致了個人的極端「原子化」。在社交媒體中,人們看似透過網絡產生了互聯性,但這是虛擬的互聯,因為他們之間並沒有真正的溝通。在年輕群體中,很多人實際上已經失去了語言的溝通能力,他們之間的溝通往往發生在一個人的拇指與另一個人的拇指之間。
更為重要的是,他們往往僅僅是大V們的商用對象,大V們對他們來說具有「邪教般」或者「鴉片般」的吸引力。在行為上,他們往往表現為現代版本的「烏合之眾」,表現出從眾、非理性、輕信、自我頌揚、自我愚昧等特徵。

人工智能的治理結構特徵
人工智能高科技的這種技術結構特徵在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第二個層面的高度等級化,即治理結構的高度等級化。儘管社交媒體看似呈現出高度的扁平化,但實質上則是愈來愈等級化,一種可以稱之為「牧民社會」或者「羊圈社會」的治理結構正在快速形成和崛起。自從人類有意識地去發明和創造技術以來,一個總的趨勢是:機器愈來愈像人,而人則愈來愈像機器。因為人是根據自己的人性來塑造機器的,機器便有了最終征服和奴役人類的機會。
「牧羊社會」由三部分角色組成,即牧羊人、牧羊犬和羊群。今天,就人工智能的發展水平來說,它已經有能力扮演或者已經在扮演着牧羊犬的角色。
今天,人工智能愈來愈具有能力來扮演牧羊犬的角色,而在這個過程中,社會不可避免地成為了受害者,至少可以從三個方面來討論。
一、被取代
儘管人類已經在各個方面感受到了人工智能對社會造成的衝擊,但人工智能依然處於快速發展過程之中,並且愈來愈像人類本身。今天,人工智能要比大部分人更有效率,也更加聰明。愈來愈多的工作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就是出於這個原因。在一些國家,政府決策部門愈來愈依賴於人工智能。依賴人工智能被視為是能夠提高決策的科學性和效率。迄今,人們可以這麼說,因為人工智能已經超越社會的大部分人的思維和思想。
不過,也應當指出的是,這個大趨勢不變,那麼最終決策者的思維會被人工智能所取代。一方面,人工智能變得愈來愈聰明,另一方面決策者本身愈來愈沒有能力做任何自主的思考。
二、被殖民
「殖民」分為「內部殖民」和「外部殖民」。這是人工智能大模型的使然。「內部殖民」的發生是由高度集中的技術和高度分散的用戶這一結構所致。「外部殖民」源自人工智能的思維邏輯。
OpenAI與DeepSeek有什麼區別?大模型的運行邏輯是一樣的,只有效率和成本是不同的。但這裏必須指出一個嚴酷的事實是,今天,人工智能的大多「餵料」都是西方的。在人工智能時代,大部分國家會失去訊息的主權,因此會失去思想的「主權」和知識的「主權」。可以預見,思想思維被殖民對大部分國家來說是一個愈來愈嚴峻的問題。如果說在過去,決策者還有能力抵制和抵抗西方思想和思維,但對愈來愈依賴於人工智能的決策者來說,這種能力趨於弱化,直到最後的消失。
三、被欺騙
在人工智能時代,更為重要的發展是「DeepFake」,即深度偽造。深度偽造在取消人類文明的根基。人類文明建立在經驗事實之上。但深度偽造已經促成人類進入「後真相時代」(Post-Truth Age)。當什麼都可以深度偽造,那麼文明的根基也就動搖了。可以預見,這一趨勢會愈來愈甚。
現在的「深度偽造」是建立在人工的「餵料」之上,還可以追根溯源,但一個機器自己創造訊息的時代正在快速到來,屆時愈來愈多的自我生存的訊息變得不可追根溯源了,那個時候人類文明就會遇到大麻煩。人們可以想像,對決策者來說,一旦失去了文明根基,那麼決策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情境呢?一旦那些在人工智能領域佔據主導地位的文明和文化就會變成普世和普遍的文明和文化,那麼其他文明和文化的生存空間在哪裏呢?

從技術不平等到智力不平等
迄今,人們對人工智能所造成的不平等主要聚焦在就業、收入、技術的可得性等方面。這些不平等不僅存在,而且還會加劇,這些不平等也已經成為人類揮之不去的噩夢。不過,從目前的發展趨勢而言,人工智能及其相關工具所產生的最大也是最具有危害性的不平等是人類智慧上的不平等。這種智力上的不平等並不是由人們日常所說的「技術不可得性」造成的。
關於新興科技對社會的影響,一種普遍的觀點是,只有那些能夠得到這種高科技的社會群體才可以享受新興科技所能帶來的好處,而那些難以得到新興科技的社會群體則難以得到科技帶來的好處。但是,就人工智能及其工具對人類智力的影響來說,結局是恰恰相反的,即是說,這種高科技愈具有可得性,使用頻率愈高,使用者的智力受到的損害和傷害就愈大。
馬斯克最近說,愈是體力勞動,愈少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而愈是知識勞動,愈有可能被人工智能所取代。如果是這樣,人工智能革命和迄今為止的工業革命剛好相反,因為之前的工業革命都是把人類從體力勞動中解放出來,而人工智能革命則是把人類從智力勞動中解放出來。如果這樣,那麼,隨着人工智能的發展,人類的自我愚昧進程也必然加快。
對絕少數人來說,人工智能是智能,而對大多數人而言,是「人工智殘」(artificial ignorance)。「人工智殘」指的是一種當今愈來愈普遍的現象:在人工智能時代,由於廣泛和毫無節製地使用(無論是主動使用還是被動使用)人工智能相關的工具(尤其是基於互聯網的各種社交媒體)所導致的人類自我智力傷害。
毫無疑問,人工智能的發展一直在惡化知識界的「異化」現象。近代以來知識界一直被視為是理性的最重要的來源,但現在人工智能使得人類理性變得愈來愈遙遠不可及了。今天的知識和智慧領域出現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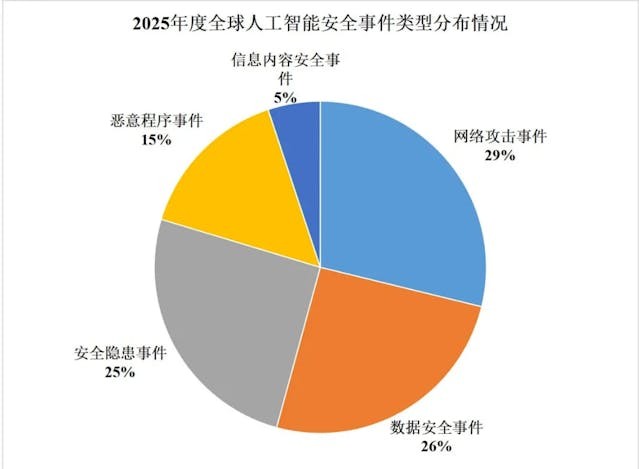
制度性風險與牧民社會
從經驗看,人工智能在快速摧毀此前保障人類生活正常進行的所有體製。這種趨勢在美國最為嚴峻,因為美國幾乎還沒有監管人工智能的有效機製。2024年9月5日《紐約時報》刊發的《對人工智能的癡迷可能導致民主的終結》指出,「隨着技術使訊息傳播變得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注意力』成了一種稀缺資源。隨之而來的對『注意力』的爭奪戰導致了有害訊息氾濫,而這一戰線正從『注意力』轉向『親密』。新的生成式人工智能不僅能生成文本、圖像和視頻,還能與我們直接交談,假裝人類」。
實際的情況可能比該文章描述得更為糟糕。在很大程度上,人工智能賦能的社交媒體已經導致美國傳統民主形式的死亡。民主是否能夠在人工智能賦能的社交媒體時代得以生存和發展是一個很大的問號。不僅僅是選舉制度,所有其他制度都經歷着嚴峻的考驗。而一旦失去這些傳統制度的保護,人類無疑將處於一個極度個體化的原子狀態。
人們可以說,舊制度的消亡是必然的。的確,任何制度必須與時俱進,否則就會消亡。人工智能已經顯示出其強大的制度毀滅能力,但人們仍未發現其制度建設能力。在新制度確立遙遙無期的情況下,個人的「原子化」趨於加快和加劇。
不難理解,當今社會的「牧民」特徵愈來愈明顯。儘管在社交媒體上,每個人都可以說話,都可以各抒己見,但就其本質而言,社交媒體已經出現個人匯總成為「會說話的羊群」的局面。人性最光輝的一面──理性逐漸消失了,而最醜陋的一面──非理性得到了張揚。這在很大程度上已經威脅到人類共同體的生存和發展。
今天,各種基於社交媒體之上的群體張揚的是階層階級之間的仇恨、民族種族之間的仇恨和國家之間的仇恨,商用民粹主義、商用愛國主義和商用民族主義情緒,深入到了社交媒體的各個角落。
更為嚴峻的是,對那些大V來說,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是「商用」,即由流量產生的利益,但對很多他們的追隨者(也就是「羊群」)來說,則是信仰、是行動。仇官、仇富、仇(不同的)宗教、仇(不同的)價值和仇外國人已經從線上轉到線下,造成了一些群體的生命危機。
〈誰「偷」走了中國的中產階級?〉四之三
原刊於「大灣區評論」微信公眾號,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