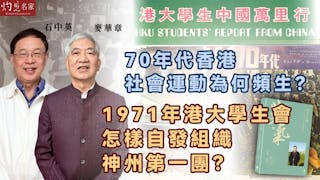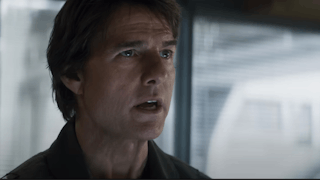正如上一篇文章所試圖梳理的,香港教育中的身份認同,始終在多重身份的張力中反覆糾纏。而這一切,在去年《港區國安法》頒布,以及高中核心科目改革、國安法教育推行等大幅度的教育變革中,可能會出現翻天覆地的變化。隨着這個「新香港」已然來臨,我們尚未知道,到底屆時的教育和身份認同培育,會變成什麼模樣。不過此時,也可讓我們回顧一下香港教育中有關身份認同的不同討論和取向。不論光譜如何、取態如何,這是一個多元紛呈、對身份認同議論百花齊放的年代。
以國民身份認同統攝身份認同教育
自回歸中國以來,對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培育已成為香港教育最核心的事務之一,而隨着近20多年的發展,對國民身份的培育更愈來愈取得主導的位置,在此不贅。
而在不少偏向保守立場的論者眼中,由於英國殖民統治時期沒有着力塑造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令面對回歸時,這一身份認同的闕如成為不得不處理的課題,因此這種發展是無可避免,甚至是應有之義。有教育學者在2000年代初便已指出,由於港英政府在1967年後,「重視『懷柔政策』,於課程不着痕跡地幕後操控,少有公然「鎮壓」,淡化年輕一代中國青年的民族意識,在一定程度上頗為成功,故回歸後在公民教育方面,須下一番不偏不倚的『撥亂返正』工夫。」(葉國洪,2002,125) 當中亦明確表示「香港推行公民教育,應該使香港市民在面對 97 前後的國民身分轉變時,能夠處於泰然、樂於接受及認同新的國民身分。」(葉國洪,2002:126),並以「公民教育/國民教育」的方式指稱身份認同的培育。
這樣的表述,其實已很接近將對身份認同培育涵攝在國民身份認同的教育中。而在前幾年面對港獨思潮的出現,亦有相近立場的論者提出,應該推行一套以國民身份培育為根本宗旨的公民教育。在這種倡議中,「公民素質可以理解為:根在中國,有強烈公民責任感,擁護『一國兩制』,認識全球、中國和香港議題和情況」(馮可強,2017),而公民教育的目的在於「引導學生認識香港與中國內地不可分割的關係、『一國兩制』和《基本法》的由來和議題,進而建立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身份認同」(馮可強,2017)在這一理解下,雖然仍有公民教育的名目,而且還有現行課程框架所納入的本地、國家、全球等不同層次的元素,但卻已有以國民身份認同去統攝整個身份認同培育的趨向。
當然,持相類立場的論者,也沒有否認香港人有其本地的身份認同,不過在他們看來,「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和「中國人」的身份認同並不是矛盾,而是前者統攝於後者,屬於一國下的本地群體認同。例如有論者便認為作為本地居民的「香港人」和作為一國公民的「中國人」的「雙重認同」,一直是主流,「香港人」與「中國人」身份相輔相成,增強港人認同感與培養國民身份並非對立」,並指出「建立鞏固的雙重認同,方為落實一國兩制的有利條件」(宋恩榮和潘學智,2017)

在這樣一種對國民身份認同培育的理解下,注重情意便成為首要的策略。有持相近觀點的教育學者便指出,「國民身份教育不單是一種知識的理解,也是一種情意的培育[…] 這被忽視了的情感在政治生活中非常重要,因為它有助加強社群中各成員的團結意識和歸屬感。」(胡少偉,2010),國內交流體驗亦因而被視為能提升學生對國民身份情意的有效方法。理工大學近期有關此類活動的調查亦顯示,不少學生在參與這些活動後,對中國內地及內地民眾有更正面的態度,且同時對「香港人」、「中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及「中華民族一員」的「身份認同強度」,均有顯著提升。這彷彿在呼應着以上論者的觀點:在國民身份認同大前提下,國民身份認同和本地認同可以是和諧並存的。
公民教育和「理性的愛國者」
有別於強調國民身份認同培育主導性的觀點,自回歸後,另一種較強調「公民教育」的名義和概念的觀點亦同樣長期存在。從抱持這種觀點的論者而言,他們固然同樣批評港英政府在殖民時期並無着意推動身份認同的培育,但他們的重點卻側重於對香港人作為本地乃至多元公民的身份培育。(謝均才和馮菀菁,2018)
根據這一理解,國民身份認同固然是公民教育中的重要元素,但只是其中一部份,「國民教育只是『多元公民教育』(簡稱為公民教育)的一個環節,絕不可以部份取代全部」,「一個『公民』,可以同時屬於不同的『政治群體』,擁有不同身份。故此,公民的概念至少涵蓋了地方公民、國家公民、區域公民和世界公民等多重身份的『多元公民』(multiple citizenship)。」(民間公民教育聯席,2013),這一理解意味着,作為身份認同培育的範疇,公民教育要培育的是包含個人、本地、國家、世界等多重層次的公民身份。根據這種多元公民身份,學校教育的目標應是「讓學生認識及瞭解其自身擁有的多重身份,雖然身處香港, 也不應只局限在兩種身份之中,反而應由此引導他們去明白和反思這種多重身份觀。」(謝均才和馮菀菁,2018)
在這種對公民教育特性和多元身份認同的理解下,知識建構和理性思考成為身份認同培育的主要取向。有抱持此一觀點的教育學者指出,國民教育是有知性和情感的雙重使命,所採用的教學法必須能滿足這雙重使命(梁恩榮,2008)。
基於多元身份培育的需要,公民教育應採取多元的教學方法,兼顧「參與式學習」、「爭議性課題」、 「批判思考」和「情意教育」四種取向,以達到同時顧及學生對身份認同的情意和理性發展。
不過這一取向所較重視的,始終是理性思考和批判的面向。有教育學者指出,在具備充分知識和理解下,才能幫助學生分辨如何愛國才是「愛得合宜」,並達到「明智的愛」,即不單愛國,同時亦體察其他更高的價值(謝均才和馮菀菁,2018)亦有學者提出公民教育的目標應該是培養學生成為「理性的愛國者」,即是能持平地及批判性地從不同角度來處理有關身份認同的議題,並能反思及討論各觀點,培育批判思考(香港社會服務聯會,2008)。這比起灌輸式或側重情意的教學方式,更切合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多元特性(梁恩榮,2008)。
在這種對公民教育的觀點下,身份認同的培育應是在重視知識建構和理性批判的前提下進行。這一觀點認同國民身份培育的重要性,「讓學生自由討論及選擇身份認同。在建構主義的教學模式下,學生透過澄清概念及價值觀,以及多角度分析的討論過程,一般也難以全盤否定中國人身分,亦能表達對傳統文化的欣賞」(陳曦彤,2020),同時亦指出國民身份培育只是香港人多元身份培育的一環。在持相類取向的論者看來,2011年的德育與國民教育科課程文件,之所以會引起爭議,正是由於他們認為這種以「國民教育」取代「公民教育」命名的做法,「完全改變此科的教育本質,收窄公民教育的應有面向」(民間公民教育聯席,2013)。

本土意識與身份認同教育
隨着近十數年的社會和政治衝突,對香港人本土意識的關注日益受到關注,乃至不少人重新審視香港人獨特的身份認同。雖然這些論者對於到底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到底是什麼、以及這種香港人身份認同與作為中國人的身份認同應處於什麼關係,當中的看法有很大差異,但他們的共同之處在於,他們都希望確認和捍衛香港的價值與獨特性(Hong Kong’s distinctiveness)(Fung 2010: 595;Yew & Kwong 2014, 1091;鄭祖邦,2019)。
不少保持這種理解的論者,都會傾向將自回歸至今的身份認同培育,都被視為威脅香港人獨特身份認同的「洗腦教育」;同時亦由於粵語和繁體字被視為香港人獨特身份認同的重要構成元素,因此近年在不少學校推行的「普教中」也被認為是對粵語乃至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蠶食。亦有台灣學者指出,在這種對香港身份認同的意識下,更主要的是在中港互動日趨頻繁和普遍下,如何保持香港人獨特的身份認同和有別於中國內地之處(鄭祖邦,2019)。
當然,到底什麼是本土意識?本土意識在身份認同培育中又有何意義?近年來確實是人言人殊。在有人提倡香港人獨特的身份認同的同時,亦有論者對本土意識提出不一樣的看法。例如有論者針對本地的語文教育,指出「語文,作為工具,實不應標榜『本土』元素[…] 該以如何培養學生的語文能力,而不是以『民粹』作招徠」,而所謂在語文教育上加入本土元素,並不是只重視繁體字,而是要納入和香港本地群體文化和生活有關的素材 (梁振威,2016)。
此外,有認同國民身份認同培育主導性的教育學者,亦認為本土意識和國民身份培育並不必然矛盾,「在推行國民身份教育時,不能只講認同國家和世界層次的內容,也需同時留意香港社會的本土特色;[…]在國家的憲法和香港的《基本法》中,香港的土地雖然是國家的一部份,但香港公民的權責在基本法中與內地憲法內公民權責是有些分別的。因此,在香港學校推行國民身份教育時,不能輕視讓學生理解本土特色的重要性。」在其看來,香港人的獨特身份認同,以及本土意識,不會也不該與國民身份培育相衝突。以上所述,均顯出,對於本土意識乃至香港人獨特身份認同在身份培育上的角色,確是呈現分殊的看法。
結語
香港人的身份認同從來不是非黑即白、「自古以來」的,而是外向型、複合型,且多元複雜的。這從本文所回顧對於身份認同培育的不同光譜和取向中,可見一斑。而這些圍繞身份認同培育,紛陳駁雜的觀點和討論,也足證香港教育乃至社會的自由和開放性格。到底在「新香港」下,這些觀點和討論會否繼續延續下去?還是會定於一尊呢?這對於往後香港的身份認同培育,又會有怎樣的影響?這無疑是值得我們細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