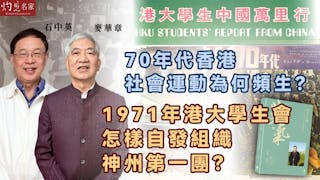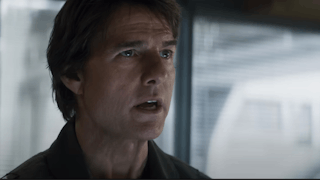尋花問柳?竟是少女葉曉文的所為。讀她那部《尋花——香港原生植物手札》,可以充分想像,她如何為了尋覓野花而瘋狂地忘我;拗路墩,橫水澗,赤足涉水,攀爬絶嶺。在她筆下,尋花之路殊不簡單,有時走到腿膝痠軟無力,有時狂風把髮變成一杆地拖,有時以沉重的步伐踏破顛簸的浮橋;有時迷惑走錯路,有時直闖禁區,只為了看最一棵老鼠簕,或者,一無所獲,多走一會,忽然以為在做夢似的出現珍稀綬草。作者花那麼多氣力和精銳的年輕歲月,然後寫一部不足300頁的小書,無非想向世界說明一個重要的本土事實:香港就算連郊野也能全球珍貴而稀罕的原生花種,誰個冒失政客貪方便割郊區以自肥,肯定有機會把一些列入瀕危的絶跡花草趕入窮巷。
像僅只在香港有記錄的「香港茶」,作者也做了一番查證功夫:第一次有人發現本土茶屬植物在太平山,全港僅得三株,當時是1849年,剛割讓港島,原來要經過育苗,才可以遍植盧吉道和薄扶林。可是,它跟其他地方的紅茶花有何不同?那些科普特性,甚麼雙子葉,山茶科,甚麼樹形較窄,花瓣多少片……不知道作者查看過多少本植物圖鑑之類的專書,才知曉葉生出來的形態分類,互生、對生、輸生、叢生、覆瓦狀,若沒有作者繪畫的圖畫說明,根本永遠不能望文生義。由第一頁開始,葉緣、花序、果實,頂生抑或腋生,儼如生物學老師。鐘形抑或羽狀,傘房花序抑或隱頭花序,圖文並茂,天啊,更量着直徑多少厘米,幸好見好就收。
不過,作者似乎刻意交出專科名稱,挑戰讀者,彷彿叫大家迫視香港很多獨有的事物,需要專業需要學識需要誠意。我們所謂領袖賢達、名人政客,可能一概不知詳情。例如大部分香港人只知洋紫荊乃常見喬木,在1965年定為香港市花,通用硬幣一枚一朵。讀書才知它榮任市花85年前,一名法國神父首次發現,最不為人知的,是那株不結種子的羊蹄甲,用插枝法移植到薄扶林道一帶的修道院,才開枝散葉。香港電視製作的《惡毒老人同盟》,以黑色幽默諷刺社會所產生的老人問題。片中白彪飾演過氣武打名星,因演宫粉羊蹄甲大人而意外爆紅。原來我們的市花是宫粉羊蹄甲與紅花羊蹄甲的混血兒,雜種生來而艷麗,不結果子。這個無可無不可的「騎呢」角色,饒有所指。現在經作者這麼一提,洋紫荊的身世跟香港便彷彿遙相呼應了!

文字可人 勝台灣同類書
書中每一種野花只佔一頁,不多,科普陳述只有一少段。大多寫一種另類的尋幽探秘。在午後安靜的三門仔發現海邊開得燦爛的黃槿,作者這樣寫:「幾所村屋靜靜躺卧海邊午睡」,「那裏的水龍頭不知為何總關不牢,水淌下來,落在下面的粗麻繩上,一大束嫩綠的小葉子便笑着探出頭來」。寫聲音寫色彩,結合動態,讀者像跟着作者做田野考察,或像尋找失散的情人,偶爾在野外邂逅,直悟成風景。於是,說是尋花札記,不如視之為結合科學和文學的記敍小品。作者引王維的「夕雨紅榴拆,新秋綠竽肥」,若以為所講的,是竽頭泛綠吃了會中毒便笑壞人了,原來是海竽,香港也有原生種,到了秋天便長得肥大翠綠。讀下去又猶如文學百科,武俠小說裏的蒙汗藥何來,韋小寶餵飼馬匹讓馬拉一夜稀泥巴臭臭的巴豆,用來製藥油給頭暈的婆婆擦頭的白花油草、涼茶鋪所用田灌草等等,原來都可以有原生在香港野地的物種。
台灣也有類似的出版,叫《原來野花這麼美》,出版於今年2月,出版比《尋花》後半年,是否「抄橋」不得而知,但體例太似了,也是以季節分輯,也是收集當地野花花種介紹植物科名及特點,可是欠的,就是文學筆法,還有拍攝粗糙。葉曉文卻每種花草細加繪描,圖文皆出自她一人手筆。一花一草一字一圖,皆出於作者這名香港郊野這秘密花園的主人,清清楚楚指出哪裏收藏珍品。論數量,香港的野生原生植物不夠台灣多,但論書,葉則更勝一籌。尤其是當作者痛心逾千曾屬於本土特產土沉香遭亂斬,任人霸佔,顯得無計可施;讀者不能再抗拒細讀書後枯燥的法例:「仼何人無合法辯解,不得售賣、要約售賣、管有、保管或控制在香港法例第96章規例下的植物」。看到嗎?魔鬼在細節裏,法例沒直接提及不得砍伐植物的一部分。
此情此景,猶如香港人共同擁有的郊野遭覬覦,沒有詢問情由,法例沒規定不得砍伐植物來建造豪宅。愛花人的秘密花園如果變成富賈劃地割據的私家花園,本土野花,還有生存空間嗎?唉!花猶如此,人何以堪?書中序言那一小段的批判,暗示為甚麼我們逐漸失掉旅遊景點,到底我們的郊野公園還有甚麼別家所無的價值。作者說:興建港珠澳大橋、更改綠化地帶土地用途、東北發展計劃等,令至少需要半世紀長成的次生林頃刻摧毀,我們還有沒有全球唯一的頻危野花品種可存?
幸好,忽然,有人又驚喜發現,清冷水邊綻放可愛小黃花,連中國也列為極危物種的香港報春,帶着「青春的快樂和悲傷」的花語,暗暗抓住傾斜得幾乎垂直的泥坡,泰然昂首地盛開。
(原刊於《本土新聞》,作者稍作修改後於本站發表。)
封面圖片:網上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