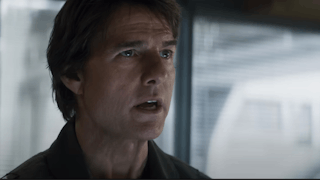電影《奧本海默》賣座不如《芭比》。今年暑假的西方年輕觀眾,流行將兩齣戲一日之內看完,興起所謂的Barbenheimer電影娛樂風潮。
但這兩部電影,無論主題內容和風格,像一對同床異夢的男女,其實無法連線結成一對。
《奧本海默》不是介紹這位猶太核子物理學家研製原子彈的經過,而是有另一層政治和時代的含意。新一代的觀眾,不太理解何謂麥卡錫主義,也不知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政府恐懼蘇聯盜竊原子彈機密,對物理學家掀起嚴格的審查與防範,還禍及荷里活的電影工會。
年輕一代觀眾對於戲中總統杜魯門會見奧本海默的那場戲,導演的反諷在哪裏,恐怕很難體會。
奧本海默的時代背景和心理精神
主角奧本海默在他的戲劇處境裏,戲中鏡頭和對白曾掠過一系列名字:史特拉汶斯基、長詩《荒原》、畢加索的立體派繪畫,這些文藝作品,不但構成那個時代的背景,而且還成為主角心理精神的象徵。
例如,為什麼片中出現畢加索的立體派繪畫?這是導演暗示奧本海默的人物性格,背離傳統,尤其對左翼的社會主義發生興趣,如畢加索顛覆繪畫傳統一樣,都是離經叛道的創新人物。
而艾略特的《荒原》,出現在銀幕上,是一首著名的長詩,描寫世紀末工業革命為知識分子的文化心靈帶來的巨大震撼。 這些文藝作品典故,呈現在電影的開頭,並非一般的name-dropping。導演基斯杜化路蘭是倫敦大學學院英語文學系的畢業生,在此片中大展身手,將自己的文學知識與歷史和電影結合。
20年代,英美和歐洲的文學藝術都在震撼和衝擊中湧現新的作品。英國作家赫胥黎的《美麗新世界》,一樣警告科技為人類心靈帶來的破壞。雷馬克的《西線無戰事》更記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戰壕和坦克的軍事科技的恐怖、戰爭的殘酷。還有小說家湯馬士曼的《魔山》,刻劃情感的虛偽與墮落、社會價值顛倒之下的心理意識流。
愛爾蘭小說家喬伊斯的《尤利西斯》,將小說的敘事手法徹底打破,着力描繪心理分析和意識流。經濟大恐慌和蕭條,令文藝和藝術陷入貧窮和戰爭的威脅陰影。文學家認為:創作應該有驗證的目的,要譴責社會的不公義。美國作家史坦貝克描寫經濟蕭條時代,美國基層工農的苦難生活。
這一切都對那時候的原子物理學家有深遠的影響。文科天才和科學家連成一線,形成對社會不義的同情。政治家不獲信任,所以杜魯門在片中的形象類似小丑。
《奧本海默》中蘊含的人道主義
《奧本海默》不但是一部大電影,導演的野心是想將電影的敘事結構和拍攝手法還原到90年代、美國知識份子獨立製作興盛的時期。不止如此,諾蘭要在銀幕呈現的,是人道主義的召喚。其中當局對共產黨間諜的提防、對核戰的準備,這部戲在今日全球,特別是西方國家上映,面對中國、俄羅斯、台海、烏克蘭,有非常深刻的警世意義。
但如果只視之為一部見識原子彈如何在IMAX銀幕大爆炸視覺效果的爆谷電影,就好像當年看《色戒》,只看見片中的梁朝偉三場床上戲,不見其餘。
與《芭比》同看,只會將《奧本海默》這一部淡化。《奧本海默》是嚴肅的、幽暗的、沉重的,不只是一道主菜,而且是一桌聖餐。《芭比》只是一道粉紅色的甜品。
對於知識分子:有如在教堂裏,不可聽完牧師講道之後,在後室看脫衣舞。不是不可以看,而是要走出教堂,拜託,過兩三天可以嗎?
原刊於CUP媒體,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