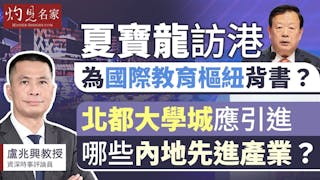2022年香港文化博物館的「敦煌──千載情緣的故事」應該是現階段最後一次敦煌文物在香港的展覽。
敦煌歷史 多元深度
自1944年敦煌研究院成立,到2014年的60年間,敦煌應該未在香港展覽過。不過,敦煌這名字對一些香港人來說並不陌生。1979年中國一開放,絲路旅行就成為一陣熱潮,愛藝術或愛旅行的人,又怎能抵抗絲路上最大藝術寶庫的誘惑呢?可是能親自去敦煌的人數始終有限,所以2014至2022年3次香港博物館的展覽,應該是很好的機會讓更多香港人不光知道了敦煌,而且了解了敦煌。
2014年第一次展覽「敦煌──說不完的故事」效果很震撼,我另文曾提過敦煌樊院長即電副院長來看,而觀眾亦多好評。第一次展覽能有這效果,除了康文署博物館中人將士用命、手法純熟之外,還有獨特優勢:既然60年來從未展過,那麼只要夠大型,精銳多出,那是很難不震撼的。如何做第二第三次,才真正考功夫,而第二次是關鍵,因為它會影響第三次的路向。
跟敦煌研究院簽約做3次展覽我是贊成的,因為敦煌有足夠的深度。然而正因為很有深度,所以不可能即食處理。記得我們編敦煌全集時,出版前去了兩三次敦煌,光是開大會開小會聽作者們各自講所研究的範圍,以及爭論某些畫面的歸屬,已經聽得我暈頭轉向。再由各卷的作者領到洞裏看畫面,就更是頭腦爆炸。曾經早上看了第148窟,下午又由另一作者領去重看,看到的竟然是全然不同的畫面,這一切還未包括藏經洞文書和繪畫,未包括當時剛發掘的北區洞窟,未包括壁畫不多的洞──原來那些洞裏也有很多故事。

人員輪換 歇澤而漁
正由於敦煌多元多方向,想引領香港觀眾逐步深入敦煌,理應一開始就做全盤規劃,想定每次展覽的主題。
可惜這不是香港政府的習慣方法!
為了培養通才,香港政府的文博機構採用人員輪換的方法,而且不會因事制宜。因此3次負責敦煌展覽的館長都不同,處理內容的隊伍也不同,這做成每次都歇澤而漁的狀況。至於下次還有沒有魚,已經不及想了,因為每次近兩年的籌展時間裏,臨時受命的隊伍要大約摸一下澤裏有什麼魚,已經花盡了時間和精力。
第二次展覽是「數碼敦煌──天上人間的故事」。除了「數碼」兩個字,還有什麼方向?其實從第二次已經可以猜想第三次展覽將要進入死胡同。
第三次展覽可以怎麼辦?壁畫被數碼取代了,藏經洞的東西絕多去了外國,立體文物不是敦煌的強項,複製洞窟已經展過兩次。今次的「敦煌──千載情緣的故事」於是來一次「數碼敦煌」+「敦煌拼貼裝置藝術」,集中在展覽手段上顯手身:北朝洞窟形制的裝置裏放入唐宋的文物,早期西域式龕楣髹上盛唐148窟的綠色;沉浸式Art-tech裝置看山水畫和講孝道的「父母恩重經變」絹畫,拼貼式數碼過道鋪滿民俗畫和供養人;還有巨大的九色鹿打卡位裝置等等。
憑着政府博物館人員的專業展覽水平,對敦煌了解不多的觀眾還算滿意,而我就充滿了同情的敬意。
沉浸式展示的好壞
在Art-tech新潮下,沉浸式成了「必須有」,恰巧我跟1990年代初一起做電子出版的朋友去看這次敦煌展覽。看5號館那「父母恩重經變」為主的大型數碼展館,她視之為裝置藝術。為什麼呢?因為它無助觀眾了解文物本身;那些從文物中勾出的人物在走路,對觀眾有什麼重要意義呢?相對於另外兩個展出文物的展館,5號館顯得面積過大,不成比例。一語中的!做了30年數碼出版的朋友畢竟看過數碼世界無數潮起潮落。

這3次敦煌展覽裏有一個數碼展示既有新意,又有意義,那是第二次展覽所做的數碼虛擬洞窟。它採用不全面復原第254窟的方法,只做出中心柱和塑像,而在牆上、塑像上投射要留意的圖案和說明。當投射到南壁頂上菩薩小像的兩蛇相銜瓔珞時,我禁不住擊節讚賞,這個參觀者常會忽略的重要細節,終於因這個展示方式,得以突顯出來。

現時大館有皮皮樂迪.里思特(Pipilotti Rist)的空間錄像藝術,北角K11在做Arte M的「超越時空的永恆自然」,風向所趨,這類被動沉浸式展示肯定要淹蓋觀眾主動式的沉浸(面對一件藝術品,出神靜看,不是沉浸嗎)。如果我們沒法不跟潮流,政府的博物館何不專門闢一個展廳長期做各種Art-tech沉浸,省去經常轉換裝置的鉅額費用呢?

這同時能為付不起百多元參觀費的弱勢人士提供較便宜的數碼沉浸體驗機會,也是拉近貧富知識差距的方法。我相信無論香港題材、敦煌、故宮,以至香港藏藝術品,都值得Art-tech沉浸一番,再藉這機會深入培養香港Art-tech敏銳度。在元宇宙說得震天價響的「夢幻天視」時代,或許仍是值得一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