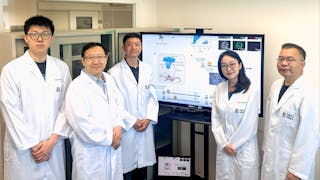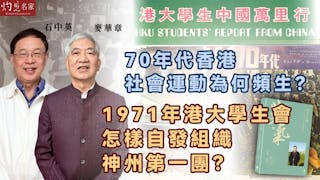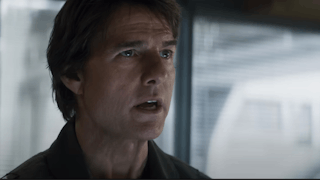本文另兩位作者:
杜啟泓,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傳染病及微生物科醫生,專研流感病毒。
龍振邦,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傳染病及微生物科醫生,專研小兒科傳染病。愛憶舊懷古,以史為鑑。
皇后大道是港英政府於1841至42年間以移山填海的方法建成的人工大馬路,對開便是維多利亞港。當時的皇后大道非常繁榮,大道兩旁盡是二、三層高的商店,有中式的白牆青瓦,二樓粵派騎樓之上,有簷篷遮蔭擋雨,中式店舖之間,不時夾雜維多利亞式的建築,精緻的雕花圓柱,圓拱迴廊延伸開去的二樓陽台,每個細節皆流露着英式典雅高貴的氣派。白文信爵士(Sir Patrick Manson, 1844-1922)1883 年來到香港,並在這裏開設診所。
從皇后大道轉入威靈頓街一路向上走,便會見到鴨巴甸街。那裏雖然比皇后大道窄,但民居商店同樣林立,主婦在街上洗滌衣服,有三五老人坐在屋簷下閒聊,中間穿插着追逐的小孩,不時飄來陣陣炒菜幽香,筷子敲打瓷碗獨特的聲音,對洋人來說更是新奇無比。
白文信開設診所不久,便與何啟爵士一起籌辦雅麗氏利濟醫院(Alice Memorial Hospital),它位於鴨巴甸街與荷里活道交界。白爵士處事認真,事必躬身,既要主理診所,又要兼顧醫院事務,公務繁忙下,打算聘請助手,助他管理診所日常事務,並為日後回英作好準備;白文信於是致函英國友人莊明寶醫生(Dr. John Mitchell Bruce),希望他能夠覓得一位有心的賢醫,條件為匿名招聘,也不公開工作地點和白文信之名。
一生最重要的決定
康德黎(Sir James Cantlie 1851-1926)生於蘇格蘭鴨巴甸班芙郡(Banffshire, Aberdeen, Scotland),15歲(1866 年)以優異成績考入鴨巴甸大學(Aberdeen University)修讀文科。
他藍眼棕髮,方面大耳,臉頰滿布雀班;個子不算高大的他,身材健碩,橫肩闊胸,總予人好動和充滿活力的感覺,加上他為人和善熱心,甫入大學不久便交上很多朋友,其中一位較友好的是比他年長數年的醫科學長莊明寶。
受到學長的影響,康德黎畢業後繼續攻讀醫科,1873 年以優異成績畢業於鴨巴甸大學醫學院。完成醫科學位後,他往倫敦找學長莊明寶;剛走進莊明寶入住的旅館後,莊便熱情款待並恭賀康德黎:「查靈十字醫院(Charing Cross Hospital)已決定聘請汝為解剖示範員(demonstrator of anatomy)!」
1877 年,康德黎考獲外科院士資格並擢升為駐院助理外科醫生。
1883年,埃及亞歷山大港爆發大型霍亂(Cholera epidemic),當時只有32歲的康德黎雖然剛與龐美寶(Mabel Barclay Brown, 1860-1921, 即日後的康太太)訂婚,但他憑着無私的心和無比的勇氣,自告奮勇前往疫區參與救援;龐美寶非但沒有阻止未婚夫,反而全力支持和鼓勵他,還囑咐他一定要完成任務,然後平安返英。
是次公幹,年輕的康德黎有幸認識到微生物學界的翹楚鍾麥基爵士(Sir Thomas Jones Mackie),他還第一次接觸到熱帶傳染病,以及踏足遠東的國度。經歷是次旅程,康德黎已給神秘的東方深深吸引;1887 年,他作出畢生最重要的決定,而這決定,也大大改變了中國的未來,令她也走上改革之路。
一次隱名的招聘
長期參與急救工作、接觸貧苦大眾的康德黎,發現倫敦人的體格普遍較差,於是開始發掘箇中原因。他得出的結論是,環境污染、衞生惡劣、空氣污濁均有損健康。1885 年,康德黎在倫敦柏斯衞生博物館(Parkes Museum of Hygiene) 公開演說,題為〈墮落的倫敦〉(Degeneration amongst Londoners)。
雖然時間已證明康德黎是個極有遠見的人,但在當時老一輩的醫生和輿論眼中,這個年輕的蘇格蘭醫生只是杞人憂天,譁眾取寵,後來還招致各方口誅筆伐,最後演變為報章罵戰。
事件雖然沒有影響康德黎晉升為高級外科醫生,但已足夠令年少氣盛、心高氣傲的他萌生去意。1886 年聖誕期間,莊明寶收到白文信來信,盼莊氏能為他尋找賢醫一名,助他管理醫務所。
康德黎一家當時正暫居莊明寶家中,莊明寶問他可有合適人選推薦;康德黎不知那是白文信的委託,經過一番討論後,苦無結論。
最後康德黎說: 「聘者若為香江白文信或埃及鍾麥基,吾欲親赴。余往埃及公幹之時,曾有緣與鍾爵共平霍亂之疫;白君則只聞其名而未嘗與之共事也,但聞其事迹足使余傾慕已久而欲效之犬馬。」莊明寶第二天發電報往香港,白文信則欣然接納。
經過17年努力,康德黎始能晉升至高級外科醫生一職,但千篇一律的倫敦生活,未能令康德黎提起勁來;他內心一直醞釀強烈的冒險慾望,年輕時前往埃及的經歷,使他覺得遠東之地乃冒險不二之選。在命運和緣分的驅使下,他於1887 年初夏乘火輪船離開倫敦,前往生命的下一站——到香港行醫。
在港生活非常充實
1887 年的仲夏,康德黎終於抵達香港。澄明清澈的海水,倒映着蔚藍的晴天,盪漾的碧水,閃耀着奪目的金光,遠眺前方薄霧籠罩的海岸線,驟見矇矓的山巒起伏,比起濃霧深鎖的蘇格蘭山頭,香港洋溢着神秘的東方色彩,實在別有一番風味。
清末的香港始見繁象,在維多利亞港停泊了舢舨和歐洲商船,又不時見到香港舊式雙帆帆船駛過,蒸氣小輪穿越港澳廣州,整片海港好不繁盛。雖然香港的盛夏比歐洲炎熱得多,但百多年前的香港沒有參天高樓的阻隔,故岸邊不時吹來透心涼的海風;和風沾衣,鹹香盈腔,7 月之時更經常下雨,雨水洗滌過後的香港更見清澈涼快。
白文信為人嚴肅認真,不苟言笑,但威嚴背後卻是外冷內熱,和善而且毫無架子。康德黎為人幽默灰諧,平易近人,待人熱心友善,常常為大家帶來輕鬆歡樂的氣氛。兩人一冷一熱,亦師亦友,成為好拍檔。康德黎初到港時,生活雖不富裕,但每天過得非常充實。
就傳染病而言,年輕的康德黎乃門外漢一名,這一科在當時仍未完全成熟,也沒有什麼熱帶醫學教科書(一直到1898 年才有第一本熱帶醫學教科書——Tropical Diseases: A Manual of the diseases of Warm Climates,作者正是白文信),故此康德黎的熱帶醫學和傳染病知識,差不多全部來自白文信和病人身上。在白文信指導之下,康德黎對傳染病有更深厚的認識;而他在外科手術方面的專長又替白文信處理很多外科病人,大大的減輕了白文信的工作量,使他有更多時間處理醫院和籌辦西醫書院的工作。
太太變成「細菌獵人」
康德黎一家到港後住在山頂,在未有纜車之前,一般的洋人大班皆以轎(山兜)代步,但好動的康德黎卻喜歡步行上山落山,沿途也會探望他的病人。到康德黎逐漸掌握熱帶醫學之後,便在家中另闢一隅作實驗室,下班後,帶同標本回家做細菌培植;康太太則為丈夫預備種菌用的培養液,以及處理培養出來的細菌。在白文信和康德黎的薰陶下,康太太成為一位熱心的「細菌獵人」。
當時大部分中國人皆活在貧窮和疾病之中,擠迫的居住環境,加上惡劣的衞生令腸熱病(Enteric fever)、痢疾(dysentery)和肺癆病非常流行;潮濕溫暖的天氣,有利蟲媒播病,如瘧疾、登革熱、黃熱病和黑死病(鼠疫)等。
基於文化差異和愚昧迷信,一般華人多不接受西方醫學。無論港英政府怎樣努力,基督教傳教士怎樣游說,華人每當生病,只會找中醫;就算明知生命快要完結之時,也寧願在家等死,也不願到西醫院看病;港英政府最後也得順應華人意願,於1872 年在上環普仁街興建第一所中醫院東華醫院。
此舉雖然讓更多的貧苦華人得到中醫治療,但華人如果繼續不信任西方科學和醫學,整體社會的衞生和健康根本無法進步。如何釋除華人的疑慮和打破隔膜?倫敦傳道會(London Missionary Society )楊威廉醫生(Dr. William Yong )先在太平山下開設專為華人服務的那打素門診和藥房(Nethersole Dispensary)。
出乎意料之外,這家門診很受中國人歡迎,於是到了1884 年,傳道會決定興建一所全新的西醫院。當時的何啟爵士從英國回港不久,其妻雅麗氏不幸因傷寒逝世,為紀念亡妻,雅麗氏利濟醫院於1887 年2 月正式落成啟用,成為第一所專為華人服務的西醫院。
雅麗氏利濟醫院成立後極受香港華人歡迎,求醫者眾,故院內極為擠迫,所以後來先與那打素醫院合併,之後再與何妙齡醫院合併,成為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醫院;其後由港島西區遷往東區,成為今天的東區尤德夫人那打素醫院。不過,西洋醫學若要更為普及、要更廣受華人市民接納,最直接的方法,莫過於培訓華人西醫!
康德黎創先河
每當市民遇有急性創傷之時,需要聖約翰或紅十字會救傷隊的急救服務,可曾問過,誰為他們編寫急救手冊?又或有肝衰竭而須作右葉活肝移植的病人,可會知道是誰確立左右肝葉的分界線,因而令這項手術更為安全?兩者的答案,正是香港華人西醫書院(香港大學前身)第二任教務長(院長)康德黎爵士。
(西醫書院教務長康德黎.三之一.待續)
原文刊於《信報》,文章與圖片獲作者授權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