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庚戌子按照金庸在該篇後記論及的思考方式,又破解了一個本來毫不起眼,也可能因而從來未有研究者深入分析過的事物──西瓜。

《婦人集》為陳維崧所撰,記明末清初數十奇女子生平軼事,李香君為其中一則。其所謂「與陳處士小札」云云,頗值一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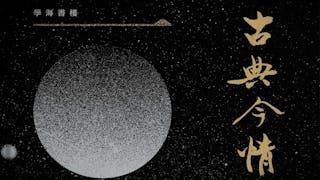
學海書樓始創於幾位積學之士的崇高理念與坐言起行,在百載變遷之中,逐漸與香港公共圖書館、教育界、藝文界結合成學術文化的共同體。

能敬重和欣賞別人,才能增進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原來十分重要。

寒鴻夜雨,誰曉蘭心語,霜染青絲飄幾許,回首紅妝院宇。

在金庸數百萬言計的著述中,寫及親兄弟的也實在太少。而那些兄弟友愛,同步同心的親兄弟,卻又是難以結交,沒有知心朋友的人。

創辦於四十四年前的「油中」,自創立之日起,便定位為人文社科專門店,當中尤以文史哲書籍品類最為齊全。在「油中」遇見「似曾相識的香港」,秋夜有書香盈袖,便是香港書業邂逅香江文化的一道亮麗風景線吧。

日下春䌓楊柳色,滿城澹湯惹蘭薰。 庭園寂寂階前月,彼岸遙遙夢裏音。

Beckett的《等待果陀》,說的可就是一個「沒有結果的等待」故事。這與挪威作家喬恩·弗斯筆下的女主角等待奇蹟出現,一去不返的丈夫,或許仍會回來。

「明月幾時有?」我們沒有忘記900年前的蘇軾,經典的文學作品有着抗衰老的特異功能,在中秋佳節思念親人之際,〈水調歌頭〉必然載譽而來。蘇軾、蘇轍的兄弟之情,將會一直感動人心,淪肌浹髓。

大俠逝世五周年之際,一場名為「從金庸小說到金庸文化」的展覽正在尖沙咀鬧市一間書店舉行。意猶未盡的「金迷」朋友,大可以來一場書中漫遊,在風起雲湧的武俠世界之外,再下一城,探索變幻無窮的金庸世界。

2023年10月8日,適值「寒露」節氣,颱風「小犬」掠過香江,國際風雲撲面,唯以述懷之作,應對窗外咆哮。

金庸寫人性的透徹,人生的際遇,都能深入人心,使人掩卷浩歎,樂於追讀之餘,啟迪神思,拓展更遼闊的思想領域。人性是永恆的,不會因時代而大有改變;反而有因環境而改變的共通性。

1977年1月,董橋在《明報月刊》第133期寫了一篇〈訪書小錄〉,講述他在倫敦逛舊書市的喜悅。董橋筆下的倫敦舊書店老頭閒話書事的情景,今天仍然可以在香港找到疑似的影像。

一片青雲入夢來,微廊秀閣為之開。

張謙宜好談藝,《詩談》一卷,論「和平」、「天趣」、「布置」等,皆有見地,卷三所謂「莫吃一家飯」,舉「蜂之釀蜜,豈止一花」為例,言為學需「兼採」為上。

今年64歲的福瑟,1959年出生於挪威海于格松(Haugesund),以挪威新諾斯克語創作大量作品,涵蓋戲劇、小說、詩集、散文、兒童讀物和翻譯,他將獲得1100萬瑞典克朗(折合約100萬美元)獎金。

雲聚嶺南和風岸,灣前碧水月流華。

以長篇小說《家變》享譽台灣文壇的作家王文興逝世,享年84歲。

孔子嚮往周初社會之美好、民風之淳厚,希望重建禮制,使天下歸仁,恢復文武周公之治。但他「既不得位,無以行勸懲黜陟之政」。

然而,古詩是有格律的,若然讀錯了這些字音,整首詩不僅喪失音律之美,而且詩的內涵也隨之改變。唯有按照詩歌的格律來吟詠,方能真切理解詩歌的情意。

傅山哭子之時,尚未悟「父為子綱」之毒,愚忠誤子,傅山當難辭此咎。

分亦難,聚亦難,衣帶汍瀾向故園,月還人未還。

黃之生平最為人所稱道者在學屈子,年近七旬,三次涉江,皆被救起,乃絕食五日而亡。

西西最後一首詩《疲乏》,對生命有了新的體會。人來到某個時刻,再也走不動了。眼、耳都累了,腦袋也疲乏了:「千千萬個問號/是非對錯,一直如影隨形/撕裂着你我的神經」。腦袋,一如眼、耳,都想休息了。

夕陽西去,遠望山如玉。夜珠千滴荷葉綠,半盞清茶一敘。

這首詩在講什麼呢?它其實是截取了人生的一個斷面,描述了一次偶然的相遇,展示了人生的一種常態──缺失和遺憾。我在無意中邂逅了你,我在無意中錯過了你。

杜茶村於詩專學少陵,實為明清之際最得少陵神韻者。於詩自有分教。

詩詞和音樂最能觸動人心,也最能安撫人心,比如說,「向晚意不適」時,如果沒有古原可登,最佳的排遣方式,便是找出一本喜歡的中文書來看,你所經過的失落,古人都經歷過,而他描述的比你還深,看了有知音的感覺。

貪走鷺門銀杏路,流霞兩袂步斜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