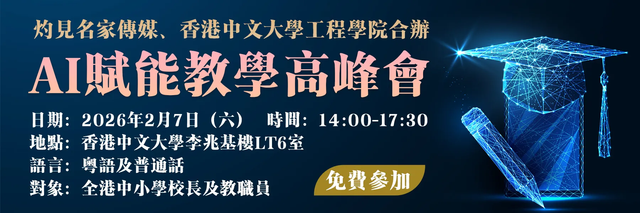11月初,雪來得猝不及防。
我穿着單薄的外衣踏出山西大同南站,風裏夾着大片濕雪迎面砸下,冰涼順着衣領往裏鑽,冷意瞬間貼上皮膚,身體不由自主地縮了起來。站口聚集了一群的士司機,看見我拖着行李箱,紛紛圍上前:「哎!閨女,坐車呀不?」濃濃的山西口音帶着拐彎般的腔調,像唱歌一樣,也大概能聽明白。他們蜂擁而至,我連連擺手說不用,從人群中擠出來,快步走向租車公司。

鑽進車廂,坐上駕駛座,關起車門,我把暖氣開到最大,玻璃很快蒙上了一層霧。身體漸漸鬆了下來,感覺像是重新活了過來。這趟從大同出發,沿途穿過山西、河南,一路往南,最後在陝西西安還車的自駕之旅,就這樣在風雪中開場。想到未來1000多公里的路途,將跨越三省,心裏止不住的雀躍,卻不知道等待我的,卻是一場多麼驚險的旅程。
山西人的驕傲
從華嚴寺往西約15公里,武州山的南麓,有一個龐大的窟群,那就是中國四大石窟之一的雲岡石窟。我沿着339省道走,半小時車程就到達停車場。此時雪已漸停,化成細細的冷雨,地面濕滑,遊客疏疏落落。零度出頭的氣溫,我在原地跺了兩下腳,對着手心呵了一口白氣,暗自給自己打氣:這些石窟在這裏等待了將近1600年,自己再冷也該去一睹尊容。

售票員建議我坐電瓶車:「走過去得20分鐘呢。」看了一眼遠處灰濛濛的天,再看一眼自己單薄的外套,毫不猶豫點頭。
雲岡石窟與平遙古城和五台山同列為世界文化遺產,都是山西人的驕傲。北魏時期的都城──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大同,曾是這一切的起點。這個由拓跋鮮卑建立的政權,在興安二年到太和十九年之間(453-495年),開鑿了雲岡的主要洞窟。如今整個石窟群保留了大小窟龕254個,造像近6萬尊,從露天巨佛到指尖大小的小像,規模令人驚嘆。

踏上石階,第一眼看到的是長達一公里的崖面,被一個個洞口鑿得像蜂巢。走近了,佛像的面容、飛天的衣帶、藻井的紋樣一層層浮現出來:有的佛低眉含笑,慈和恬靜;有的身形健碩,肩膀寬得幾乎撐滿整個洞口;有的風姿綽約,或拈花微笑,或閉目傾聽;還有的細小如手指節,密密匝匝刻滿整面石壁,對於密集恐懼的我,不敢多看。走到第五、六窟時,視線幾乎無處可落。洞室四壁與中央石柱滿是浮雕,從佛主誕生、成長、婚姻,到出家、成道、弘法,這些故事圖雕其實就是一長篇連環畫。

為何佛教在中國盛行?
走着走着,心裏忍不住泛起疑問:為什麼在南北朝這樣一個戰亂頻仍的時代,佛教在中國會如此盛行?
佛教起源於印度,東漢時由西域傳入中原,那時不過是一種新奇的外來信仰,遠遠談不上普及。真正的轉折,發生在東漢末年以後。連綿不斷的戰事使生靈塗炭,中原滿目瘡痍。無數的家庭被摧毀,無數的生命在戰亂中消散。面對這樣的現實,講究禮法秩序的儒學很難安撫那些破碎的心靈。於是,一個談因果、說輪迴、倡導「離苦得樂」的佛教在中國發展了起來。可以說,南北朝佛教的興盛是時代的產物,杜牧筆下的「南朝四百八十寺」想來並未誇大。
統治者比誰都明白這一點,所以北魏政權亦希望透過佛教來凝聚人心,乃至後來雖然發生過滅佛的風潮,但始終沒有真正斷絕。雲岡石窟的開鑿一直延續了近百年,前後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每個階段都有其獨特的藝術風格與文化特徵。

最早期的「曇曜五窟」(第16至20窟)多為露天或近露天的大像,佛身較為健碩,五官立體,服飾的褶皺細緻可見,有古印度氣息。站在這些佛像面前,很難不被那粗獷壯闊,氣勢磅礴的胡風所感染。
之後孝文帝時期的石窟風格開始改變,記得我在中學的歷史課本裏有念過,孝文帝為了鞏固政權,推行了許多大刀闊斧的改革,包括遷都洛陽、改姓氏、穿漢服、通婚姻等,使胡漢之分逐漸消弭,對當時和後世都有深遠的影響。這時期開鑿的石窟,佛像面容開始變得柔和,眼眸拉長,嘴角收斂。
到了後期,那些坐在蓮座上的佛與菩薩,身上的袍袖已逐漸演變為南朝士大夫的穿著──寬袖長袍,腰間繫帶,臉形與五官也變得愈加漢化。在一公里的路程裏,走過的卻是跨越好幾十年的時代變遷。
或許正因如此,雲岡石窟與洛陽的龍門石窟雖同為北魏石窟,給人的感受卻迴然不同。雲岡的佛像臉龐厚實,刀法直接有力,是漢與西域、印度、中亞等多種文明藝術融合的初期;而龍門則更好地「承先」,融合了漢文化,佛像比例更精準,表情更內斂,雕刻手法亦愈臻成熟。
當我走到最後時,陽光正落在第20窟露天大佛的臉上,石面被染上一層淡淡的金色。大佛結跏趺坐,眉目慈祥,手結禪定印。


雪停了,大佛依舊靜靜地坐在那裏,看着一代又一代的旅人來來往往。雪會融化,太陽會重新升起,而我也會繼續前行。

原刊於點新聞,本社獲作者授權轉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