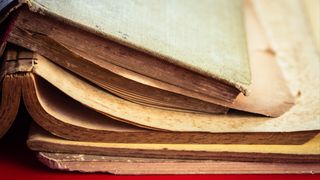真理愈辯愈明?這句話看似天經地義、理所當然,但卻盲點處處、脫離現實,在網絡時代更呈反其道而行之勢。希望透過對等討論或辯論而找出真相或真理,是如此的一廂情願,猶如癡人説夢。
如斯事例舉目皆是,日前本地資深電影人文雋,批評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冷待」賣座電影《破.地獄》,以及電影評論學會董事會主席李焯桃回應一事,就是新鮮滾熱辣的典型例子。弄清此事背後之思路,或許可以帶給我們更為切身及深遠的思考。
質疑聲音
今年1月12日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公布第31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得獎名單,《九龍城寨之圍城》奪得最佳電影,而本年度最賣座電影《破.地獄》未能得獎,僅被納入10部推薦電影名單。
4天後(1月16日)該會創會會員之一、資深電影人文雋在其網台節目上認為《破.地獄》被學會冷待,其賽果很可能是經過計算,並不公平。
文雋的批判可歸為三大理據:
一、質疑電影評論學會的投票機制;
二、如此賽果,很可能是經過學會會員經過計算後的結果;以及
三、經過計算的賽果,是與全香港買票觀看《破.地獄》的觀眾為敵。
繼而資深電影人田啟文在1月23號接受訪問,稱不知道電影評論學會的評選準則為何,認為其缺乏透明度,以及「見唔到評論學會有解釋《破.地獄》係輸係啲乜嘢」。
回應文章
隨後在2月5日,學會董事會主席李焯桃在《明報》世紀版以文字回應(〈第31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大獎平議〉),全文約1萬字,分為七個項目予以解釋及反駁,具體觀點如下:
一、電影票房與獎項並不存在必然的因果關係,例如《一代宗師》和《東邪西毒》;
二、學會的投票機制是接近電影節和金馬獎的評審團模式;
三、學會向來重視會員素質,嚴選入會資格;
四、陳述學會多年來所實行的投票機制;
五、陳述整個評選標準及程序均以文字記錄,且在每年出版的年度香港電影回顧專書中公開披露,其中附上每人每片的得獎理由;
六、陳述電影學會每年都須向香港藝術發展局提交完整的會務報告及財務報告,接受委員會及審批員的考核,長期均獲得高度評價。
好了,文雋透過網絡質疑/批評,李焯桃經由紙媒解釋/反駁,此時「真理愈辯愈明」的前提已然存在。那下一步正反雙方是否能夠繼續討論,説清箇中是非,令真相浮現呢?

還原基本步之循環論證
當然不是。因為討論就此打住,一切還原基本步,充其量只是多了個循環論證。因為自李焯桃於2月5日回應後,文雋在2月16日的訪問中是如此說的:
「我在節目上說電影評論學會冷待《破.地獄》,不是為《破》爭取獎項,只是這部電影獲得那麼好票房,又是全城討論,為何在評論學會20幾人討論時都不受重視,討論完不給獎。沒有所謂,我只是發自內心,難得有一部好戲。」
然後他說《破.地獄》團隊應多謝金像獎選民,18項提名證明他們的辛苦是沒有白費云云。
這是一種怎樣的回應呢?這只是將自己於1月16日的看法相對溫和的再說一遍,然後繼續通知大家電影評論學會的選擇與廣大觀眾背道而馳。對李焯桃的七個解釋,他並無回應。
電影評論學會是否小圈子選舉?其投票機制是否有問題?會員的資格何在?是否走偏鋒?又是否冷待《破.地獄》?票房收入與電影鑒賞和評論究竟是何關係?這些問題一個都沒有弄清,連說法也沒有一個。
不對等、反思考的溝通模式
以上論述孰是孰非,讀者不妨自行分析。我更有興趣的是這種獨特且普遍的對話模式──正反雙方基本上可以毫無交集,各說各話,然後就此打住,而我們的社會整體卻能夠如此神奇且自然地形成「定論」。
哦,說雙方毫無交集倒不太公平,因為往往是被指責的必須回應,但主動指責的卻不用理會,充其量只是將批評再說一遍。
如此模式有何特徵?一是只重論斷或立場,二是不重理據,三是缺乏交流(或毋須交流),姑且可稱之為「自說自明」或者「霸王硬上弓」式溝通。雙方打一開始就處於不對等的失衡關係,在「先下手為強,後發者吃虧」的格局下,「真相」老早定調。
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是目前還是將來,留給大眾的只有一個印象中的真相:香港電影評論學會小圈子選舉,評選準則很有問題,冷待高票房電影。君不見網絡上一面倒的訊息,已老早宣判了真相。
如此模式下,再多的文字解釋也注定收效極微,嘥鬼氣,尤其在這個網絡主導、文字沉淪,以及專注力弱化的現代社會。(敝文必然君體相同,幸好不為收效,但求自明。)

我們得到什麼?又錯失什麼?
如此溝通模式着實不妥,後果堪憂,不但容易導致群體性的認知錯謬,更很可能扼殺了獲得新知、提升民智的可能。
為何?因為合理的論爭有三大内核,一是尋求真相,二是修正自我,三是延伸討論,具有螺旋式提升認知的效果。而該次事例就相當遺憾,三者皆失,前兩者一早收檔,第三內核(延伸討論)也隨之錯失。
為何?因為此事除了弄清電影評論學會有否故意冷待《破.地獄》外,本可以帶出一系列與之密切相關的討論,例如,我們該如何鑒賞電影?票房高低是否與電影水平直接相關?電影評論的標準為何?如何定義電影藝術?香港的電影評論又是如何發展、有何特色或缺點?前景及方向又是如何?
這些本是更有意義,有助提升大眾電影鑒賞力的話題,但卻無人在意。大家只關注誰的聲音更大,哪個票房更高,為何不支持高票房的本地電影,評選透明度很有問題,以及繼續發酵的種種陰謀論……
真理還是愈辯愈明嗎?在虛無主義和相對主義大行其道的時代帷幕下,如斯壯言顯得如此的乏力及滑稽。
既然如此,社會上那些所謂的真相、真理,主要靠什麼來決定呢?觀乎當今世情,也許誰的聲音更響、權力更大、話語權更多,以及深諳網絡操盤才是終極王道。
知道那麼少 懂得卻那麼多
此時有人或會說「觀眾的眼光是雪亮的」,只要獨立思考就一定能夠辨別是非。天見可憐,這肯定又是個一廂情願、脫離現實的奢望及幻想。
原因有二。第一,人之理性說起來高大上,有助提高盲目自信,但在現實中卻問題重重,所謂的理性可以是非常盲目及反理性,歷史上的例子比比皆是,其禍害是恐怖及災難性的。多少古今思想家對此憂心忡忡,提出洞見,呼籲大眾予以警惕,更要慎防高估自己。(註1)
第二,在資訊泛濫、網絡速食文化及專注力喪失的時代,本就諸多盲點的理性和獨立思考更是江河日下。人們更希望一步到位,化繁為簡,盡快得到所謂的定論或觀點,對於轉發的興致,也遠大於對真相的關心。故此指望主流群體能具備鑒別真假的金睛火眼,既不符人性,也違背現實,卻切合政客獲取選票的公關口吻。(註2)

如此看來,現今最令人擔心的還不只是那類不正常的討論模式,我們更需要正視一個無比切身的重大問題:為什麼人們知道的那麼少,卻自以為懂得那麼多?
不是嗎?社會上深信自己已掌握真相及真理,繼而振振有詞,付諸「正義」行動的人難道還少嗎?時下主流是擅於論斷,還是自我懷疑?是將複雜事件簡單化,還是睇定啲先再講?是你要畀我發聲,還是我都唔係好知?
此時深諳人性本質,且在背後操盤的聰明有心人,繼續猶如洗腦般地鼓勵每一個人:「你正在獨立思考,你是自由自主,你真有社會良知,我很尊重你的看法,社會的未來由你決定,你的聲音真是非常重要……」(註3)
這也難怪多少有識之士對那個聲稱以個人自主及獨立思考為基石的現代民主深存懷疑。因為「真理愈辯愈明」是這兩個神聖觀念後那看似毋庸置疑的前提,如此的令那「原子式」的個人血脈沸騰,自我膨脹,卻又如此的銀樣蠟槍頭,就好像這次發生於本地的獎項風波那樣,如此的荒誕,卻又如此的真實。 (註4、5)

註釋:
- 西方思想家對人類理性之反思論述比比皆是,例如
- 古希臘時期蘇格拉底的「自知無知」(Socratic ignorance);
- 休謨(David Hume)認為「理性是激情的奴隸」,揭示理性在動機層面的依附性;
- 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反思法國大革命,認為「政治應該適合人性,而不應該適合人的推理。理性只是人性中的一部分,而且絕非最大的一部分」;
- 法蘭克福學派對於啟蒙理性的悖論分析,認為理性主義中存在「同一性暴力」;
- 李歐塔(Jean-François Lyotard)、傅柯(Michel Foucault) 揭露了知識與權力的共生關係,認為理性常常是權力結構的共謀;
- 心理學家鄧寧(David Dunning)和克魯格(Justin Kruger)提出了「缺乏元認知」(meta-cognition)概念,即缺乏對自身認知能力的反思能力;
- 心理學家史蒂芬·斯洛曼(Steven Sloman)指出人們常將「他人知識」(如網路搜尋結果)誤認為「自身知識」,導致虛假的自信心。
- 例如美國語言學學者Naomi S. Baron的著作《數字世界中閱讀的命運》中,揭示了網絡世界對書寫的巨大衝擊,降低了人類思維、反省和表達的能力;Mark Bauerlein在《最愚笨的一代》指出,美國大學生整體素質下降,語言能力減弱,專注力喪失及知識貧乏,「卻以為一機在手,萬事皆曉,自信心爆棚」;作家Susan Jacoby在《美國的無理性時代》一書,她指出當今美國的反智主義是史無前例的嚴重,體現在對於無知的「毫無羞恥感」,並漠視理性和客觀真理,而網絡就是背後的強大黑手。
- 有關本地社會運動期間,聰明人如何運用在網路上散布錯誤訊息,從而操弄民意,鼓動撕裂,本人曾有文章予以分析,見〈盲從網絡,還是回歸文字?──從社會運動時期的一幅油畫說起〉、〈「感人」音樂與「理性」判斷──從蘇聯歌曲《喀秋莎》說起〉。另可參考普林斯頓大學哲學系主任哈里·法蘭克福(Harry G. Frankfurt)的著作《廢話》(On Bullshit),本人曾予以引用,分析「亂噏當秘笈」現象對社會的負面影響,請參考〈論土豪式亂噏〉。
- 當代哲學大家Charles Taylor對基於原子式個人的現代民主相當懷疑,深入反思啟蒙運動以來的「世俗化理性」(secularized reason)。他認為這種理性難以使人成為真正的「自由行動者」,如此所形成的共同意志並不具有正當性。見Charles Taylor《當代社會中的理性》,聯經出版公司,2018。
- 值得留意的是,席捲全球的網絡文化正嚴重削弱民主模式的基礎。台灣文化人張鐵志曾引用哥倫比亞大學法律教授、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的高級顧問吳修銘(Tim Wu)的著作《注意力商人》(The Attention Merchants),認為以網絡為主導的「注意力經濟」(Attention Economy)已席捲全球,不斷侵蝕及弱化個人的理性及思辨能力,而此二者卻是民主模式的重要基石。換句話説,掌握網絡話語權,才是真正的「真理」締造者,影響那些自以為「個人自主」及「獨立思考」的廣大網民。參考〈張鐵志:注意力經濟不斷侵蝕我們的思考能力〉